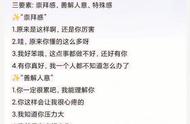塑造个人
除了衡量原因之外,历史学还塑造个人。
历史学是民族认同的熔炉。通过民族传奇、法国国王的传说、革命和帝国的史诗,历史学成为团结的要素。同时它也有批评职能。知识就是武器,历史学解释民族如何形成,由此给公民提供一些途径,让他们形成自己关于当时政治和社会演变的观点。例如,它给法国人提供了要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采取某种独立的、有强烈动机的立场所必需的思维工具。
历史学家夏尔•瑟诺博司曾说,历史学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参与社会生活”,接受必然的变动,并有秩序地为这变动做出贡献。为此,就必须让学生理解自己将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这正是历史教学的独特意义,历史学也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有能力来造就公民。
不过,历史学远不止是一座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它还塑造了做历史学的历史学家。米什莱在《法国史》的序言中曾说:
“时间流逝,历史做出了历史学家,远甚于它被历史学家所做。我的著作创造了我。我才是它的作品。是儿子创造了父亲……如果我们相像,那很好。它来自于我的特征在很大程度深是我欠它的,是我从它那里得来的。”
每当历史学家着手研究一个新主题时,他都为此必须以第一人称重新思考。他必须设身处地,重新经历他研究的那些人们所生活过、感受过和思考过的。历史学家重建人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住所、服饰、饮食、劳作、所用物品和所交换的东西;他重建他们的思想世界、对世界的观感,他们的欲求、渴望、宗教信仰等等。
这种出奇丰富的体验激发、培育了多种态度。要有这种体验,就要去想象,要怀有好奇的和殷切的同情心,可以说,是要虚己以待,让自己受对象本身的指引。

然而,历史学家不是小说家,他不听任自己的想象力为所欲为。光对他所研究的情境中的人做一番想象还不够,他还必须核查他的想象是否准确,要在文献资料中找到痕迹、迹象和证据来确证他的说法。
历史学是想象,历史学也是通过博学研究来对想象所做的控制。它既是同情,也是警戒。
历史学家就这样在其他境遇中经历其他生命的体验,由此他最终发现自己是何人。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再次引用柯林武德:
“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知。”
然而,历史学家也由此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的人,而同时自己还是自己。这是种矛盾的体验。这种体验使我们可以知道,人对具体历史境遇的依赖有多么大:认知存在于某个特定社会中的某个给定时间的此处或彼处。
哲学家很久以来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人,世间的存在。我想加一句:人,时间的存在。历史学使历史学家回到了人类境遇的历史性和他自己的历史性。

构建人性
历史学让我们理解了生活中的各类难题,因为生活就是一直经受着各种难题。这是历史学教给我们的,它向我们表明,从来都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社会是不碰到难题的。人们说“幸福的人没有历史”,有时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学让人明白,在这些难题上交错着我们无可奈何的制约,与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做出的选择。它使我们免于被当前的生活所吞没,这是因为,通过理解当前的生活,我们对之做出了解释,这样,以一定的方式,我们仍是它的主人。
从这个观点看,历史学不仅仅是公民教育,它是在每个人那里永无止境的构建人性。
诚然,我们对一切反思性的学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许还有文学)都可以如是说。然而历史学比它们的方法还是要多一些东西:它是动态、运动和演变的。
因为人是历史的存在,因为他的历史性是他这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做历史学工作,他就无法构建自己。人们经常说,只要还有人,就还有历史,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个神话。然而这句老话应该倒过来说:只要还有历史,就还有人。
历史学是对存在于每个人,永远必不可少;这项工作不断在新的基础上重来、从新的问题出发。处于社会之中的人是一种既脆弱易感,又能感染他人的实在,如果没有历史学这项工作,他就会被野蛮给盯上。而这野蛮是一直都可能出现,不会彻底消失的。

- 版权信息 -
编辑:子水 黄泓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历史学十二讲》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