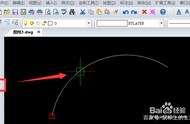作者:胡晓军
一
《2023中国诗词大会》近日圆满收官,受到观众好评。无数人聚焦于这一诗词的舞台,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它生动演绎了古典诗词在当下的一种活法。

《2023中国诗词大会》海报
2016年,央视首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问世,热播全国。笔者也同万千粉丝一样,连续追“季”,兴奋之余更作一文,认为该节目所采用的网络海选、才智PK、权威点评方式,加上催泪故事的编织、平凡英雄的打造,这一系列新颖时尚的创意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推广,可积极扩展古典诗词的群众基础,并进一步认为当代原创诗词若能按此办理,同样有望实现“扩群”,实现与古典诗词盛况的“合龙”,重现“诗的国度”的当代愿景。
而今回头再看,感觉自己当时未免有些冲动——不能将公众对古典诗词的欣赏热情,等同于他们对原创诗词的接受愿望。事实上,两者的差距极大,不在一个谈论范畴。
当然,新时代以来,我们也看到原创诗词势头渐劲、发展正猛,据粗略统计,目前全国诗词作者已达三百万人,各类诗词报刊三千余种,加上自媒体,每年推出的新作近千万首。然而,必须承认,当代诗词作者队伍貌似庞大,但占全国总人口之比却是小而又小,难以突破小众文化状态。原创诗词作品看似海量,但其与质量的落差大而又大。这种落差不仅损伤了原创诗词的名誉,也遮蔽了少数力作的光芒。
孔子用“兴、观、群、怨”(《论语·阳货》)来表述诗的社会作用。“兴”是抒情与启思,“观”是观照与认知,“怨”是指责与批判,三者均属创造审美层面;“群”是传播思想情感、交换见解看法、寻求社会共识,属于接受审美层面。平心而论,当代原创诗词在“兴、观、怨”上的表现不虞匮乏,且少数优秀之作既有情感又有观念,既有赞美又有批判,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但因“群”的过小导致创造审美与接受审美不匹配、不平衡。“兴、观、怨”一旦“失群”,便失去了从个体精神扩展为社会精神的可能。而起决定作用的内因,是语言文字系统及环境的改变,使根植于文言文和古声韵系统的古典诗词,成为今人乐于学习、欣赏和引用的“非遗”文化;却使同样源自文言文和古声韵系统的原创诗词,不复是使用白话文和普通话系统的今人惯于接受、欣赏和传递的文学体裁。
综上所述,传统诗词创作需求量小及其所致的交流圈窄、传播力弱,并非个人之力所能造成,而是时代社会变迁、语文环境变动再加上文体盛衰、审美兴替的综合作用。
二
回顾历史,传统诗词创作到了清末,早已沦为强弩之末,不但在应对时势变化、回应社会关切上无能为力,反而因大量泥古不化、缺乏情志的劣作而遭抨击。只不过,因启蒙教育、审美习惯仍在,人文环境、社会共识依然,传统诗词虽已无法真正发挥“群”的功能,却仍可以撑持“群”的规模。此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诗词创作很快两者尽失。
20世纪的诗词创作,为了反映新生活、表达新思想、展现新形象,大量使用新词组、新语法、新韵脚,呈现出与传统诗词迥异的创作风貌并影响、推动了更多相似作品的出现。为了与传统诗词进行区分,可将其称作“非传统诗词”。非传统诗词也是诗词,虽然其文学的属性弱、格律的问题多,却能凭白话文语境、普通话声韵,为当代诗词创作扩“群”。改革开放以来,非传统诗词与传统诗词的创作都进入低谷,并出现了前者向后者靠拢的趋势。大批非传统诗词创作者放弃了“主义”或“主意”,活用经典诗句、使用典故符码、讲究对仗音韵、追求意境营造,试图在古典美与时代性中找平衡、求发展。这种平衡与发展,对具备文言文功底和古声韵能力的作者而言,则更易达成。
最重要的还是语境。百多年来,“言文一致”已实现,而“言文隔绝”并未出现。“文白交织”的语境为“文白互用”的文艺创作提供了通道和空间,体现在小说、散文、戏剧、曲艺等多种门类上,其中诗歌要比其他体裁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一,单字思维依然运用普遍。名词方面,白话词组取自文言单字,仍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拆分、独立使用(如“光明”“魂魄”“感觉”“冰雪”“道义”“缺少”“增加”),这显然有利于对仗(虽然容易“合掌”)。文言单字常与白话词组结合,成为“半文不白”的新词组(如“航天魂”“获得感”“可燃冰”“无间道”)。值得一提的是,追求字数相当,但词性、平仄并不求完全对应的词句,在当下的创作中十分常见,可称其为“非传统对仗”,例如,“星光何等耀眼,烟花如此炫丽”“修志存史励后人,鉴往知来开新局”。白话词组工对难度较大,而“非传统对仗”虽然略显粗糙,但有利于诗词创作思维的培养。
其二,成语熟语依然引用广泛。源自农耕社会、基于文言文系统的成语和熟语,依靠基础教育助力大量被使用,其所蕴含的历史、自然、人文典故也为今人所熟知,这明显有利于诗词创作中的用典。古代成语和熟语大多已具备了延伸意涵,在使用中毫无过时感、违和感,极少被新词所取代。即便偶有同义或近义的新词出现,质量并不更优,底蕴并不更深,生命力也未必更长。
其三,文化符码日渐被频繁采用。随着古典文化以各种形态回归今人的视听,许多具有隐喻性的事物和象征性的意象(如“红豆”“兰舟”“桃源”“荼蘼架”)被人们广泛读取,并开始在生活中被频繁采用,例如“采薇服饰”(意为天然质朴)、“梦蝶电子烟”(意为哲学冥想)、“东篱农家乐”(意为自然食材)等。即便今天的科技进步已到了“上天入地”的程度,但其冠名仍多为“嫦娥”“神舟”“天宫”“蛟龙”之类,这些具有历史积淀感和民族象征性的符码,早已与当代生活、文化融为一体了。
总之,语文环境的“文白交织”和日用而不觉的“文白互用”,既有益于传统诗词创作的生存,也有助于非传统诗词创作的提升,更有利于两者的共存、竞争与调谐、优化,并逐渐形成了属于新时代的“新传统诗词”。
三
可以确定的是,新时代之诗词创作,已不是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旧文学”“死文学”,而是中国梦理想要复兴的“新文学”“活文学”之一。欲为新时代之“新文学”“活文学”,诗词创作须在“兴、观、怨”尤其是“群”上有突破、有发展。如前所述,基于文言文语境和古声韵系统的传统诗词创作无法实现广泛“扩群”,而基于白话文语境和普通话声韵系统的非传统诗词则难以有效“扩群”,必须开辟新路。
开辟新路,并非“另辟”,恰恰是在传统诗词创作和非传统诗词创作的共存、竞争中,逐渐完成调谐和实现优化,以“新传统诗词”使“扩群”既保持高质量,又掌握普遍性。
这种现象以及趋势,早已现出端倪。其中非传统诗词向传统诗词创作的靠拢,前文已有述;而对传统诗词创作方法的改革则出现得更早,并持续至今。改革的着力点,主要在四声和押韵。由于普通话的普及教育及社会覆盖,古典诗词欣赏与传统诗词创作均出现了四声和押韵不匹配的问题,故对今人而言,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都是充足的。
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一是将入声派回平上去声,按普通话的四声重新标定,得到“新声”;二是以此“新声”划定诗韵,得到“新韵”。两者合为“新声韵”,使传统诗词创作整体进入白话文语境和普通话系统。此举与非传统诗词创作,堪称是相向而行。而采用“新声韵”的传统诗词创作,吸引了大批新作者和大量新读者,为“扩群”作出了贡献。
不过,改革必有代价。“新声韵”一方面会挤压传统诗词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会使少数非传统诗词创作愈发“无厘头”,在边“扩群”边“失群”中重蹈新诗的覆辙。事实上,已有一些诗人如周啸天等因践行“白话文”、尝试“新声韵”付出了被指责甚至被谩骂的代价。笔者以为,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样的代价是必要和必需的。
由于古典诗词的强大和深入人心、“文白交织”的语境及现实状态,恪守文言文语境和古声韵的传统诗词创作仍具生存合理性,却不复适合成为新时代诗词的主流。同时,但凡改革包括文学改革,都会是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创作实践和研究成果,需要社会和时间的共同检验。笔者以为,当下只是新时代诗词的初级阶段,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暂时的、局部的,都应作为相关研究的材料和改进的载体。而诗词创作中存在的“口水化”等问题,虽很可能泛滥,却也不必对其过分担心。回望历代的传世佳作,能为今人耳熟能详、口诵笔录的多为当时通俗也很文雅、文言而近白话的作品。由此推断,大可不必为当前新传统诗词的“浅白”“俚俗”而杞人忧天。对诗词创作而言,重要的是在诗的情志立意、时代特征、生活质感、普适情趣上多下功夫。
我们不能低估传统诗词、非传统诗词的转化能力和转型能量,它们都将是新传统诗词萌生与长成的主力。可以看到,传统诗词创作正在不破古律的前提下吸收白话文词汇(包括网络流行语)、普通话声韵(寻找与古声韵相同的字词)以反映现时代;非传统诗词也在“力写今生”的前提下运用单字思维、典故、工对以增强古意——年轻的初学者尤其如此。两类创作的性质和站位不同,但目标一致,有望在交流和竞争中实现求同存异的共识、优胜劣汰的发展。
只要保持理性的宽容,避免非理的攻讦,新传统诗词创作则可迎来多样性的繁荣。相信这两种力量的合作,将会达成笔者对新传统诗词的愿景——以白话文和普通话声韵为主,以文言文和古声韵为辅(白文结合,以白为主),反映这个时代的真生活、抒发真情感、表达真理念、挥洒真兴趣,摆脱机械呆板,拒绝形式主义,实现总体标准、同中有异、灵活变通、古今逢源的体裁形式,在白话和文言自然而巧妙的结合中生发诗意,在社会的评价和历史的检验中持续“扩群”。(胡晓军)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