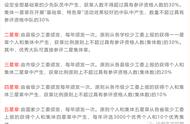今天还能写作,是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阅读
《教育家》:今年5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作为校内实体机构正式成立,您担任所长。文学讲习所在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和语文教育方面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文学讲习所您有什么样的期许?
曹文轩:成立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20年前我就提出来了。一方面,是为了消除一个误解——“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另一方面,是为了顺应全世界兴起的创意写作潮流。
从北大中文系自身的发展历史而言,教授作家引导学生成立文学社团从而形成某种文学流派,这本就是北大开创的传统,也是现代文学时期高校普遍采用的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讲课: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吴组缃、林庚……
大学对于作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除了能在理性上给予人足够的力量,让理性之光照亮自身的生活矿藏,激发出必要的艺术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它酿造了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所必要的冷静氛围,为培养作家和作家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机会、一种可能。纳博科夫在谈到“大学与作家的关系”时,非常在意一种气息——学府气息。他认为当代作家极需要得到这种气息。这种肃穆而纯净的气息,将有助于作家洗涤在生活的滚滚洪流中所滋生的浮躁气息,使作家与生活拉开必要距离,更有助于分析生活。
除了文学创作上的意义,我以为作家在大学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他们的研究,会使学术研究出现另一种路数,从而使学术研究更加立体、更加丰富。鲁迅的学问,是一个作家的学问,或者说,他如果不是一个作家,也许就做不出那样一种学问。不是说作家的学问好,而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与纯粹的学者做的学问,可交相辉映。
《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文学理论研究者这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曹文轩:的确,这两种身份看似是矛盾的,因为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具象的、感性的,一种是抽象的、理性的。但这对我而言,我曾说过“简单得就像看电视换频道一样”,而且它们之间一定是存在正面影响的。鲁迅当年在北大当老师、做学者,同时也是作家,他也在学术与创作的双重工作中困惑过,但他本人恰恰是将二者结合得美妙绝伦的实例与典范。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文献,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绕不过去的著作。
另外,理性的东西对文学创作是大有裨益的。走了这么多年,我深深地体会到理性对一个作家来讲是多么重要。我很感谢自己15年的哲学阅读史,在特殊的年代只能看马恩哲学及其相关书籍,培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然后一路下来,读到科恩等人的科学哲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这些都对我影响巨大。不要小看一两千字的童话书,那背后其实是哲学在潜移默化里给我的力量。当然有个问题值得注意——当你进行创作时,一定要把这些痕迹抹得干干净净,不能在你的文学作品里去显示理性对你所发生的作用。
《教育家》:您一直非常强调阅读的作用,能谈谈在您身上阅读和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吗?
曹文轩:阅读是写作的前提,写作是阅读的结果。就我个人而言,为什么今天还能写作,是因为我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在我的时间表上,一直是三分写作、七分读书。我的阅读量非常大,读书非常杂。我的床头永远堆着书,可能一会儿看看民国的京剧,一会儿看看《德国的科学》,一会儿看看印度的《奥义书》。各种知识交汇在一起会使人的感受力得到升华。比如《资本论》里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公元1世纪的作家普鲁塔克提出的哲学难题“忒修斯之船”,都可以给我带来写作的灵感。
我早就意识到,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拥有生活的海洋,其实是很难维系捕捞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捕捞。他如果要使创作的香火延续不断,必须同时拥有两片海——生活的海洋和知识的海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的海洋可能更加重要,没有这片海,生活的海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最多也就是一片空海,是无法发生捕捞的。知识海洋不仅让我们发现了生活海洋,它本身也可供我们捕捞。一个单词、一个短句、一个观念、一个隐藏在他人作品中未被作者感觉到的动机,都可能是难得的捕捞之物。这种从书本中获得惊喜的情景,我已无数次地体验了。所以,我必须拥有两片海洋,我要驾着我的小船,自由地出入于这两片海洋,只有这样,我才能使我的一生成为捕捞的一生。

语文的美好,应该是什么样子
《教育家》:您在《回忆我的语文老师》中写道:“特别要感激的是我的语文老师……这位女性是我心目中最高贵、最美丽的人。”
曹文轩:这位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的高才生,是“文革”期间下放到我们那里的。当时来自无锡、苏州多所名校的名师集中到穷乡僻壤的一所学校里教书,对我们来说真的堪称“盛宴”。当说到那段历史时期的时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涌现的是停课闹革命、是文化荒漠,但我的历史记忆不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受到的最好的教育恰恰是在那段时间。
虽然当时的语文课本非常政治化,但我的老师是把它当语文课来讲的。我记得她第一次走上讲台,把两只手轻轻地悬在讲台上,她没有带粉笔,没有带备课笔记,也没有带语文教材,是空手走上来的。她望着我们,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什么叫‘语文’?”然后她用了两节课的时间,给我们阐释什么叫“语文”。其间,天开始下雨,她将脸朝向窗外,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年四季的雨是不一样的。春天是春天的雨,夏天是夏天的雨,秋天是秋天的雨,冬天是冬天的雨。”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天里的雨也是不一样的,上午的雨与早晨的雨不一样,下午的雨与上午的雨也不一样,晚上的雨与夜里的雨也不一样。”然后她又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雨落在草丛中和落在水塘里,那个样子和发出来的声音都不是一样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所有人把脑袋转向了窗口,外面有一大片荷花塘,千条万条银色的雨丝纷纷飘落在那片很大很大的荷花塘里。这就是我的语文老师。虽然她长得并不好看,但她是一位气质非常雅致的女性。后来她离开我们去读书了,考到了现代文学史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先生的门下。
《教育家》:您曾写道:“语文和语文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是一所学校的品质的建构者和体现者。”您认为新时代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哪些素养?您怎样看待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
曹文轩:在我的心目中,语文是一切学科的学科。一位数学家若没有非常好的语文能力,想成为那种划时代的、具有纪念碑式意义的大数学家,是绝无可能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哲学家也一样。因为语文能力牵涉到思维能力以及认识世界之后的表达能力。
语文老师首先应该拥有非常好的语文能力。语文能力来自哪里?除了专业知识的培育,还来自广泛的阅读。我曾多次讲过,如果一名语文教师仅限于堂内阅读,哪怕这种阅读特别精细甚至烂熟于心,他也不能对语文文本做出理想的解读,因为他需要一种发现文本的眼力,而这种眼力来自堂外阅读。语文是一座山头,攻破这座山头的力量,并不在这座山头,而是来自其他山头。周边的山头屯兵百万,你必须广泛调集其他山头的力量,才能把语文这座山头拿下来。学生学习也一样,一个学生如果只将语文堂内阅读当成阅读的全部,想学好语文是不可能的,就算把语文课本全背下来也没用。
另外,讲文学课,我们务必不能只停留在对作品的人文性解读上,还要回到艺术层面对作品进行解读。现在,凡选到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都是经典,或者说是具有经典性的作品。既然是经典和经典性的作品,必有一个前提:它们具有高度的文学性,或者说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语文老师解读一篇文学作品,应以欣赏一件艺术品的姿态进行,并以这一姿态去影响学生,使他们也能在面对一篇文学作品时呈现出一副欣赏姿态,成为一个有情趣的文学欣赏者。但遗憾的是,因为我们在此之前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没有这个意识,又因为我们对艺术性范畴的知识掌握不够丰富,即使在艺术层面上进行解读,也显得有点勉强,不是蜻蜓点水,就是机械性套用。
我总记得一次去某座城市的一所学校给孩子们讲写作,其间说到了契诃夫的经典短篇《凡卡》。我就问现场的孩子们:“有谁现在愿意和我谈谈《凡卡》的?”正好赶上他们刚刚学完这篇课文,一个小男孩将手高高举起,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慷慨陈词:“《凡卡》写了俄罗斯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控诉了沙皇俄国的残酷统治……”这个男孩口才绝佳,滔滔不绝,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掌声。听下来,这个孩子的所有言辞,都是关于《凡卡》的思想意义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品主题。他说得对吗?当然对。但,这毕竟是一篇小说,是一篇文学作品,对它的解读不能仅有这些。于是我问他:“你还能从其他方面说说吗?”男孩忸怩了很久,说:“没有了。”
那天报告厅的后几排坐着一个区的语文老师。我问了两个问题:如果将凡卡在皮匠店里做学徒的苦难经历,由凡卡给爷爷写信倾诉出来,改为由作家本人直接叙述出来,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篇叫《凡卡》的经典短篇吗?凡卡投到信箱中的那封信是一封没有地址的信,那信封上只有一行“乡下爷爷收”的字样,如果文中没有这个著名细节,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一篇叫《凡卡》的经典短篇?以上两个隶属于“艺术”的问题,是这篇小说的“眼”和“魂”,如果没有讲到,我们能说完成了对这篇小说的解读吗?恐怕不能。
— END —
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12月刊第2期,原标题《曹文轩:用文学为儿童“造房子”》
文|本刊记者 李香玉
设计 | 朱强
统筹 | 周彩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