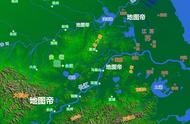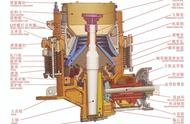诗文、书法和绘画原为彼此独立的文艺形式,可宋元时期的士大夫文人在创作实践中把这几种文艺形式有机融为一体,相互辉映、相互补充——用诗歌抒发情感,在书法中感受风骨,于绘画里获得气韵生动的生命体验。
“琴棋书画”四艺并称的记载,在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里虽已出现,但直至宋元时期,弹琴、弈棋、书法和绘画才真正成为士人“游于艺”的主要内容。作为怡情养性的生活之艺术,宋、元士人精研四艺进而涌现出大量的琴诗、题画诗、论书诗和书画题跋。诗与音乐和书画艺术的会通,成为推动宋元文艺思想发展的重要元素。

古淡深远的琴声
有关“琴棋书画”的诗歌创作,既反映作者的性情和品格,也包含着对文艺作品气韵、风骨和意境的认识。以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的古琴而言,向来分为“艺人琴”与“文人琴”两个序列,文人琴于宋代不只是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流行,还为许多山林隐士和僧人喜爱,留下不少咏琴的诗歌。琴道的承传、琴心的感应和琴意的发明,都在“古淡”的琴声中展开。如欧阳修喜好弹琴,《江上弹琴》里有:“江水深无声,江云夜不明。抱琴舟上弹,栖鸟林中惊。游鱼为跳跃,山风助清冷。境寂听愈真,弦舒心已平。用兹有道器,寄此无景情。”调清、声直、韵疏迟的古琴,可以用来修身,培养高尚的情操,还可以交流思想意识,以至于用它来参禅悟道。在宋代士人所写的琴诗中,有对古淡乐音的细腻体会,有对自身命运的感慨抒怀,有对清幽韵味和深邃思想的心领神会。梅尧臣的《次韵和永叔夜坐鼓琴有感二首》说:“夜坐弹玉琴,琴韵与指随。不辞再三弹,但恨世少知。知公爱陶潜,全身衰弊时。有琴不安弦,与俗异所为。寂然得真趣,乃至无言期。”宋代士人习惯以琴声传达清幽意趣和无言之美,在描写琴乐的琴诗里,他们重视的不是“艺”而是“道”,希望能借琴声明心见性,故不太关心弹琴技法是否纯熟,而倾心于琴声意境的深远。

淡墨写出无声诗
随着士人画在北宋中期的兴起,以题画诗为代表的绘画文学与音乐文学一样蔚为大观,宋代题画诗的数量已超过5000余首,元代题画诗的数量则多达近万首。“题画诗”的大量涌现标志着诗歌与绘画的深度融合。所谓“题画诗”,从狭义的角度说,就是题写在图画上的诗歌,而广义的题画诗创作不一定非要题在画上,也不必局限于所观画的本身,题画者可以自由挥洒、驰骋想象,尽情表现因观画所引起的一切情绪感动,表达自己的审美爱好和艺术格调。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里提出的“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观念,明确将绘画纳入以诗为主导的文学体系里,促进了文人品题绘画的流行和诗意画创作的进步。他曾采用杜甫的诗句,与著名画家李公麟合作了一幅诗意悠然的《憩寂图》。
黄庭坚在《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二首》里说:“松含风雨石骨瘦,法窟寂寥僧定时。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把诗句绘成图,是为了更加形象地表现诗的意境美。黄庭坚用“淡墨写出无声诗”来形容诗人与画家合作的诗意图,非常到位,十分贴切,以至后来“无声诗”遂成为中国画的流行称谓,而包括题画诗在内的意象鲜明的诗歌则被称为“无形画”。但诗与画毕竟分属不同的文艺门类,作为时间艺术的诗歌,如何与属于空间艺术的绘画互补?苏、黄等人的题画诗创作和书画题跋,为解决这一重要文艺问题指出方向,使得宋元时期的诗画会通意识不只体现为题画诗和诗意图的创作,而且由意境风格上升到美学精神和艺术思维层面,对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视听圆融的美感
宋代由文同、苏轼开创的“士人画”,重在表现作者意在丘壑的胸襟和君子人格,带有文人“墨戏”性质,多以简笔水墨为之,率意而作,痛快淋漓。“墨戏”又称“墨戏三昧”, 作为文人士大夫参禅悟道的艺术方式,多出现在“墨竹”和“墨梅”画的创作里,用单纯的水墨体现禅定时澄明寂静的心境,达到与自然冥合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自然无我之境。墨戏并不限于绘画,也包括书法,尤其是行书和草书,以笔画的“天趣”和“神采”展现作者的逍遥自适心态,体现造意和率意的风格。如果说般若空观对“诗中有画”的山水诗的兴盛具有决定性影响,那么“诗画一律”的创作则建立在六根互用的通感和视听圆融的通观之上,涉及视觉与听觉的沟通、色法与心法的集合,以及虚实相生的美学原理。以庄禅思想为底蕴的视、听圆融之空观和通感,是中国人接受大乘教义启发的直觉智慧于美感层面沟通诗与书画的内在联系。
诗文、书法和绘画原为彼此独立的文艺形式,宋元时期的士大夫文人在创作实践中把这几种文艺形式有机融为一体,相互辉映、相互补充——用诗歌抒发情感,在书法中感受风骨,于绘画里获得气韵生动的生命体验。以诗情和书法的笔意入画,完成了中国绘画的一次脱胎换骨转型,树立起文人画创作的新范式。从表现形式看,诗歌和书画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诗歌是运用语言的时间艺术,书画属于线条造型的空间艺术,一诉诸听觉,一诉诸视觉,但都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有限的文字和简单的笔墨线条,经过诗人与书画家的巧妙构思、精心营造,传递给观赏者的情意和美感,已经远远超出文字与画象之外。

诗书画“三位一体”
在创作中追求诗、书、画“三位一体”, 以诗为魂,以书立骨,是宋元时期文艺发展的主要方向。有无诗之意境,遂成为衡量书法和绘画艺术成就的基本要求。绘画与书法的不同之处在于,绘画不能完全脱离形似,而书法更重在表意,尤其是草书的笔走龙蛇,抒情写意的意味更浓。
元初诗书画“三绝”的代表人物赵孟頫在倡导“作画贵有古意”的同时,又创“书画同法”之说。受他影响的元代馆阁文人,将“书画本来同”的思想纳入可操作的法度层面,在书画关系中突出以书法为本位。与赵孟頫关系密切的“元四家”进行书法创作时,习惯于以诗歌为书写内容。他们痴情于书画艺术和“墨戏”创作,题写在画面上的文字,是蕴含文人高雅趣味的书法,更是意境优美的诗歌,进一步促进了诗学与书画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融通。
在诗画交融和书画一体的创作实践里,元代的诗人画家将文艺的社会功利性与书画的笔墨形式及气韵意态作了有效分离,以志在山林丘壑的从容、萧散,将淡泊、宁静的神情与自得、自适的美感融合为一体,表现性雅、情雅、气雅的审美趣味以及“古雅”之美。他们以骨法用笔作为切入点,将“书画本来同”和“书画同源”的思想,落实为便于操作的笔法和墨法,进一步实现了书法对绘画的深度渗透。作为诗书画“三绝”的典型,“元四家”以写代描,运用书法的笔墨技巧,将诗人的幽情和清高品格融入画中,作品具有形神兼备的生动气韵和荒寒清旷的意境,充分体现了元画的本色。如果说黄公望痴情于书画的墨戏,以天真萧散的笔墨显示心灵的澄明与解脱;那么,倪瓒则以逸笔草草的简淡笔墨,将诗与书画艺术的会通升华至清美绝俗的境界,似白云流天,如残雪在地,达到了逸品的极致。
综上,通过对有关“琴棋书画”的诗学文献加以认真梳理,不难发现诗与音乐和书画艺术会通的现象学研究之重要性在于:从士人“游于艺”的生活之艺术入手,便于明白时空交融的视听感受和生活体验所起的作用,揭示中国人特有的生命情调和审美取向;以琴诗、题画诗和论书诗为线索,对追求诗书画“三绝”的文艺思潮作历时性的考察,便于说明中国文学艺术的诗之意境与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诗与音乐书画彼此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分析,不仅可“还原”以琴棋书画为内容的游艺生活所蕴含的幽情壮采,还可上升到文艺思想和艺术哲学的层面进行意义阐释和理论总结。这对于中国文艺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诗学与书画艺术相融合的现象学研究”负责人、南开大学教授)
原标题:“琴棋书画”的文艺思想史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毅
声明: 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