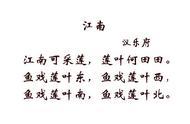“白日”自然是值得欢畅的,因为它会给人带来了阳光,送来温暖,使人们看见宇宙之生机,万物之华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白日不到的地方会是什么样子吗?而那里恰恰是苔绿生长的地方,对于这一点,白日一定是不自知的。清代的袁枚不愧是性灵派的一大师,仅以一首小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把“苔藓”生命骨子里的那种真性情给和盘脱出了,足以见得袁枚写景之作,模山范水,落想不凡,笔墨精致,妙从中来。任何一种东西都不是一切,只有自性才是一切的。白日之于白日,当然是一切,白日不到的地方,就不是一切。但它却可能是苔藓的一切,苔藓之于苔藓恰恰是白日不到之处的天堂。

世界上,凡是具体的、有形的、看得见的东西,总是有界限的,即使是白日也有它照不到的地方,而在它照不到的地方,一定还会有新的事物发生。正如一首歌的歌词所言,“白天不懂夜的黑。”而这种白日不到处与白日普照之间是不可说,不可知,不可道的。用老子的话讲,这也是“徼”与“妙”之关系,凡具体的、有形的、看得见的东西就是“缴”,而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如袁枚所说“白日不到处”,却正是“青春恰自来”的妙处所在。然而对于世人而言,却往往总是把目光投放在“白日所到处”,而对“白日不到处”却寞然处之,这恐怕是今人浮燥有余而幽妙不足的主要原因。正如《楞严经》所言,“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楞严经•卷三》)意思是是说,世上迷惑之人恰恰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总是以自然界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真理、为标准去衡量和区分世间的一切,而一旦这样做了,人就会完全蜕变成“现实之虫”,因为你太现实了,太用力了,太正确了,以至于正确到无以复加,没有一点纠错的余地了,这在理论上也许是对的,但是并没有真实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提出了“知白守黑”的理论,庄子提出了“和光同尘”的理论。

其实人有所不知的是,“汝宛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楞严经•卷三》),人的本性是清净的,空灵的,就象风的本性一样,虽然是空的,却是真实的存在,这种清净虚空之性遍及着整个现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种无区别的清净之潜为就藏在大自然之中的,它是要依托人的认识之心来得以呈现的。正如康德所认为的一样,一切都不是出于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恰恰相反,是客观事物依托人的感知而非认识得以呈现的。

为什么要依托感知而不是认知去把握这个世界呢,因为认知的本质是区分的,是区别的,是有界限的,它只能看到“白日”所及的地方,而无法理解“青春恰自来”的世界,感知则不然,感知不是用眼睛看,不是用耳朵听,不是用鼻子嗅,不是用舌头尝,不是用身体触,而是用自心本具,用现量境,用法身去感知世界,用老子的话就是以“天下式”去“知其白,守其黑。”这里的“式”就是法身、法则,就是在无我和离相中悟,正如古人悟道时有云:“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故欲本来面目全体显现,正须于不思不议一念不生之际,惺然自证。何谓“白”?白日所到之处即“白”寓昭然,明白;何谓“黑”?白日不到之处即“黑”,寓意暗昧,愚拙。成玄英曾解释说,“自显明白,昡曜于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韬光晦迹,退守暗味,不忤于物,故足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为修学之洪范也。”“知其白”,“白”即“白日”所及之处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意味着繁华、荣光、正确,显赫、竞争、富有、力量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好事,是盛世的标志,但它同时也可能带来骄、奢、侈、燥、淫、人格分裂等问题,这样在老子着来,也就离祸、害、灾、难不远了,因此老子告诚我们,在知白知荣的同时,切不要忘记还要守得住黑,守得住辱,要像天下的山谷一样,不要站在太高的地方,做到下而能容,虚而能纳。正如袁枚所描述的一样,“苔花如来小,也学牡丹开”,照样也不失其惊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