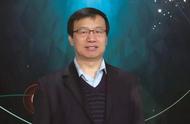行话,即“春典”,也有“唇典”一说。相声前辈张寿臣先生认为“唇典”更为准确。他讲“春”,实际指的是“相声”曲种,例如一名艺人既说相声又兼说评书,就被认为是“春、评两吃”。现在许多人把江湖“行话”都称为“春典”,可视为“约定俗成”之称。
在过去,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话”,但,各行各业的行话,又都不像江湖中的“行话”那么全面,那么能够涉及到生活、生意、思想、情感等众多方面。而且,江湖中的“行话”多达万余言,让其他行业的“行话”望尘莫及。当然,这一万余言的“春典”,相声界几乎无人全部知晓,他们也只是根据走江湖的需要,一般只能掌握百余言,多至几百言,而能会千言者为数不多。
对于行话的魅力,我也有切身体会:1965年,我15岁时,随团到河北省张家口的坝上演出。一天中午,我吃过饭后突然肚子疼痛。因下午就有演出,不能误场,怎么办呢?一位姓海的变魔术的老艺人,见我疼得大汗淋漓,便立即拉我出了剧场。剧场外面就是农村的庙会,他走到一个卖虫子药的(行话叫“挑肉汉儿的”)生意人跟前,先道“辛苦”,然后用江湖人所惯用的语言——“行话”,和卖虫子药的“盘道”。所谓“盘道”,就是江湖中人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以取得对方的认可。当时,我“行话”懂得不多,在他二人交谈中,我只听懂一句“要尖的”。“尖”,就是“真的”或“好的”的意思(有些“春典”是一词多解,如“尖”也表示“好看”、“漂亮”),不能给“腥”的,即“假的”,也不能是“半尖半腥”,即半真半假的。那个卖虫子药的“老合”,先摸了一下我的肚子,又看了看我的舌头,然后给了我一包药。海先生要给钱,他坚决不收。我到剧场后台喝了药,效果很好,顿时止痛。我对药的效力如此之好,虽然也感到神奇,但江湖中人之义气,“行话”之魅力,对我的吸引力则更大。由此,我便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时,曲艺团领导不许学员学“行话”,他们把“行话”叫“黑话”,因此,也绝不允许老师传授甚至讲解“黑话”。但从那时起,“行话”就一直吸引着我。现在我认为,旧社会所产生的“行话”,在当时,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作用。比如,陌生而又同是江湖中人的两个人见面,用“行话”交谈,就可以认定对方是否是“老合”,不但产生亲切感,而且还能互相帮助;再如,有一些不便当着观众或是其他人讲的语言,也可畅所欲言,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端和麻烦等。
还有,在旧社会,如不能掌握这些最基本的用语,就难于在江湖上生存。我可以举一实例:当年李润杰先生(快板书艺术的创造者,也说相声,后来拜焦少海为师;学说评书,拜师段荣华)流落东北,生活陷入困境,欲向一名以唱“数来宝”为手段进行要钱、讨饭的老乞丐学习演唱。不想,老乞丐说的是一嘴“春典”,可是他一概不知,莫名其妙。老乞丐方知他原来是一个“空(读kong)码儿”(春典,即不是江湖中人,地地道道的外行),当然就不会教他。也是因为希望自己多一名“麾下”,多一些收入,老乞丐让李润杰拜师。然而,李润杰为人耿直,不了解老乞丐的底细,便给予拒绝。而老乞丐认为不能让“空码儿”立足,于是一声令下,小乞丐们一拥而上,将李润杰一通暴打,然后轰出老乞丐的“管界”。以后他才明白,“闯江湖”必须会“春典”。
有人把“春典”视为“黑话”,对此,我认为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春典”毕竟是“避人双耳”,“使人不知”,这自然也就沾了一个“黑”字。不让行外人明明白白地听懂,这不是“黑话”又是什么?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黑话”也是如此。同是“黑话”,相声艺人运用了,与《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的“脸红什么?”“怎么又黄了?”等显然不一样,一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最起码的生活权利,而另一个维护的则是反动势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称“春典”也好,称“黑话”也罢,其实无所谓,关键是看为什么人服务。对于相声艺人来说,在恶劣的环境下讨生,就应该、也必须懂得一些”黑话”——“春典”。而“春典”的传授者是师父,或是出自同一师门之人,如师大爷、师叔、师哥等。其实,这也是行规之一,不拜门叩师是不能教授和学习“春典”的。只有会了一些“春典”的相声艺人才能跑码头,走江湖。
比如一场演出,场上的艺人在台上表演,该接他场的艺人未到,怎么办?“掌穴”的,即整场演出的负责人,就会告诉在台上表演的艺人“嗨点使”,或是“马后”,就是让艺人放开使活,说得长一点,好等未到的艺人;如“掌穴”的对台上的艺人说“蹶着点”,或是“马前”,意思就是可以少说一点段子中不必要的情节,缩短演出的时间,快一点。“嗨”是“春典”中“大”或“多”的意思;“蹶”是“春典”中“小”或“少”的意思。无论是“嗨点使”、“马后”,还是“蹶着点”、“马前”,如果让观众知道了,肯定不会满意的。可是又要照顾艺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只能使用“春典”进行交流。
再如,有能耐的艺人在什么场合演出什么段子,艺人要视观众的情况来决定。比如观众群文化层次较高,可以使“文哏活”,因为“包袱儿”容易抖响;如果青少年观众多,就应该使“皮儿薄”的段子。且不说艺人“撂地”,就是进了茶社、剧场演出,门外竖立的“水牌子”,即演出广告,报纸上登的广告,也只刊登艺人的名字,很少登演出的段子。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有经验的艺人在台侧或在台上,瞄上一眼台下的观众,就可知道观众的需要,并以此决定使哪块“活”。但在“逗限”的和“捧限”的商量演什么段子时,不能让外行听见,以防“泄密”。因此,有一些段子也有“春典”,像《黄鹤楼》叫“楼腿子”,《八扇屏》叫“张扇儿”,《俏皮话》叫“平缝儿”,《树没叶》叫“干枝子”,《大上寿》叫“罗口”,《空城计》叫“站门儿”,《地理图》叫“跑梁子”,《梦中婚》叫“晃亮子”,《白事会》叫“报出子”,《夸住宅》叫“谝窑儿”,《栓娃娃》叫“爬坡儿”,《相面》叫“戗盘儿”,《福寿全》叫“丧碟子”,《论捧逗》叫“张咧子”,《拉洋片》叫“把光子”,《窦公训女》叫“钻斗儿”,《学数来宝》叫“默梆子”……
也有另外的一种情况,“逗限”与“捧限”的在上场前不用商量,而是用“包袱儿”“问”观众,这里提到的“问”不是“春典”,所谓的“问”就是试探,试探观众吃什么样的“包袱儿”,知道之后再开始“使活”。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前场艺人说的段子,或是某个“包袱儿”,后边上场的艺人不知道,会出现重复使用的情况。这也没关系,后台管事的或是捡场的发现,马上会喊一句:“越了!”台下的观众根本听不懂,也就无所谓,而台上的演员立即就会改说别的段子。以上所说,都是视观众的情况来选择要说的段子,用“春典”说,叫“把点起春”,“点”就是观众,“春”就是相声段子。
台上的艺人在“使活”,忽然听见从后台传来“牐棚,摆金”这句话,那么艺人就得立马儿找相声的“底”,结束演出,鞠躬下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茶社、书场都是在艺人说过一个段子后,向观众敛钱。如听后台管事的一喊“牐棚,摆金”,就是告诉台上的艺人:“外面阴天(牐棚)了,要下雨(摆金)啦!”艺人就会快点结束,否则,如果打闪,闪后带着雷声,观众会“起堂”,即离开剧场。这样,钱也就敛不上来,节目就算白演啦。
有的“春典”,只是时代的产物。在今日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比如在江湖有“十大块”一说,就是十个字,即:神、鬼、妖、庙、塔、龙、虎、梦、桥、牙。这十个字,包括相声艺人在内的所有江湖中人,在中午12点以前都不能说,即使是同音字,也不行。如果一定要说,可用“春典”代替。如“龙”要说“嗨条子”;“虎”要说“嗨嘴子”;“兔”要说“月嘴子”;“梦”要说“黄粱子”;“桥”要说“悬梁子”;“牙”要说“柴”……在中午12点之前不能说的并不是只有这十个字,如:狱、更、兔、蛇、脚、雾等字,也是不能说的。江湖中人认为,说了这些字,就是犯了大忌,认为一天的生意会遭不测。于是便一天不出门,让犯忌者包赔一天损失,且又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即使是不会“春典”者或是在无意中说出了口,同样如此严厉对待。真是不可理解,如果认为鬼、妖、狱等字不吉利,可以不说。可是神、庙、龙应该是属于吉祥的字,为什么也不能说呢?对此,我曾向多位老艺人请教,但无人能给我以准确回答。看来已经无从考察。但此类“春典”含有封建迷信的色彩,绝对应该抛弃。
过去的相声艺人几乎没有不懂“春典”的,然而,“春典”并不是相声艺人所创,这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有关“春典”的记载,最早见于《康熙字典》,上有“春”一词。“春”本身就是一句“春典”。
“春典”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不能否认其发明者实为智者。且不说它所起到的作用,许多的“春典”在用词用字上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有意思。试举几个例子:
帽子叫“顶天儿”。全身的部位属头最高,而帽子还在头的上边,距离天最近。
鞋叫“踢土儿”。过去的路多为土路,鞋穿在脚上,当然要“踢土”。
袜子叫“熏筒儿”。因为袜子为筒状,又容易出不好的气味,所以叫“熏”。
裤子叫“蹬空子”。穿裤子肯定两条腿要“蹬空”。
挨打叫“蛇鞭”。因为有“鞭托”一说,即打人用鞭子,而鞭子就像是蛇。
大便叫“撇山”。撇就是丢弃,而过去极少坐便恭桶,多在茅房甚至在野地方便,抛出之物成堆形,如山状,将其丢掉,所以叫“撇山”。
少数观众退场叫“抽签儿”,如同算卦盛卦签儿所用的签儿桶,抽走一只就会少一只。大批观众退场叫“开闸”,就像是打开了闸门,水泻不止,当然会影响演出。......
仅这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春典”很有个琢磨劲儿,因为通俗易懂,容易理解,富有趣味,所以说“春典”是一种生动且又形象的语言。
是不是所有的“春典”都有根据,如上边举的例子一样呢?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一句“春典”都有一定的根据,绝非凭空而想。但可惜的是因为“春典”产生的时间较早,而大多数的艺人只是追求会说、会用,却不探询其来龙去脉,所以有一部分“春典”,已无法找出根据所在。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用“春典”说是:溜、月、汪、摘、中、申、行、掌、耐、居;小女孩用“春典”说是“抖花子”;小男孩用“春典”说是“怎科子”。其根据是什么,虽绞尽脑汁琢磨,却也不知其详。还有一些“春典”可以进行揣摩,比如姓赵的用“春典”说是“灯笼腕”,是不是因为走夜路要用灯笼照明,打灯笼的人都是走在最前边,而《百家姓》中的第一姓就是“赵”?还是因为灯笼能照明,取“照”和“赵”的谐音?姓唐的“春典”是“憨子腕”,是不是“唐”取“唐突”意,与“憨子”沾点儿边?姓王的“春典”是“虎头腕”,是不是因为虎是兽中之王?姓刘的“春典”是“顺水腕”,是取“刘”和“流”的同音,还是“顺水”比“流水”更吉祥呢?姓汤的是“浑水腕”,汤当然比清水要“浑”,可能是这个意思吧?饿了的“春典”是“瓤”,而“瓤”是各种瓜的中心部位,“瓤”又是空的,是不是以此寓意肚子已空?如果,这几个“春典”的推理、判断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大多的“春典”就可以找出根据了。如管“外行人”,叫“空码儿”;“官”叫“翅子”;“打官司”叫“朝翅子”;“衣服”叫“撒托”;“下雨了”叫“摆金”;“下雪”叫“摆银”;“解小便”叫“摆柳儿”;“哭”叫“撇苏儿”;“走”叫“撬”;“吃饭”叫“上啃”;“演出脚本”叫“册(读cai)子”;“快一点”叫“马前”;“慢一点”叫“马后”;“茶馆”叫“牙淋窑儿”;“马”叫“风子”;“牛”叫“岔子”;“正合适”叫“对托”……
有些“春典”实在难以找到根据,所以,把一些“春典”写成文字,只能取其音,而不能取其意了。还以一、二、三、四、五……为例,写成文字是:溜、月、汪、摘、中……对吗?对。如果写成的文字是:遛、悦、枉、寨、钟……对吗?也对。
一些个别的“春典”,具有多意性,就是说一个“春典”代表两个、甚至更多的意思。比如“尖”,可以解释为“好”,其他的像“真的”、“真实”、“漂亮”、“好看”等也可以说是“尖”。再如“念”,就是“不好”的意思,还可以“翻译”成“没有”、“差”等。
有时“春典”会组合使用,比如“捂杵”,就是由两个“春典”组成,“捂”(读wu)就是“不说”的意思,“杵”就是“钱”,“捂杵”组合在一起,也就是“拿到钱不说出来”。“捂杵”多指“穴头”所为,在暗中得利,用行话说也叫“使黑杵”。
今日,一些个别的“春典”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用语,为大众所熟知,如“走穴”、“穴头”、“大腕儿”等。作为一种行业保护的手段,“春典”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作为艺人之间的交流手段,“春典”也起到了江湖中人相互帮助的作用。如艺人在“走穴”中,遇到困难、问题、麻烦,不管双方是否认识,只要用行话进行交流,就立即能得到关照。
来源: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共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兼秘书长孙福海《逗你没商量:相声界奇闻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