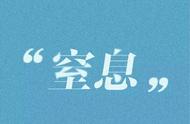“不管我怎么做都会觉得自惭形秽,我每时每刻都感到不安,感到忐忑,以至于无处可容。”
尼采认为:对于人生本质的虚无性的认识,很容易使人们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禁欲和厌世,二是极端的世俗化。
直治的虚无让他难以面对真实的生活,于是他开始走向极端,用放浪形骸抗争虚无。但是越挣扎却变得越“粗俗又下流”,他认为自己的堕落可以换来平民的友情,也不过是得到了自己臆想中的,被世人抛弃的结局。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在《禁闭》之中,曾写下关于四个人的魂灵坠入地狱后的故事。那个地狱中没有预想的酷刑,只有一间封闭的密室关着他们。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要在别人在场的情况之下进行,所有人都妄图在别人的眼光中寻找自我。渐渐的,四个人开始痛苦,但这里刀子*不死人,而这种痛苦就是地狱般的痛苦。
同样的,战后的日本宛如地狱,新旧交替下,直治对自己曾经的贵族出身感到羞愧,他想从世人的身上找寻自我的价值,但他却融入不了平民的生活,他认为世人都在嘲笑他曾经的身份,所以别人的目光便成为了他口中的地狱。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萨特
“请你相信:不管我怎么娱玩,我从未真正觉得快乐,也许在快乐这方面我是个“阳痿”者。我只不过想甩开自己这个贵族的影子,才发狂、才拼命作乐、才放纵不羁的。”
直治这个角色带有许多太宰治的颓废身影,因为他们同样身为没落的贵族,同样面对身份的转换。当理想照进现实,他们看到的是满目疮痍,这样的心理落差使得他们绝望,所以他才会使直治的世界里处处充斥着“死亡”与“罪恶”。
可以说,直治是太宰治笔下无赖派文学的集中体现,折射出当时社会中成批的绝望人群。他们不满社会现实,同时又需要被人肯定,渴望被赋予价值。
但他们不会像母亲那样选择优雅接受,也没有像和子一样选择同命运抗争,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虚无与幻灭,从而最后走向自我毁灭的地步。
优雅的母亲,从疾病到死亡,代表着日本贵族没落的必然性“她才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啊,她身上有些东西是谁都学不来的。”
书中对于母亲的着笔尽是溢于言表的赞美之情。她一直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就连简单的喝汤也是“轻敏地”将汤匙送进娇小的双唇之间。并且,无论何时都不曾言辞激烈,甚至不曾对人颐指气使过。即使当女儿和子不小心烧着了柴火,差点造成火灾之时,她也是柔声安慰: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嘛,柴火本来就是用来烧的呀。”

太宰治之所以这样描写母亲,无疑是把心中的完美母亲形象寄托在了书中的母亲身上。
由于母亲身体的原因,太宰治自便被寄养在叔母的家中。所以,对于母亲,对于母爱,他的心中一直颇有遗憾。于是在写作中,太宰治便把对“母亲”的向往具象化,刻画出《斜阳》中这位理想的母亲形象。
然而他笔下这位——从头到尾都是从容美丽、轻巧而又恬淡的贵妇人,却在家产变卖后开始疾病缠身,日渐衰败。
因为从始至终,母亲对于这样的身份转换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矛盾心理。她表面上假装幸福,其实内心日日受疾病折磨,殚精竭虑。
她一辈子与世无争,无怨无恨,虽然美丽但却仍旧没有逃过死亡的厄运,就好像滚滚而来的历史大潮一样,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母亲的疾病与衰老,暗示的便是当下社会贵族的没落与新秩序的即将建立,而后的死亡则透露出,新旧社会转换的必然性。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病呢,这是神灵召唤我死去然后再让我重生,并且把我变成跟昨天不同的另一个人哪。”
所以,即使是母亲在离世之前的场景,也是充满了温馨的暖黄色调。太宰治用“双颊像蜡一样光滑,薄薄的双唇好像仍含着微笑。”来描写死去的母亲。
他用“圣殇中的圣母玛丽亚”展现着内心隐约对新秩序的期盼,用“日本最后的贵妇人,美丽的母亲走了”来象征贵族的没落与终结,暗含着太宰治对家国命运的担忧,也展现出了社会中那些对未来充满恐惧,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人们。
他们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虽然适应不了新的生活。但是,与其腐烂,他们仍旧选择美丽而又体面地接受旧制度的死去与新制度的到来。

“我愿意相信:人正是为了恋爱和革命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和子这个角色,与以往太宰治书中的女性形象一样,有着乐观坚强的心。虽然身处封建社会她没有选择的权利,;面对丈夫的诬陷,她没有辩驳的权利;面对孩子的胎死腹中,她没有悲伤的权利。但是自从家族的没落,她开始有了选择的权利,她凭借自己的独立和勤快,做起了农活。
与优雅又不安的母亲和颓废又绝望的直治不同,和子心中带着这份乐观与坚强,快速的适应了这个转变。劳动给她带来了充实,即使穿上廉价的胶底短布袜也觉得轻松与愉快,这对于和子来说,是战争中唯一快乐的回忆。她虽然曾经也虚无与迷茫,但是仍旧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她认为:日子再苦,也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无论如何,从今往后,我必须振作起来,好好地过日子才行。”
再加上直治的老师上原曾经的恶作剧似的吻,和子心中开始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她开始萌生了反抗命运的心理,她想与旧的社会道德宣战以重获新生。
于是,和子开始追求有妇之夫的无赖——上原。这种被看作道德败坏的事情,是她对抗世界的方式。
“我喜欢坏蛋,而且喜欢臭名远扬的坏蛋。我也想做一个臭名远扬的坏蛋呢。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没有别的生存方式。”
太宰治之所以用这样的“道德败坏”的形式来体现,我想其中原因便是当时的社会秩序重新洗牌,如直治一般憎恶生活的人不在少数,而他们又如直治一般只是空有期盼,却不做出任何的努力,同时还利用道德去束缚他人。
只有和子不同,她只是想好好的活着。
“那些毫无痛苦感受的旁观者,一面卑鄙地无精打采地偃憩他们的帆,一面却就这问题进行所谓的批判,真是荒谬至极。”
虽然新旧交替的社会道德下,作为女性的她仍旧没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心中的秘密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因为她知道只有冲破旧的才会迎来新生。所以,在母亲去世的那天,和子意识到旧的传统已经死去,她必须生存下去,必须与这个世间残存的旧道德抗争下去。
尽管和子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仍旧有太多的人力所不及,有太多的险恶,但她的心中有追求和渴望,这些就够了。
我们可以看出,太宰治想要借着和子的口吻,去抨击那些自甘堕落的同时又用着世俗的道德批判他人的人。
他在和子身上寄托了新生的美好向往,这也与太宰治自小生活在一个女性众多的家庭中有很大关系。女性的围绕式成长,使得他一直对她们有着近乎于信仰的特殊情感,所以他才会通过描写女性的心理转变,来讴歌和子的顽强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