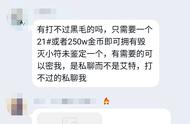■ 张家鸿
一个人与一本书的遇见,可以是迸发火花的某个瞬间,一闪即逝;也可以是长久的相知相守甚至相濡以沫,如张新颖这般。唯其如此,他才能写出这本虽薄却厚的《漫长相遇:书和成长的故事》。
与阅读相伴相随的是成长,尽管张新颖笔下并不明言,然而,把一本本书串联起来,串成的就是一条清晰可见的成长线路。《约翰·克里斯多夫》《喧哗与躁动》《围城》《夏洛的网》《渴望生活》《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单向街》……阅读所处的某个时间点,就是成长的紧要处。心灵被书香濡染,被书籍中某些句子撞击后产生的颤动,对张新颖来讲,是难以忘怀的点滴美好。
读初二时,在教室前面的书摊上,他买到钱锺书的《围城》,小说语言对他来讲“奇异而新鲜,有时甚至是震动”,吸引着他从头读到尾。高考结束后,他从低一年级的女生处借来包着书衣的《战争与和平》——“这个悠长的夏天,因为这部伟大的著作而显现出以前未曾感受到的辽阔和深邃,涌动不息又踏实沉静。”这部书的阅读,成为张新颖告别高中岁月的标志性事件。在大学宿舍上铺的蚊帐里,他读欧文·斯通撰写的梵高传记《渴望生活》,读得无法停下,读完时天已亮了。1992年夏天,当了记者的他接过贾植芳先生赠予的《人之子》英文本,这本十四五万字左右、出自德国传记名家爱米尔·路德维希之手的著作,张新颖花去一年半时间,在工作之余译出。
书中所写的与某些经典作品的缘分,抑或因它们而牵扯出的事件,不止以上那些。列举顺序不必完全按照时间早晚,打乱顺序也许更能看出书籍在其生活中的无处不在,阅读在其人生许多阶段里的影响深远。在《经典,把现在的噪音调成背景轻音》中,张新颖写道:“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找到成长的位置,确认书籍因之而在。寻觅书香,倾听心跳,仿佛可快速返回当年。这是张新颖在整本书里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他在写作时一再提醒自己的事情。这,何尝不是他在寻找那个或许已经消失却真切存在过的自我?
这些美好,是经典给予读者的光照。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给过无数人光照,在不同的时空里,蒙受过经典光照的无数人,成长为他们应当长成的模样。书籍濡染带来的有心灵上的质地转变,亦有容颜上的悄然转化。黄庭坚所言,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虽有夸张之嫌,却并非全无道理。
这些美好,也是《漫长相遇》的书香之源。被许多经典陶冶过,并且把这种感觉、这段经历,经由自己的笔触传递给许多素未谋面的读者。书中,一定站立着一个“我”,从年少轻狂到年长稳重,从未经世事到历经沧桑,“我”被书成全,亦成为最了解书籍的那个人。如此说来,把《漫长相遇》视作别样的传记亦可,一部以阅读为主线、书籍与自我互为主角的传记。
回忆会自动过滤。许多书在字里行间被提及,但更多的书籍则被忽略,原因不一。未被书写的这本书与那本书,以及许多许多的书,共同参与过张新颖生命的建造。它们不是不存在。写下来,是郑重的纪念;不曾写,是无言的缅怀。张新颖评价汪家明《难忘的书和插图》时所写的一段话,亦适用于他本人:“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阅读,不仅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过去的经验,还可能在成长过程中被吸收、消化,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现在的一部分。”更何况,阅读带来的影响,何止是青少年时代呢?那是漫长一生说不尽道不完的事。起初的起初,遇见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他根本读不下去,连第一部分都没能读完。后来的后来,他再遇该书的新译本,一读之下,竟不忍释卷。差别如此大的阅读体验,令他深深自省:“年轻时候企羡炫目的天才,哪里有耐心体会平实生活的滋味?”从无缘、遗弃到沉浸、热爱,站在两端的是同一个张新颖,也是两个不同的张新颖。
身为现代文学学者的张新颖,骨子里是个虔诚、恳切的读者。张新颖之爱书是当然的,然而表述时他常常欲言又止,抑或点到为止,不让情感溢出。这反而给人愈加丰富、宽广的想象空间。“漫长”是对过去的总结,其中有欣欣然的满足与感恩;也是对自我未来的期许,不需要力量来支撑,不需要热爱来鼓舞,只需如过往一样继续伴着随着读着乐着即可。张新颖说:“许多年之后,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读过的书,可是它已经把种子留在了我们身上,它持续地在我们身上起作用,虽然我们未必意识得到。”持续的作用,看的不是现在,眼光所向的是未来,甚至未来的未来。那么当下呢?且尽情享受书香带来的愉悦吧。
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