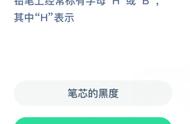无常鬼终于出场,于“夜深”时分;看客心情愈加“起劲”。先看见“无常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本来是挂在台角上的,这时预先拿进去了”;
再听见声音“鬼物所爱听的喇叭似的特别乐器,目连瞎头”响起来了。
无常的服饰比画上的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朱唇粉面,如漆眉黑,紧蹙着,看不出是笑还是哭。一出场就打了一百零八个嚏,同时放了一百零八个屁,然后自述他的履历。
这是全文中最鲜亮的一笔,让观众也“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使无常的形象变得丰厚而耐人寻味。至于“一百零八个”嚏和屁,自然是民间文学中惯有的夸饰之词,我们读者也仿佛听见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哄堂大笑……。

然后,直接引用无常的一段唱词,这既是戏剧演出的一个高潮,也把全文引向高潮。这位阴间之鬼竟是这样的有人情味:堂房的阿侄突然生病,刚吃下药,而且是本地最有名的郎中开出的药,就“冷汗发出”,“两脚笔直”,看阿嫂哭得悲伤,不禁善心大发,放他“还阳半刻”。不料“大王道我是得钱买放”,开了后门,“就将我捆打四十”。阎罗老子居然误解了自己的
“人格,不,鬼格”,无端的惩罚“
这真是神来之笔!看似随和的无常突然翻转出刚毅坚定的一面,诙谐中显示出严峻,这是能给读者以一种震撼的。更可以想见,当在人间,面对“皇亲国戚”肆无忌惮地徇私舞弊而无可奈何的普通老百姓,突然在无常这里看到了抵御腐败、不平等的“铜墙铁壁”,顿会产生一种“若获知音”之感:他的所言所为正是表达了底层民众的愿望。
总结鲁迅情不自禁地说:“一切鬼魂中,就是他有点人情;我们不变鬼则已,如果要变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较地相亲近。”并且满怀深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至今还确凿地记得,与故乡的“下等人”一样,常常高兴地正视过这半鬼半人、有理有情,可怖又不缺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和笑,口头的硬语与诙谐。

这是全文的一个“核心”所在:前面所有的描述,议论,铺垫,都最后归结于此。这里,对无常的形象所做的总结、概括,自然把读者对无常的认识提升了一步,让我们关注“鬼”中之“人”及“鬼”所保留的“理而情”的理想“人性”;而“至今还确凿地记得”这样的强调,则提醒读者注意埋在鲁迅心灵深处的永恒记忆:“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怎样与无常鬼同哭同笑……”
这意味着,鲁迅从童年起,就有了与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民间想象物融合无间的生命体验,这是他的生命之根,也是他的文学之根。
鲁迅先生的讽刺文章,可谓是“入木三分”,而且是反话正说,没有深入了解背景的读者,是很难读懂鲁迅先生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