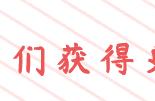在如今的韩国社会,“未来”二字正给年轻人带来巨大的不安和忧虑。
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中,目标单一的残酷竞争正在成为所谓的“模范人生”。比起质疑一生只能被“高考”这一准则“审判”的评价体系,他们更热衷于将学历歧视扩大再生产。各大书店常年占据销量榜首的是一系列成功学书籍,他们明明已经因极端的自我管理饱受煎熬,却还是会为了得到一点渺茫的竞争优势而不放过任何歧视他人的机会。到底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一现象引起了韩国一线社会学教师吴赞镐的注意。他曾辗转于韩国多所大学做讲师,对当下的韩国大学生群体进行过多次深入访谈,并以此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通过近距离观察韩国的大学生群体,吴赞镐发现这些年轻人其实既是不合理社会结构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更是维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帮凶。
近日,基于其博士论文的新书《“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中文版出版。总体来说,这本书到结尾也没能对这一现象提出相应的解法,但书中细致呈现的案例还是抛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东亚教育模式僵化的另一面。下文经出版方授权刊发,摘编自书中第三章“变成怪物的年轻人的自画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较原文有删减,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韩]吴赞镐

《“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韩]吴赞镐 著,六一 译,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学历等级化秩序的过度执着,显然与过去单纯的学历主义至上不同。过去韩国社会的学历主义,是通过特定权力发挥作用的学阀问题,首尔大学等少数名牌大学以学阀为基础垄断社会要职的严重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学阀的概念常与韩国社会集体文化的关键词——共同体性、亲缘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对以共同体性为基础存在的“过去式“学阀来说,隶属某个群体带来的积极效果存在于未来,因此,他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顺应该群体的规则为前提。只凭同门关系就能实现互帮互助,是因为该大学的大部分毕业生都能成功就业,因为没有必要视其为竞争者,所以才能与其成为肩并肩的同伴。
但是,如今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就选择联手,“校友要互帮互助”在自我开发意识固化的今天,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我先活下来”才是首要目标。他们也没有帮助同门的余力,何况现在也不是凭学校名字就能轻松解决就业的时代了。因此,凭同门这一个条件就能聚集起来的学阀概念,就相对地淡化了。

韩剧《天空之城》(2016)剧照。
即便如此,学历主义和学阀主义也不可能完全消失。虽然一个学校名字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但作为凸显自己的特别、“推挤”他人的战略还是十分有用的。这一战略很周密,并不是盲目的歧视,而是会拿出“客观上那个人能力不如我”的论据,实际上是在强烈主张学力(在此学力被扩大理解为全方面的能力)上的差异。正如上文的例子,他们不仅不会因为是同门就抱团(不是说抱团就是正确的),甚至在同一所学校内还要用“高考分数=客观学力”的逻辑与他人划清界限。
过去,“学阀”一词蕴含着共同体的含义,而在这一点上,学历等级主义是相反的——以守护现有排名的方式,要求社会认同“学力客观差异”。尤其是在大学教育普及的今天,光是考上大学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所以大学生执着于守护自己所在位置的小小优势,蔑视哪怕只比自己低一点点的人,并且无法忍受地位被动摇。
在这里还有一点微妙的不同。过去在学阀主义的“炫耀”中,一般会产生这样的对比——首尔大学vs非首尔大学、名牌大学vs非名牌大学、“首尔圈”大学vs地方大学……在这里,学阀讨论的核心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有批判性意味;但在用来“蔑视”的学历等级主义中,被关注的往往是排名更低的大学学生,问题从“谁在炫耀”变成了“谁被蔑视”。

韩国纪录片《学习的背叛》(2016)画面。
其实从这个不同点里最能看出现在的年轻人是以什么姿态生存于社会上——被蔑视的受害者有时也会成为蔑视的加害者,蔑视的连锁反应一直持续到最底层。对于被蔑视的一方是否就不会蔑视他人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学生能独善其身。
综上所述,现在大学生的思考方式是将高考分数的差距扩大理解为所有能力的差距。更讽刺的是,比起抗议处于“更高处”的学生蔑视自己,他们更倾向于去蔑视处于“更低处”的其他学生,蔑视他人的行为就这样逐渐被合理化了。我见过的大部分学生,不管是不是名牌大学的,都认为上述行为是正当的。
都说现在的社会是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个人通过消费来体现自己的等级。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因学历感到自卑或优越的样子,简直和为购买廉价品而羞愧、为得到名牌而骄傲的现代人消费心理如出一辙。一名西江大学的学生吐露了他在高考分数带来的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徘徊的心情。
首先,面试官会查看简历确认面试者的学校,神奇的是,如果和我一起面试的都是录取分数低的学校的学生,我就会变得很从容,面试的时候也很有自信,还能开一些幽默的玩笑。然而,有一次一起面试的都是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的学生,只有我是西江大学的,我就开始变得焦虑紧张,想着如果失误了怎么办,结果最后真的面试失败了。
看上去这位学生的面试状态在从容和紧张之间转换得十分自然,但这其实根本不是他自控的结果。因为根据当下的情况产生什么样的感情,是早已训练好了的。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下胆怯畏缩,什么情况下从容不迫,这充分说明了他们正处于一种被追赶的不安状态。
如果只是因骄傲而歧视他人,就应该止于炫耀,而他们在炫耀后,一定会对歧视对象进行排挤,只为拼死守护自己也不知何时会被推挤下去的位置。别说团结起来改变社会了,他们自己先陷入了无用的“蜗角之争”。盲目相信自我开发逻辑的大学生被推上“蜗角之争”的战场,又不得不依附于这个战场,无法脱身。
想象一下蜗牛的两只触角互相争斗的场面吧,谁看了都会觉得索然无趣。人们经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争斗,实际上这些争斗大多是脱离了本质的消耗战。在这个充满问题的社会中,他们变得更幸福了吗?社会问题还在不断积累,不过徒增了牺牲者。个人靠着仅有的一丝希望,用冰冷的竞争法则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对本质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站在蜗牛的角上,进行无谓的争斗。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一现象正在无比自然地循环着。大学生A遭到了录取分数线没比自己大学高几分的某大学学生的歧视,十分生气,为了稀释这种受害意识,A觉得必须说明自己的情况是特殊的,于是他开始努力寻找大学毕业以后的出路。如果能找到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就可以洗掉至今为止的屈辱,所以他要努力提高学分、考各种资格证,积累所谓的履历,做着卧薪尝胆的梦。“我虽然现在上着这么个大学,但是我一定要找个好工作,证明高考的分数不是我真正的实力!”就这样,他人的蔑视成了大学生A卧薪尝胆的兴奋剂,虽然这一动力的源头还是自卑感。
然而,只有A在卧薪尝胆吗?A曾经蔑视的某个人也会同样地下定决心要打败A。看到爬上来的其他人,A的优越感又带来刺激,“我不能输给那个家伙!”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想要绝对坚守自己的位置,无论如何都不能掉下去。
就这样,所有人都为了克服被蔑视(自卑感),维持蔑视(优越感)埋头努力地积累履历。这些履历是通过严格的自我控制式自我开发才能取得的东西,年轻人自我开发循环的起点就在这里。这就是压得他们无法喘息,只能盯着前面一直跑的生存法则,也是他们不得不往前奔跑的理由。
现实就是这么扭曲,在这个扭曲的社会里,大学生也正在成为扭曲的人。所以,对在歧视中活得很艰难的年轻人,我们不该再说“要想战胜那些委屈,一定要努力自我开发”这样的话,这样是绝对无法把他们从蜗牛的角上拽下来的。
所有大学正在
逐渐“工商管理化”
未来希望渺茫的原因,和变化的大学环境也有很大关系。现在韩国的大学致力于将年轻人培养成更完美的资本主义商品,大学逐渐企业化,甚至只根据就业率的高低来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文体类专业首当其冲,连研究韩国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国文系都难以幸免。
斗山重工业会长兼中央大学理事长朴容晟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大学是素质教育的平台,是学问的殿堂’这种唬人的话已经过时了,要承认,现在的大学就是‘职业教育所’。”
这话虽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确实存在这样的趋势。现在大学的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训练有素的公司职员”,因为只有成为这样的大学,才有希望从企业手里拿到一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