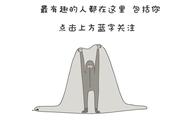冒襄在《影梅庵忆语》记载,他的小妾董小宛(明末秦淮八艳)“秋来犹耽晚菊”,“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足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淡秀如画。”人坐菊中,人菊俱在烛影摇红中,别说眼见,想一想“人比黄花瘦”,这美色醉人心!
《浮生六记》里的沈复与芸娘,“惟每年篱东菊绽”,“喜摘插瓶”。“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花取参差,间以花蕊,以免飞钹耍盘之病”。“视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则眉目不分”,“必须参差高下互相照应,以气势联络为上”,“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这一段描写,濡染诗意又充满灵气。他们夫妻“琴瑟和鸣”、情笃和好;生活经历却很惨。对菊的喜爱诉诸于笔端,是如此旖旎多情。菊,陶冶了他们的心性,滋养了他们的人生。崇韵致,尚清雅,偏爱旁逸斜出之趣,这是一种诗意,风流不羁、高雅脱俗。为苦涩日子增添了一份美好气息,透出一缕温暖光辉。

董小宛、沈复与芸娘都是现实中的人,而蒲松龄的《黄英》写了一个“菊花精”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马子才“世好菊,至才尤甚。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他爱菊花如痴如醉,因而菊花精陶氏姐弟主动制造了“偶遇”。因陶渊明是当之无愧的“菊花代言人”,故而蒲松龄便给菊花精取姓陶,姐弟俩一名三郎一名黄英。“黄英”就是菊花,“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照应的正好是菊花的高洁和美丽。马子才种菊是一种精神娱乐,与孔方兄无关,否则就“有辱黄花矣”。
马子才丧妻后娶了黄英,他认为黄英卖菊致富亵渎了“东篱”,便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把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黄英赞扬陶渊明的爱菊之心,也喜爱高洁的花中魅力。后来三郎醉酒丧生,在黄英的精心培育下,成为有名的酒菊——醉陶。他本为菊精,化身为菊,还为本身,很是感人。

对菊花的赞美,较早的见之于屈原的《离*》: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寒秋里绽放的菊花谢绝繁华,回归简朴。
丛菊如有情,幽芳慰孤介。
——宋·欧阳修《秋晚凝翠亭》
菊之气节:孤高绝俗,耿介赤诚;菊之姿容:清瘦纤细,傲然独立;菊之幽香:浓而不扬,淡而超逸。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
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
——唐·李商隐《菊花》
恰恰是这即无绝色又无奇香的菊花,在天寒地冻之际。
沽来新酿经秋醉,开尽寒花未出门。
——清·张光启《对菊》
不随俗媚时,不趋炎附势。淡淡绽开在秋风之中,填补寒秋的缺憾和失落,着实令人敬佩。

林黛玉《咏菊》诗云:
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古诗人不吝啬用最美的语言赞美菊花。凉风起,雁南飞,菊花黄,芦花白。
颜色只从霜后好,不知人世有春风。
——清·许廷荣《题画菊》
这被喻为花中四君子的菊花,便在古诗词里凌寒绽放。
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
——唐·白居易《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
细细品味,每枝菊都在讲述着一段曲折的故事,每朵菊都在展示着一份独特的情趣。
煌煌丹菊,暮秋弥荣。
——晋·嵇含《菊花铭》
庭院有菊堪观,案头有诗可读,穿越时空的缕缕幽幽菊香,扑面而来。在赏菊、访菊、对菊、问菊、簪菊中,把一盏清茗,去古诗文里赴一场菊花之约,远离尘嚣,平静安谧,足矣……
-作者-
朱少华,莒南县人,中学高级教师。喜欢写作。教学论文、散文随笔、诗歌、剪纸等作品,散见多家报刊及网络平台。在征文及网络文学作品大赛中多次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