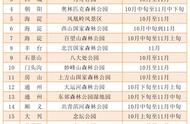1870年,朝阳门迤南的内城东垣外壁,护城河两岸
“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感觉冷。那种高兴劲儿,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感”。孔庆普说,在阜成门城楼上拍照是“特级享受”。
特级享受的前提是呕心沥血。孔庆普在修缮阜成门时的确下了大工夫。城楼二层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缮的项目也最多。他先后请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几位老木匠,才逐步复原出格扇门、木楼板和它的对接方式。
“质量合格,可以报竣工”,检查评语写完后,孔庆普的喜悦难以言表,索性乘兴写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他有个习惯,考察一座古桥,修缮一座城楼,就写一首诗,只为纪实。但从1952年起,纪实诗在本子里渐渐少了。
“我修的,又让我拆”
1951年底,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不来。当时的孔庆普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与此同时,从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担北京城运输任务的骆驼,50年代在城门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铁作为新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1953年开始规划。这些变迁具体落实到孔庆普身上时,他接到“城楼修缮工程”变成拆迁命令的通知。

运煤的骆驼,曾是北京城外西侧、为国外摄影者钟情的一景。
“谁都不想拆。”在孔庆普的记忆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从技术工人到老局长,再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都对刘少奇的这一指示不理解。此前,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在城门一边或两边开辟豁口或修建门洞,是曾参与城楼修缮工程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所有人又无可奈何,“拆”这个大字还是层层传达了下来。这次,孔庆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从西便门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关系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庆普根据现存城楼的规模,制定了一项在绝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门被列入倒数第二年,东直门城楼和希望保留下来的是西直门整座城门列在最后。

1921年,西直门南面全貌及绕过瓮城向南流的内城西护城河被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下。“文革”期间,这座被孔庆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楼也被误拆。
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再写过纪实诗。直到拆到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再记。“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孔庆普笔记本上的测绘图
就这样,在命运反复的煎熬中,孔庆普历练成为一位功夫扎实的技术专家。“文革”期间,他因专业技术过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单士元。而单士元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
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躲过一劫。
城事无尽,追忆未完
“至少说明我的技术过硬”,而今,89岁的孔庆普回忆那段时光,于苦难之中有达观。从单士元接过资料后,他先后撰写《北京志·桥梁志》《北京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专著。
本来也有机会在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的。“文革”后,圆明园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圆明园建设工程处”,要寻一位高级工程人员。文物局推荐孔庆普,说“孔工办事特别认真。找他做事,保准工程做得好”。对方一听“认真”,便找了别人。1992年,丰台区世界公园也请孔庆普当顾问,“只要签字,上不上班无所谓”。孔庆普没去,“不让我认真,我不干”。
他的认真不太受欢迎。北京各个区都希望“旧地重修”古建筑,孔庆普也被邀请看过“6项古都标志物”等计划。“假的”,他态度坚定。但凡位置移了,就不是他认可的城楼,更不必说那些附会出来的“旧地”。早几年,他还会应邀写《真正的天桥》《真正的燕翅楼》等文章,但随着各区文保工作与政绩挂钩,报刊、杂志也不好再发。
孔庆普倒也乐得自在。每天起早遛弯,上午敲电脑写书,下午练练书法。他脑子里还有城和事,要继续掏,就在他不大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