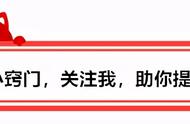《夏承焘日记全编》出版,赵荣光(左二,游先生弟子)、吴蓓(左三)和路伟(右一)带着日记拜访游修龄(左一)
游老对很多往事都记不太清了,只有一件事,他重复讲了好几遍。
我这个人,欢喜音乐,会拉二胡,也想学小提琴,就攒钱买一把。他(姐夫夏承焘)在上海,我托人把钞票寄给他。后来,钱退回来了,因为还差两三块银元,最后没有买,我后来就改学二胡,二胡便宜。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一两年,有一天,我在家里拉二胡,他来了。我因为思想很集中,不知道有人来了,他也不响,在旁边听。
拉完后,他才说话——非常抱歉。
我听不懂,什么抱歉?
小提琴还差几块钱,没有买成。
1947年,夏承焘在日记里写,七八年前,他在上海,修龄托他买一把小提琴,已经物色好了,但是,“以无弓弦遂迟疑放过,使修龄不能成此艺,实由予一念蹉跎之过。平生最爱戴东原‘持躬守不苟二字,对人守无憾二字’两语,不谓躬蹈有憾之悔,思之疚歉。”
80多年过去了,一切没有消逝。
1950年3月4日,夏承焘写:阅《克利斯朵夫》有感,成《挽歌》一首,写如下。修龄为予添两活字,甚好:
你并没有死,不过更换了一个位置。从前活在我的眼前,现在活在我的心里。
2.
夏承焘的原配叫游淑昭。
日记里记载的淑昭,身体弱,多是生病。“得淑昭四月初一日书,谓头痛、脚痛未愈,念念不已。”“淑昭居游家养病将一月,未愈。”

1940年,之江大学友生饯行夏承焘、游淑昭于上海市楼
1971年7月24日-1972年3月25日的日记,目前没有找到,但在5个月后续接的日记中,妻子已逝。
〔八月八日〕夕梦与淑昭泛舟,逝后此为第一次入梦。
他想把淑昭葬于西湖边。1973年1月9日,收到妻舅游止水的信,说淑昭的骨灰邮寄不郑重,“几人能得葬西湖,但风景区不许葬,可较远离。即作复函,告周年纪念延至明正,予体尚未复原,不能远行。”
2017年,吴无闻(常用名吴闻,原名吴无闻)之子吴常云告诉上海《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母亲于1972年退休后赴杭州,断然与当时单身一人的老师夏老喜结连理。”
1973年,55岁的吴无闻要和73岁的夏承焘结婚,日子选在“六一”儿童节。
吴无闻是《文汇报》记者,也是一位女词人。关于两人之间的交往,读一读郑重的文字:
1972年,吴闻还在报社的零印车间劳动,一位温州的同乡路过上海,向她谈到夏承焘的游夫人已经去世,一个人过着孤苦生活。吴闻听了之后,随即向报社请假去杭州看他。夏承焘和吴闻不只是有师生之情,词心相通,还有着通家之谊,吴闻的哥哥吴鹭山,擅长诗词,和夏承焘有着兰禊之交。这样吴、夏之间又多了一层兄妹之情。吴闻就以小妹、学生、词友多重身份和夏承焘相恋,以词传情,夏承焘向她寄上《减字木兰花》:
左班兄妹,风谊平生朝世世。风露何年,湖月湖船得并肩。
一灯乐苑,相照心光同缱绻。待学吹箫,无琢新词过六桥。

夏承焘和吴无闻合影
1974年12月1日至1975年11月11日的日记,夏承焘写在小开本笔记本上。横格,每页二十行。红色塑胶封套。扉页题:“朝阳楼(一)”“自杭州赴北京,75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京。”首页钤有“吴闻”白文印。
晚年,夏承焘住在北京,记性下降,1973年5月17日后的日记,皆由吴无闻代笔,直到夏承焘去世,她一直为他做旧稿的整理与出版诸事宜。
因此,早年和晚年日记内容,完全不同,但看日记稿本,两人的字几乎完全一样,从字迹上基本上辨不出来,都学的黄道周。
1917年,夏承焘17岁的日记,写在民国线装老纸抄本上,吴无闻在晚年重编时命名为“儿时日记”。

1917年“儿时日记”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