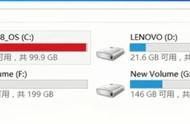2000年11月26日,丁光生在杭州。受访者供图
从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起算,丁光生的工作时长有73年。
以他自我评价来说,这73年中,他做过两件事:一是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建立药理研究室,二是创办《中国药理学报》。他参与发明了第一个被美国仿制生产的中国新药,也获得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韬奋出版奖”。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将他称为上海药物所药理学研究及中国编辑学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作诗夸他:“新药评价自君倡,期刊规范赖翁扬。”
后辈们称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他遇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随着逃难的人群辗转过西南多地,又考得公费留美名额,成为中国第一批麻醉学专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博士毕业、留院行医而生活优越时返回中国,自此在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至96岁。
年轻时,丁光生面目俊朗,轮廓清晰,上了年纪后,脸颊又圆润起来,和其小时候的照片越来越相像。他的标志是一副厚重眼镜,他有一千度的近视,晚年患青光眼直至失明。他在黑暗中又工作了近二十年。除此之外,他拒绝显出老态,一生喜爱甜食、摄影与交响乐。他的个头有一米七八,他将这种海拔高度保持到百岁。
2022年10月6日晚9点48分,丁光生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亲朋们在他钟爱的德沃夏克的交响乐中送别了他。
丁研究员
1958年4月26日,在上海中山医院,一剂0.2克的二巯基丁二酸钠被注射入丁光生的静脉内。那是他参与发明的一种新药,彼时试药能力有限,他选择用自己的身体试验,观察药物毒性。
他的同事梁猷毅接受了第二针0.5克的注射量,他随后又接受了1.0克和2.0克的注射量。
作为一种新药物的首位试用者,丁光生在此刻的感受不为人知。只有档案记录道,他与梁猷毅的体格检查、血压、心电图、血尿常规检查及主观感受均未明显变化,“半小时内,约有40%巯基从尿中排泄”。两人为此“紧紧地拥抱,泪花从眼眶里闪了出来”。
这说明二巯基丁二酸钠是安全的,可以用于临床治疗。
上世纪五十年代,调查显示全国有一亿人口生活在血吸虫病的风险中,抗血吸虫病所用药物酒石酸锑钾通过静脉注射,在治病救命的同时,也极易引发锑中毒,再次危及患者生命。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药理室主任丁光生与相关课题组合作,研发出了二巯基丁二酸钠,用以消除人体内的锑累积、解锑之毒。而后的研究,逐渐证明二巯基丁二酸不仅可用于锑中毒治疗,对重金属铅、汞、砷、铀等都有促排作用。1977年,中国药典将二巯基丁二酸收录;1991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二巯基丁二酸用于儿童铅中毒,强生公司开始仿制生产。
二巯基丁二酸成为第一个被美国仿制的中国新药。
研制出这种药物的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建于1932年,然而,其最初的近二十年研究侧重于化学,药理研究几乎为空白。“药物所之有药理研究,实自丁先生来所工作始。”中国科学院院士、前上海药物所所长陈凯先说。
1951年7月27日,芝加哥大学药理学博士、麻醉科博士后研究员丁光生自美归国,去往上海市武康路395号报到。那是一幢巴洛克风格花园住宅,窗台外布满梧桐树影,在其中,丁光生以药理研究员的身份筹办药理研究室,而后领导筹建了国内最早的抗高血压和抗血吸虫病药物研究小组。他亲自设计实验室、手术台的图纸,跑遍上海市采购卡片箱、计时器,又参与实验动物房建造,在冬日里夜宿房内,手捧火盆烘烤潮湿的水泥。
1951年12月,丁光生与周传青结婚。在长子丁民乐的童年印记中,父亲总在凌晨三四点即离家去单位,“因为觉得早上清静,没人打扰。”而晚上七八点、有时十点多才回家。在单位食堂用早餐,他总是将午饭一起买下,以省出中午排队的时间,好泡在实验室里。逢节假日,药物所保卫处唯独不封丁光生的实验室、办公室的门,因其“年三十、年初一也照样去所里上班。”他注重手下科研人员的外语能力,常发起群体学习,以便查阅外文学术杂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池志强曾在丁光生组织的俄文小测验中获得第一名,得其赠送的一把工艺小剑。

1999年11月24日,丁光生与长子丁民乐在杭州火车东站合影。受访者供图
丁光生在备忘录中记录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及药理组的发展变迁:1952年7月30日,时全所21人;1954年11月26日,仅药理组便发展至21人;1956年4月30日,药理组成员达26人;1964年5月2日,药理研究室全体有60人;1979年3月7日,药理研究室扩编为三个室,他任二室主任。
2002年,时任上海药物所所长陈凯先梳理药理室工作历史,发现建室半个世纪以来,“经筛选、药效和机理研究,推荐到临床的药物至少50个。”救人性命无数。
丁博士
1921年7月23日,丁光生出生在一个科学世家。他的父亲丁绪贤曾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母亲陈淑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两位叔父分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化工系主任,竺可桢是他的姨夫。
1946年春天,丁光生通过教育部全国统一公费留学考试,去往美国学习临床麻醉学。
从他的履历及日记来看,在美期间他的工作及生活十分顺利:他只用三年便获得了芝加哥大学药理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他给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学生上课,在芝加哥大学外科麻醉科上班,升任住院医师;为应博士生的外文要求,他参加芝加哥大学德文考试,“Pass at high level(优)”;他被美国Sigma Xi学会选为会员;他游访美国与加拿大的多个高校,与黄宛、李果珍、杨振宁等人交往。
1951年6月,时任上海药物所主任赵承嘏致信丁光生的父亲、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丁绪贤:“吾年迈力衰,对于青年召为科学家,当尽力照顾,使我国药物工作能放一异彩。”促丁绪贤邀正在美国的丁光生归国报效。1951年7月1日,丁光生即启程回国。不久后,赵承嘏再次致信丁绪贤,赞丁光生“积极精神,近所罕见”。

丁光生(左三)与父亲丁绪贤、母亲陈淑及哥哥丁普生合影。图片来源:《丁光生的八十年》
丁光生鲜少提起回国的初衷,“每次就像挤牙膏一样讲一点点。”他告诉子女们,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解放军夜宿上海街头,“认为这些人应该可以救中国。”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自己辗转联系到中国政务院,通过外交斡旋后,坐船经日本、菲律宾,抵香港,又换乘两次方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
实际上,这种动荡飘零在丁光生的青年时代并不罕见。他祖籍安徽阜阳,出生于北京,童年及青年的多数时间在苏州度过。他在备忘录里写道,1937年8月16日,日军飞机轰炸苏州市区,他于次日出发往内地逃难;其间辗转武昌、桂林、梧州,在梧州时“见报知”自己考中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遂乘船至柳州,又坐车经贵阳至重庆入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时转去成都就读。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回到南京中央大学原址,学习工作的生化科“在日军建造的平房内”。在南京一年有余,次年夏天他便乘船去了美国。
“胜利炮一响,大家便想着回家,当然了,逃离了八年,谁不希望回家瞧一眼呢?”而后北上南京,“与寄居七年之成都挥别……是回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他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熟悉丁光生的人都知道,这种乡愁贯彻了他的一生。他爱好听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乐,自认对德沃夏克背井离乡的创作经历深有共鸣,时常哼唱之。
他在备忘录中记载,1951年夏天,在美国旧金山起航归国前,他遇美国军警突击检查行李;于香港下船后,他又被英国军警持枪监视。待终于到达深圳罗湖火车站时,他第一次见到新中国国旗,热泪盈眶。
丁主编
丁光生晚年与人说,自己这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创建上海药物所药理室,二是创办《中国药理学报》。
1980年1月,本就近视1000度的丁光生曾入院检查青光眼,他的视力开始不可逆地下降,科研似乎走向末途——他后来对学生刘华清提过,视力障碍是他放弃科研的主要原因。时年近六十的他本可退休,但同年9月,受中国药理学会要求,《中国药理学报》创刊,他任主编。花甲之年,他开启了一份新工作。
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份瞩目的工作,“学报对国家、对科学发展来说很重要,但对个人没什么好处——搞研究的人发论文是光荣,但为论文做编辑的人,就是为他人做嫁衣,有什么成果都是别人的。”陈凯先说。
陈凯先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学术期刊行业还是一片混沌,“刊物的种类少,办刊水平也低,文章的规范都落后于国外,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丁光生的国际视野完全显现出来了。从1980年9月《中国药理学报》创刊始,他便要求刊物编排向国际标准靠拢,譬如采用了国际单位制,应用关键词和结构式摘要;又要求中文文章必须配备英文摘要,从1981年2卷1期起,要求文章内的图表亦用英文阐释。每有外宾到上海药物所访问,丁光生必赠送一份《中国药理学报》,所内有人出国访学,也会受其托将学报带出国交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丁光生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办公室内工作。图片来源:《丁光生的八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凯先在上海药物所读研,屡见到丁光生将不合格的论文退回,“当时的人英文普遍不是很好,但是又要求英文摘要,总被退回修改,一遍不行改两遍三遍,有些人改几遍都通不过。”编辑部里流传着一种说法,丁先生审稿,关注点大到数据内容、文法格式,小到标点与数字的规范写法,一旦有错就全文打回,但从不肯揭示错在何处,“为的是培养科研人员的自主能力。”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创始人翁永庆曾撰文回忆,《中国药理学报》的编委会几乎每次都会集体讨论《投稿须知》内容,由丁光生主导修订、宣传撰稿规范。他频频声称,“编辑学”应是一门专业学科,甚至提议要招收编辑学研究生。1984年,他首次提议用editology作为编辑学的英文名,该词汇被沿用至今。
《中国药理学报》从季刊、双月刊发展为月刊,且从中文出版渐变为全英文出版。1985年,《中国药理学报》成为中国第一批被美国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录的学术期刊。
其实,主编工作对丁光生而言是重担,任职期间,他的视力仍在每况愈下。
1991年,现浙江大学教授楼宜嘉在丁光生门下读博士研究生,她回忆,那时起,丁光生看文件已十分困难,“先是贴着两三寸远,后来几乎是贴着鼻子。”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八九副眼镜,看近看远都有选择。他有一台自美国带回的英文打字机,盲打英文飞快。他手写的字,“从0.8厘米每个字逐渐放大”,行间距也越来越长,写给楼宜嘉的信,一页纸甚至只有十几个字。
1996年,陈凯先开始担任上海药物所所长,曾劝说几近耄耋的丁光生回家休养,所里或编辑部有事再向他汇报请示。“他不肯,说自己在所里才能心情舒畅,跟大家有说有笑。回到家里,成天到晚没有精神。”
丁老
21世纪初,丁光生在家人的陪伴下游钱塘江两天——他父亲丁绪贤的骨灰撒在这里。楼宜嘉将他的住宿安排在西湖边上,他却告知她,景色虽美,他已然看不见了。
曾有友人记录自己于2001年在上海街头偶遇丁光生,那时天未亮,丁先生已在去药物所的途中。“问他为什么那么早,他说路上没人没车,可以摸着走。那时他已八成盲目……他说,‘我还有学生,有责任培养他们成器,为国服务。’”
所里自此有了传统,“新去的职工,每天下午1点钟,到丁先生的办公室为他朗读各种文字一小时,有信件、邮件、期刊和各种书籍。”编辑张华2008年入职,此后便常做丁光生的朗读者,有时还听他口述,为他誊写回信并寄出。
丁光生的时间观念极重,“有时候1点05分我们还没去他办公室,他一定会打电话过来,说都超时5分钟了,你怎么还没来?”晚年,药物所派车接送他上下班,不论刮风下雨,他一定提前5分钟站在路口等候。药物所里流传过丁光生的轶闻,称其年轻时参与所里会议,自己早早坐在第一排等候,主持会议的领导却迟到了十分钟;丁光生立刻起身离会,“他质问领导,底下的人可以迟到,你作为领导,怎么可以迟到?”
可他一直是所里大受欢迎的一位前辈。张华说,编辑部办公室在三楼,丁光生的办公室在一楼,他常在早上拄着拐杖摸索着上楼,敲敲门,中气十足地喊一句:“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陈凯先至今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丁光生拦住他,神秘地约他中午见面。午休时,他在单位院中见到丁光生举着相机,非常高兴地对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来给你拍张照。他有一本台历,记录着他结识的同事、学生、食堂职工等各种人的生日,每逢生日,便挂电话送去祝福;还年年都制作圣诞节卡片散发给同事与朋友们,直到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也要所里后辈替他制作。
他晚年在办公室接待学者、学生与各方朋友,动辄便要请人在单位的小餐厅吃饭,刷完了自己的饭卡,有时还要贴钱。他会变魔术,喜欢摄影,自己制作了三十多本相册,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标注着拍摄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光圈数据。
儿子丁民乐总结父亲,“做事情像德国人一样严谨,生活里像美国人一样热情奔放。”
他似乎从不知道计较。十年动乱期间,反对他的人将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上世纪80年代留学热兴起,他毫不犹豫地为其向美国大学写了推荐信,并满不在乎地向他人表示,举荐人才不论过往。他写文章自称座右铭是“甘为他人做嫁衣”。
楼宜嘉博士毕业时正值夏季,他坚持要在上海的高温中西装革履参加典礼,不愿轻慢该有的仪式。而他在药物所工作时的常见形象,是身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袖口早因伏案工作磨烂了,“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个朴素的老工人。”陈凯先说。
2019年,98岁的丁光生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特地换上衬衫与西裤,在家人的帮助下,挂着奖章,到《中国药理学报》的主编办公桌前留下了一张照片。
“张江有什么消息?”
2017年,丁光生96岁,在家人的强烈劝说下,才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退休生活。那之前,他仍然每天要到药物所去。
在不少人眼中,丁光生是个衰老得很缓慢的人,“八九十岁的时候,腰杆仍然挺直,一米七八的个子看着依然高大。”张华说。
年轻时,丁光生面目俊朗,轮廓清晰,上了年纪后,脸颊又圆润起来,和其小时候的照片越来越相像。当他视力衰退后,他依靠听觉生活的能力也达到了巅峰,只要周围陈设不变,他可以摸黑在家中、单位自如活动。他一辈子爱吃甜食,晚年患了高血压和糖尿病,也不愿忌口,仍要求吃蛋糕、酒酿、豆沙饼等。
过了一百岁,他的腿脚越来越不便,走动得少了,肚子胖了出来。但他的思维仍然清晰。他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所里的同事们去看望他,他能清楚报出每个人的家属姓名、工作,并询问大家生活是否顺利。药物所搬到张江去了,他就常问:“张江有什么消息?最近谁的文章发表了?”
为他朗读的习惯也带进了病房。除了期刊、报纸外,家属去看望他,为他读了他好友秦伯益院士的两本游记。无人来访时,他就用一个小收音机听新闻。

2021年7月,丁光生在百岁生日会上与护士合影。受访者供图
病房里的护工说,每有药物所同事来访,丁光生是最兴奋的,“好像一个蜡烛又给点燃。”但旁的时候,他仍然不为冷清抱怨。他这辈子很少流露伤感的时刻,唯一次在子女面前流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看到报道说许多科技人才迁居海外。
1997年,丁光生曾发表《小小十年话刊编》一文,阐述自己的“梦想”:“梦见我们已经跨入新世纪。所有科技期刊都得到全国重视,各界资助……梦见优秀论文全在国内发表,不再外流,国外也纷纷主动来稿。国刊的影响蒸蒸日上,跻身于国际核心期刊之林……”2022年6月,创刊42年的《中国药理学报》的影响因子达到7.189,在全球药理学与药学领域279种期刊中排名第28位。他的梦显然步入现实了。不过,受访者们都不知他对此的看法,他越来越老了。
照顾丁光生的护工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的身体机能加速衰败。“吃不动、咬不动了,东西得打碎了给他吃。再后来,就要吃流食。最后,医院给他用上了营养液。”他在最后的时光里犯了小小的糊涂,“有时候说话用英文。”
2022年10月6日晚9点48分,丁光生逝世,按他的愿望,后事从简,遗体捐献给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在少数亲友参与的告别仪式上,家属们为丁光生最后一次播放了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那是整部交响乐中最有名的一段乐章,降D大调,4/4拍子,别名《思故乡》。家属们认为,这是最应丁光生心境的乐曲。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