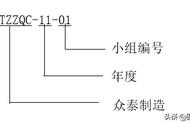空军大院主路银杏黄金大道 卢炳广 摄

空军大院主路银杏黄金大道 卢炳广 摄

空军大院办公主楼前小花园 作者 摄

空军大院办公主楼前小花园 作者 摄
空军大院是张拉满了的弓,充满生机与活力。每天,工作、生活节奏以军号为令。清晨,一听到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便迅速起床,要么出操,要么打扫环境卫生,都是集体活动。上班、下班,以至熄灯,都整齐划一。从周一到周六,连晚上都要上班,只有周日晚上才得以休息。对此,我们单身汉倒无所谓,有家、有孩子的干部,就有意见啦。但这是空军多年来的传统,是要求严的表现,没人敢破。还是粉碎“四人帮”后整党中,才作为“不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严肃提了出来,于是空军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开始有了一点松动:每周减半,即周二、四、六晚上可以不上班,美其名曰“在家教育子女”。后来,架不住干部反映强烈,晚上上班才彻底取消。其实,只要工作需要,不要说晚上加班,就是干通宵也不稀奇,星期天、节假日搭进去也无怨无悔——机关干部这点觉悟,还是有的。而完全不必搞晚上有事无事都要上班的形式主义。
作为大院活力和美的象征,每周露天电影场上此起彼伏的拉歌声,每天晚饭后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的喊叫声,天天走在大道上战士们整齐的脚步声、洪亮的口号声,都烙印般打在记忆中。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女兵队伍,空军通信总站是女兵集中的地方,这些男兵心目中的“女神”,一个个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要军姿有军姿。每当她们喊着清脆的口号,唱着激昂的军歌,列队从大路经过,总会吸引周围的人们驻足观看,啧啧称赞,其中也包括我。
空军大院有个很好的幼儿园,不说你也知道,就是当今名满天下的蓝天幼儿园。干部子女只要够年龄,至少两岁半吧,不用费什么劲儿,就可以入园。根本没有什么“托关系”“找门子”这一说,也根本没有花钱这一说。孩子可以日托,也可以全托,全托居多。我的孩子入托时,虽然幼儿园也教唱歌跳舞,但在社会上名气并不大。后来成立蓝天幼儿艺术团,由空政文工团专业人员常驻辅导,每年必有节目上中央电视台春晚,加之中央首长的下一代争相进来,这才声名远播,如日中天。除了幼儿园,还有育鸿学校,从小学到高中,不出大院即可毕业,极为方便。但中学教育质量平平,因此学习好一点的孩子,一般更愿意考到院外的初、高中就读。当时还没有划片这一说,北大附、清华附、人大附、师院附、101等中学,都有大院子弟就读。我的儿子,初中北大附、高中师院附,都是市重点,我也没少往这两处跑,无非是开家长会,和老师沟通,以及突袭检查儿子住校、学习等情况。
空军机关领导是很重视子女教育的,印象深的一件事是:空军政治部办起了儿童音乐班,每周有两个晚上教孩子们拉手风琴。我也给七八岁的儿子报了名。你道这教师是谁?竟然是空政文工团手风琴首席演奏员、60年代初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授手风琴的任世荣!那么大的名气,那么精湛的技艺,教的却是一二年级的孩子,而且分文不取,完全是尽义务!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世道人心和思想觉悟。
与幼儿园相连的,自然是大院子弟。从公主坟往西,是部队大院聚集地,空军大院是第一家,依次是海军大院、总后大院、通信兵大院、装甲兵大院、铁道兵大院、政治学院大院等。今天的复兴路,“文革”中曾一度改名为“八一路”。崔健、王朔、马未都、郑晓龙、陈红、叶京、华谊兄弟王中军王中磊、姜文等,都是大院子弟。或许是独特的大院文化孕育了一代人。不过,这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事了。
生活在大院那么多年,记忆深处也留下了一些小插曲、碎浪花。晚上下班后,生活区服务社一带,是最繁忙的小“闹市”。干部们从主楼下来,到这里买上点蔬菜、主食,赶回家去做饭。顺便说一句,那时没有不回家在外面吃饭的概念。服务社有卖热馒头的,有一次,我本意是问“一斤几个”,结果脑子走神,问成了“一斤几两”,卖馒头的也不假思索,随口答道:“一斤五两”,我立马决策:“来三两”,随后付钱,拿起三个馒头就走。事后想想,才觉“可口可乐”。
一段时间,实行“夏时制”,中午十二点下班,一点上班。一小时之内回家要做饭、吃饭、收拾,然后大人上班,孩子上学,紧张状况不言而喻。那天,我回到家赶紧洗菜、炒菜,让上小学的儿子端个小盆,去大院东南门口买张大饼。谁知菜炒好了,大饼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时间不多了,儿子空手回来了,问大饼呢?说卖光了,我厉声问,卖光怎不早点回来?儿子这才红着脸说实话:他下楼和同学拍画片玩,把买饼的事给忘了,待到想起,大饼早已卖光了。我大火,不失时机地赏了他一记耳光。我这个做父亲的其实很吝啬,这是唯一一次出手。
一位著名作家是我的棋友,课余常*上两盘寻趣。每次,他都先拿张白纸,唰唰唰写上两人的名字,赢了,在名字下画面红旗,输了则画个猪头。某次,他说中午到我家吃饭,于是通知夫人炒两个菜,饭罢拱手而别,并不道谢。谁能想到,此君后来官拜上将军。
空军大院公认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欢乐,它俗称搬家,雅称乔迁之喜。有个时期,大院住房的紧张已到极限,每个二级部,都有栖身办公室的单身干部和因无住房而配偶无法随军随调的“牛郎”“织女”。我刚调来时,就在办公室住了一段时间,至今清晰地记得是520房间。那个时候,人们最盼望、最想听到的消息,就是搬家。但房子可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出现重大人事变动时,加之空军党委迫于实情严肃提出“人走家搬”,这才有几间房子腾出来,供干部们享受乔迁之喜。就像拥挤的船铺上有人起去解手,别人才可以翻个身舒坦一下。好在那时的人们特别容易满足,饿惯了肚子给块红薯就欢天喜地,由无房到有房,由筒子楼到单元楼,由一间到一间半(另外半间两家合用),由走廊做饭到三家共用厨房,都会高兴得一个劲地感谢组织。可不是嘛,住房是组织分配的,搬家也是单位安排同事出公差帮忙——那时可没有什么“搬家公司”——,尽管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小件肩扛手提,大件喊着号子集体搬运,但组织的温暖、同事的亲密、生活的希望,尽可体现。我年轻时就曾多次出公差帮同事搬家,感觉身子是疲乏的,心情是舒畅的,因为看到了未来的曙光,他们的今天就是咱的明天哪!说老实话,一次次的搬家,如小脚女人走路,步幅实在不大,但毕竟是改善啊,总算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故每次搬家,乔迁之喜的欢乐都在干部脸上荡漾一些时日。直到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势不可逆转,新盖了几栋宿舍楼,空军大院“长高了”,干部住房的改善才真正驶入快车道。算了一下,20年间,我先后搬过六次家,与11号楼、6号楼、13号楼、14号楼、76号楼都有过亲密接触。也就是说,乔迁之喜的欢乐曾在我脸上反复荡漾过。
在我看来,空军大院最堪回味、最值得怀念的,还是独特的大院文化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南腔北调的军人来自四面八方,凡调到空军机关工作的都非寻常之辈,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有特长,人人都有功业,也人人都有后劲。我刚到机关那几年,一些老红军、一些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还在岗位上,前辈言传身教,后辈耳濡目染,机关风气是正的,干部信仰是真诚、追求是执着、工作是勤奋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大院氛围是透明的。比如不兴串门,西区、东区,不见车水马龙“拜访”“服务”的人流。路遇将军,你行礼,他必还礼,绝不敷衍。首长面前开会,尽可畅所欲言,实话实说。首长办公室,一般干部自然不会随便出入,但若有事实在要进,也绝无阻拦,不像后来,我曾见某空政副主任门口,还要安一战士执勤盘问,首长不约,绝不许进。官兵、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早已无影无踪,鱼水关系变味成了油水关系。这里忍不住告诉你我当时的心情:不是惊讶,也不是愤慨,而是鄙夷!
世风的变化,在于悄悄和暗暗之中。至今想起来不快的是,有那么两年,机关走队列、背条令、打扫环境卫生成了第一要务,甚至走火入魔,无法理喻。机关工作那么紧张,却天天要在正课时间到操场踢正步。办公次序,也要求苛刻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办公桌玻璃板下,不准压任何字条,包括电话号码;笔筒里究竟放几只笔,也有限制;连喝水杯子的把朝哪个方向,都有规定。形式主义登峰造极,人人敢怒而不敢言。这样高的领率机关,一天到晚不去研究练兵打仗,却搞这些不可思议的劳什子,岂非上层昏聩所致!后来揭出军老虎郭、徐之流,回想一下,已经是早有端倪了。一般干部嗅着不对味,说明早有腐败了。唉,今天说这些阴暗面,影响心情,但也无损于空军大院的声誉和形象吧。就像即使发现了蜘蛛网、老鼠洞,家还是家呀。
当我满满地回忆空军大院时,印象深、涌上心头的,大多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尽管今天的空军大院,是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美丽了。越旧越值得怀念,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年我进入空军大院时,刚刚提干,毛头小伙一个,待到搬离空军大院,已是名退出现役双鬓染霜的军休干部了。可以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空军大院度过的。空军大院之于我,不独有家的意义、港湾的意义,还有摇篮的意义、课堂的意义、赛道的意义、考场的意义。你说,整整40年的文化浸润和深情陪伴,教我如何不想她?
但是,自从搬离空军大院,再进门就难了。有不少战友怀旧,想故地重游,怎奈无法如愿。卫兵严格,只认今天的出入证,不认老兵的退休证。有一年,我和一名同乡战友专程到湖北随州看望老部队,路过武汉,特意由汉口到武昌卓刀泉特一号,原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旧址,想进去看一眼当年我们新兵训练的地方。哨兵查证,待我们说明来意,大概是被花白稀疏的头发和饱经沧桑的面孔以及堪当爷爷的年龄所感动,遂逐级请示,竟允许我们进门,只是须在哨兵视线之内短暂逗留。尽管如此,我俩已经理解和知足。
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啊。据说,今天的空军大院,已经不见往日容颜,人少车稀,清静多了。
无论如何,我爱空军大院,怀念空军大院。
我想,凡在空军大院住过、工作过的人,心情大概是一样的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怀念!
改于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