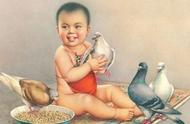而那时候,一个部族的人口如果只剩下了200,就便“结构合理”(性别比例、年龄分布都合理),也没有来自外界的充沛物资供给,更没有医疗;要隔着相当于自身聚居地“绕场一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直线距离,跋山涉水三五天乃至三五个月,才会相遇另外的部族,200的人口,恐怕等不及传到第三代,就彻底完犊子了……
今天,跟那时候比,简直是发达、丰沛得没谁了,还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鼓励“二胎”呢;可想而知,那时候,旺盛而健康的繁衍,对于生存来讲,是该有多重要。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生殖崇拜”。
人类最早产生“崇拜”的意识和诉求,无疑是出于自身生存维持的需要。
最早是“大自然崇拜”,为的更是祈求“活下去”——雷电、暴风、酷热、极寒、水旱灾害、动物侵袭、瘟疫……都会让脆弱的人类丧命。人们没有治理的办法,甚至无从躲避。于是就向那些灾害奉献出最宝贵的东西——食物、猎物、新生儿、美丽的姑娘……
后来情况好些了,人口多起来了,生产方式进步了,就会祈望人口更加丰沛、更加合理,以使业已进步了的生产得以维系、保持,甚至改进出更多人才能实现的更先进生产方式。于是就期待生殖旺盛。
差不多就在这个阶段上,原始的“大自然崇拜”,从崇拜对象到崇拜方式,都发生了趋于“概念化”、“抽象化”的衍变。崇拜对象由实体或真实自然现象,升级成象征物、象征符号(即“图腾”)。不管具象如何,在这个谓为“漫长”的“史前”阶段,几乎所有“升级”的“象征”性质的崇拜,都指向“生殖”——九尾狐、柱状物(比如高耸陡峭的山峰)、花、泉眼、蛋(卵)、蛋形物(比如“葫芦”)……

我们民族的前身“华夏族”,就是典型的“花崇拜”部族——“华”通“花”,古时没有今天这个“花”字哒——“花崇拜”的叫做“夏”的部族,就是“华夏”。
生殖崇拜中最普遍也最典型的“象征”,是“花崇拜”和“柱状物崇拜”,分别象征的是女性和男性的生殖器。这在今天看来,似显“露骨”,但可能还不至于“低速”。放在大几千年上万年前“茹毛饮血”、“始知遮羞”的“开蒙”时代,却是很纯真并且虔诚的。
相比之下,九尾狐崇拜是“象征”和“象征符号”(即图腾)的“融合”,或许更原始些,分布也较为狭窄。至少,在我们脚下这块大地上,九尾狐在内的一些更原始、更趋近“实体具象”的生殖崇拜,在被迫的迁徙和被动与主动相辅相成的部族融合、协作过程中,逐渐趋同于类似“花”这类更加“单一抽象”的载体。之后,古老的九尾狐,就成了纪念式的追忆。
追忆曾经的凄苦、忧惧、虔诚,还有不知跑去了哪儿、藏在何处的狐狸。
纪念曾经的寄望、磨砺、奋争,还有无数为生育子女喋血殒命的美丽母亲。

(《封神演义》里的九尾狐)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著有《管得着吗你》《红月亮》《武王伐纣》《深水爆破》等多部长篇小说。主笔、主创多部影视剧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谍战剧)、《危机迷雾》(38集谍战剧)已播出。
推荐: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