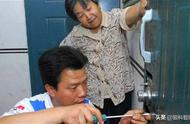进入秋天,大自然中最活跃的当属鸣虫。鸣虫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联,二十四节气中的很多节候都是根据鸣虫的表现来定义的。如立夏“蝼蝈鸣”,夏至“蜩始鸣”,小暑“蟋蜂居壁”,立秋“寒蝉鸣”,秋分“蛰虫坯户”,霜降“蛰虫咸俯”……那么,古人为什么对鸣虫情有独钟?为什么将鸣虫视为“灵虫”?蝈蝈、蟋蟀、油葫芦为什么被并称为“三大鸣虫”?促织、夜鸣虫、地喇叭等别名是怎么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用虫鸣治疗失眠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南宋宰相贾似道为何被称为“蟋蟀宰相”?
古人为什么视鸣虫为“灵虫”?
《诗经·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古人对鸣虫的关注在先秦时即已开始,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多首诗写过鸣虫。《国风·豳风》的《七月》一诗就曾提到蝉、蚱蜢、蝈蝈、蟋蟀等多种鸣虫。如,“四月秀葽,五月鸣蜩”:阴历四月份植物远志结籽,五月蝉(知了)开始在树上鸣叫。再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阴历五月蚱蜢开始伸腿鸣叫,蝈蝈则在六月动起了羽翅,秋七月田野里有很多蟋蟀,到八月份钻到屋檐下,九月蟋蟀进门,十月钻到床底。从《诗经》的描写可以看出,先秦时鸣虫已融入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男女之情感。《国风·召南》里的《草虫》一诗就曾借鸣虫表达男女之间爱的感觉:“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草虫喓喓在鸣叫,蚱蜢四处在蹦跳。久未见到心上人,心中忧愁不安宁。
古人为什么喜欢鸣虫?当然与其善鸣有关,也有《草虫》诗中那份缠绵和寄托,但更重要的是虫子身上惊人的繁衍能力带给古人的一种惊奇和想象。以螽斯(蝈蝈)为例,古人认为这是一种灵虫,“一生百子”,是多子的化身,崇尚多子多福的古人自然对其十分迷信。《诗经》中的《螽斯》就特别强调了“宜尔子孙”一语:“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蝈蝈张开翅膀,在低空群飞;子孙众多,预示家族兴旺。
古人因此认为“螽斯衍庆”。而繁殖能力超强,这是自然界中“虫家族”的共同特点,即便令人讨厌的蚊蝇都有这本事,所以古人专门用表示子嗣众多的“昆”字来定义“虫家族”,称为“昆虫”。
古人如何赏鸣虫?
《开元天宝遗事》:“以小金笼捉蟋蟀”“夜听其声”
古人喜欢鸣虫,进而形成了一种浓浓的“虫趣”和丰富的“虫文化”。
自然界善鸣的虫子很多,古人最喜欢的主要有蝉、蟋蟀、蝈蝈、扎嘴、油葫芦、金铃子等,多属昆虫纲中的“直翅目”。
从史料记载来看,蓄养鸣虫最先似乎是在皇帝后宫流行的。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唐玄宗李隆基的后宫就流行赏鸣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王仁裕如上所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玩虫记载,有人因此推测中国人玩虫始自唐朝,也可能更早。
王仁裕所记是否可靠?应该不虚,后宫深似海,“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而唐玄宗的嫔妃尤苦。据白居易《新乐府·上阳白发人》诗原注,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对其他嫔妃们来说,金笼里的虫鸣无疑是赖以打发孤寂无聊日子的一种方式。
民间认为虫鸣可治疗失眠症。传说,唐太宗有失眠苦恼,画家阎立本奏入眠秘方——夜听蛐蛐,果然见效,从此唐朝后宫蓄养蛐蛐成风。蛐蛐即蟋蟀,是古人蓄养的主要鸣虫之一,与蝈蝈、油葫芦并称为中国“三大鸣虫”,促织、夜鸣虫、地喇叭等别名皆因其鸣声而来。
蝉鸣也是古人喜欢听的一种叫声,唐诗中有大量的咏鸣蝉诗句,连唐太宗李世民都写过一首著名的鸣蝉诗《赋得弱柳鸣秋蝉》:“散影玉阶柳,含翠隐鸣蝉。微形藏叶里,乱响出风前。”当年唐长安还出现了养鸣蝉“斗声”之风,以蝉的鸣声长短来赌输赢。
为了让鸣虫根据人的需要来鸣叫,古人发明了不少“诱叫”之术,利用鸣虫对异物、异体、声、温、光等敏感的现象,诱发虫鸣。如在雄虫中放进雌虫,为了表现,雄虫就会使劲地鸣叫。为了听到理想的虫鸣,有人还在鸣虫的翅膀上点药,鸣声就会改变,行话称作“药叫”,这在明清两朝的京城虫家中间很流行。
古人“斗虫”始于何时?
《负喧杂录》:“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
除了欣赏美妙的虫鸣,古人的“虫趣”还有看虫形、观虫势。什么样的虫子最好,怎么看出是好虫?用现代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给虫子“约架”,古人叫作“斗虫”。
斗虫,是古代玩虫者最热衷的活动,让自己蓄养的鸣虫“互斗”,与朋友的鸣虫“赛斗”,是古代斗虫的两种主要方式。斗虫以斗蟋蟀最为出名,以赛斗最为流行。一般认为,“斗虫”也是从唐朝宫中开始的。“真青猛战大红袍”的民间故事,说的就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宫中设蟋坛,比斗蟋蟀之事。
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载:“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这里的“蛰”,就是蟋蟀。
斗蟋蟀往往从大暑节气玩起,一直玩到深秋。斗虫起初是图个好玩,后来渐渐变坏了——通过斗虫赌博。南宋姜夔咏蟋蟀词《齐天乐》前面的小序称:“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南宋时最会斗蟋蟀的高手当属官居宰相高位的贾似道,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蟋蟀专著《促织经》就是他写的,贾似道因此有了“蟋蟀宰相”的外号,民间戏称他为“贾虫”。
到明清时,斗蟋蟀之风刮遍全国各地,尤以京城玩虫最负盛名。据明刘侗、于奕《帝京景物略》,秋七月京城有风俗:“是月始斗促织,壮夫士人亦为之。斗有场,场有主者,其养之又有师,斗盆筒罐,无家不贮焉。”斗虫被老北京视为“京秋雅戏”。宫里斗虫更是热闹,连不少太监都是斗虫高手。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是月(秋七月)也,吃鲥鱼为盛事。赏桂花,斗促织。善斗者,一枚可值十余两不等。各有名色,以赌博求胜也。”
到清朝时,斗虫甚至成了民间的一种谋生手段,俗称“露天职业”。斗虫队伍也扩大了,除了蟋蟀,蝈蝈、黄铃等也爬进了“斗场”。
古人所玩鸣虫都是从哪来的?
《促织经》:“初秋时,于绿野草菜处求之”
有玩家认为,玩鸣虫的最大乐趣并不在“听”,也不在“斗”,而在“捉”。捉虫有“昼捕”与“夜捕”两种。昼捕就是白天捉虫,一般在午后进行,顺着虫鸣而去。夜捕则是从晚饭后开始,尤以下半夜最易得手,此时虫鸣最起劲。但夜捕想得到好虫不易,善捕鸣虫的行家圈内称“虫把式”,他们会在夜晚听野外虫鸣,记清方位,等白天去捕,如蟋蟀这类鸣虫爱伏于碎砖瓦片缝隙,或是枯叶下面,一般翻开瓦片后多半能捉到。
南宋贾似道《促织经》中的“捉促织法”对如何捉蟋蟀做过具体描述:“凡捉促织,必将着竹筒过笼。初秋时,于绿野草菜处求之;中秋时,须在园圃垣墙之中侧耳昕其声音,然后觅其门户。果是促织所在,用手启其门户,以尖草掭求其出。若不肯出窝者,或将水灌于窝中,跃出……”而且,捉虫也要讲究时机。就捕捉蟋蟀来说,一般立秋过后方成虫,有经验的虫把式不会在这时下手,而是让虫再长壮实一些,在处暑前后再行动,一直到白露,都是捕捉秋虫的适宜时段。
捉虫并不难,但是想捉到理想的“好虫”不易。《促织经》称:“出于草土者,其身则软;生于砖石者,其体则刚;生于浅草、瘠土、砖石、深坑、向阳之地者,其性必劣。”玩虫圈有“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
由于捉到好虫很难,于是古人想到了“养虫”。“养”有“喂养”与“种养”之分,喂养是蓄养捉来的成虫,这是玩虫的基本功,能“种养”鸣虫才是水平。所谓“种养”就是人工繁殖鸣虫,这是明朝人的发明。《帝京景物略》记载:“(促织)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