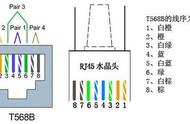黍子是起源于我国传统的农作物,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古代,黍子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唐朝诗人孟浩然在他著名的诗歌《过故人庄》中写道: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好客的主人在家中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等待故人的到来,能拿得出手的食物中,就有“黍”。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们能够把黍子制作成何等样式之美食,但是从它可以和鸡肉相提并论来看,想来不坏,应该属于百姓家中的上乘食品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曾经作为主粮的黍子已经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餐桌上,有些地方的人们甚至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亲眼见过了。如今,黍子仅在我国西北的部分地区有零星种植,我的家乡张家口就是其中之一。
黍子去皮后叫做黄米,再磨成面粉就是黄米面,在我们当地也叫做糕面。它可以制作的食物只有一种,那就是黄米面糕。黄米面糕有炸糕和素糕两种形式,虽然看似简单,却也形成了独有的饮食文化,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是我们这里的一句俚语,意思莜面和糕都十分扛饿,饭菜的选择以扛饿为目的,贫穷可见一斑。
过去的西北部地区寒冷干旱,靠天吃饭的人们如果种植小麦等作物,一年的产出无法糊住家人的口。于是,勤劳坚韧的劳动人民便选择了耐干旱的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的生存着。
黍子好活,给它一块土地就能生根发芽,偶尔下点雨就能茁壮成长,就算赶上天灾,粮食歉收,同样重量的黄米面可以比其他面类养活更多的人。为了骗饱肚子,那时候的黄米面磨的比较粗,口感发涩,可人们并不在意,因为饥饿让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变成了美食,活下去比活的好更重要。虽然人们没什么文化,但是也知道,只有活下去,才能有活的好的希望。
即便如此,黄米面糕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吃到的。聪明的主妇们在农闲时节也闲不住手脚,她们每天忙完家务,就会到山沟里、草地上挖野菜,拿回家洗净晾干,和着杂粮为家人编算着一天的伙食。只有到了农忙时节,人们才不再吝啬,家中每日可以吃上一顿黄米面糕,为的的保持体力,好熬过劳累的秋天。
到了我小时候,温饱已经不是问题,黄米面糕也成为了大米饭、白馒头等细粮之外调剂口味的食物。家中的大人们都爱吃糕,时不时的就会做上一顿。
每次吃糕,都是我的痛苦时刻。黄米面糕蒸出来是一大块的黄色面块,看上去毫无食欲。最主要的还是它的“黏”,黏到我用筷子怎么夹也夹不下来的地步,每次吃糕都把我搞的满头大汗、气愤不已,一旁的大人们看的哈哈大笑,等他们笑够了就会轻轻松松的夹下一小块放进我盛满熬菜的碗中,我不情愿的用糕块儿蘸了蘸熬菜汤,放进嘴里,开始了另一番艰难。糕面很难咽下去,怎么形容呢?只要你愿意嚼,它就会一直黏在你嘴里,不变小也不变软,噎的你干瞪眼。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米面糕都是我童年的饮食噩梦,我无法想象大人们怎么能嚼几下就会把它囫囵个咽下去,生怕他们一不小心噎着后还得去医院,幸好,这样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
及至我成年以后,交通的便利和社会的发展,让你足不出户便可品尝到祖国各地的美食。不知为什么,面对琳琅满目、选择众多的美食,我越来越愿意吃一些“土”的掉渣的食物,就连之前最不爱吃的黄米面糕也变成了我眼中的美味。当然,现在吃糕,我也掌握了技巧,不会再有咽不下去的情况发生了。

黄米面糕的吃法有素糕和炸糕两种。上面说的是素糕,我们这里叫“面型糕”,是最家常的吃法。素糕的好处是它的方便快捷,活好面,上锅蒸,出锅即可食用。
为了有些味道,吃面型糕是需要蘸汤料的。汤料没什么讲究,熬菜可以、炒菜可以、凉菜可以,甚至咸菜汤也可以。虽说是汤料,其实也就是在做菜时候多加一碗水,多放一勺盐,不用刻意单独去做。年轻人们吃糕,也有喜欢在上面洒一层白糖吃的,甜甜的、黏黏的,好像麦芽糖。一些爱吃糕的老人更夸张,他们可以什么料也不蘸,直接把糕放到稀粥里泡着吃,还吃的津津有味。我曾经好奇的试过此种吃法,没有一点味道,实在享受不了。
素糕没讲究,炸糕可就有许多说法了。
以前,只要有炸糕出现的日子,都是大日子。只有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炸糕。如果你去亲友家吃饭,主人端出一盆炸糕来,那就是最好的待遇和最高的礼节了。
炸糕可以做成有馅儿和没馅儿的。没馅儿的自不用提,有馅儿的就需要说明一下了。我们这里常吃的炸糕馅儿有豆沙和红糖两种,豆沙用的是芸豆。大大的芸豆做熟后,在大姑娘小媳妇的手中被碾压成泥状,看着简单,实际上很费精力。豆沙自然是越细口感越好,对于炸糕这么重要的场合,各家的女人们都会不吝时间,尽心把豆沙做的细腻香甜。
豆沙馅儿做好后,就需要和糕面了。和糕面是个体力活,因为黄米面粘性大,和起来十分费劲。这也难不倒整日劳作的乡亲们,一大帮子人一边聊天一边和面,丝毫没有费力之感。有一次老家亲戚结婚,我回乡参加婚礼,在厨间帮忙,看着年老的婶娘们和着糕面,我自持力气大,上去替换她们。谁知费了大劲也和不好,站在旁边观看的婶娘们早就笑弯了腰,一边把我推开一边说:“费了牛劲,和不好面。和糕面不止要用劲,还的会用劲。”至于什么是会用劲,她们说不上来。可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吧。
面好了,馅儿好了,剩下的就是包了。这个比较简单,和包饺子类似,还不用捏边。家中如果有小孩子,大人们除了豆馅儿以外,一定会包几个红糖馅儿的糕,在他们心中,甜蜜永远属于孩子。这里顺便说一句,由于糕面和豆馅儿都是熟的,所以有的孩子会直接吃没有炸的豆馅糕,味道也很不错。
一切准备就绪,炸糕开始。
把一大桶暗红色的胡麻油倒进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烧热后下糕开炸。每当这时,老人和小孩就会被关在屋子里,怕着了油烟咳嗽。在烟熏火燎中,油黄油黄的炸糕陆续出锅,稍稍凉一凉就端上桌来,孩子们忙着从里面挑选着糖糕,大人们笑呵呵的责骂着,乱糟糟的屋子里有着别样的温暖和喜悦。
炸糕之所以在重大节日才会出现,一是它需要大量的食用油。二是它的“糕”和“高”同音。乡亲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千百年来对幸福向往的传承却始终牢记心头,用最珍贵的油,炸出最美好的食物,是他们可以想到的、做到的,最隆重的礼节。
黄米面糕就是在这样一群朴素的人们手中,代代相传。没有高大上的道理,没有滔滔不绝的言语,文化就在人间烟火的氤氲中传承了下来,实惠又实在。

在我的家乡张家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特别喜欢吃黄米面糕的群体基本集中在阳原、蔚县、坝上地区。阳原蔚县都属于桑干河流域,而坝上人的祖先也大多数来自大同、朔州等山西境内的桑干河流域。
桑干河,这条古老的河流,出现过泥河湾古人类,影响中华文明的黄帝蚩尤炎帝三祖的涿鹿之战也在这片区域发生。似乎是冥冥中有了某种默契,古老的黍子在古老的人类活动地区传承至今,好似黏黏的黄米面糕,把中国人的文明和文化牢牢的与大地相连,纵使经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战乱纷争,也从未有过任何形式上的割裂,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也许,我们的祖先们,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里,就是靠着一次次的尝试,找到了黍子等可以延续种族的粮食作物,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它们捧在手心上,满怀希望的种到土地里,这一种,就是千万年。
作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已经把这片土地上泥土的芬芳镌刻到了骨子里,嘴里吃着黄米面糕,心里装着家,无论到哪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作品均为原创
请关注风舞鹰翎,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