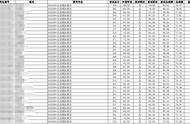在江南西,可以看到不少“旺铺转让”的告示。/碗几摄
在江南西开手工意面店的幸姐告诉我,附近每新开一家社区餐饮店,她都能明显感觉到客人被分流了。她的小店约50平方米,容纳着吧台、厨房、六七张小桌子,还有三只爱猫的小窝。
开店3年来,她眼看着附近的餐饮店换了一批又一批,“旺铺招租”的告示也贴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因情怀而入场,却因为生意中的真实计算而退场。能存活下来的,总是少数。
有人为糊口,有人为情怀
在江南西这样店铺流动率大的网红街区,一家小店能存活过3年,已经可以拿“终身成就奖”了。
幸姐原是酒店的大厨,3年前“被失业”,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于是咬咬牙开了这家小店,想着收入应该能比打工高不少。
然而,受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社区店生意难做了,堂食变少,只能转做外卖。
可由于菜品制作成本较高,她的菜品在外卖平台上与十几块一大份的预制菜相比,在价格上毫无优势;另一方面,消费者点外卖图的是方便和快捷,而手作餐饮店主打的是体验感和精细感,在讲求“快”的外送流程面前,社区小店的这些优势被通通抹平。种种原因下,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幸姐的小店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幸姐的小店里,哪怕是客满,也顶多能接纳20位左右的顾客。/碗几摄
阿朱的咖啡小店开在中山大学南校门的对面。她的店是附近街区唯一 “像样”的咖啡店,主要做的是附近三所院校的学生生意。店内面积约20平方米,整体装修、布置都以实用为主,天气好的时候,阿朱会把店外的遮阳伞打开,让客人可以坐在露营帆布椅上,边聊天边呼吸新鲜空气。
不少熟客总担心她赚不到钱。一瓶冷萃咖啡,制作时间一般需要10个小时甚至以上,在阿朱店里堂食卖26元,在外卖平台上卖30元(扣除外卖平台近30%的佣金和各类活动满减后,她真正能拿到手的不足20元),而相近的品质放在高档小区或者写字楼附近则可以轻松堂食卖到38元。对此,阿朱并没有太多怨言,她认为,在社区开店,首先就不能抱着要赚大钱的心态。

每天上午,阿朱都忙着给外卖订单出餐。/碗几摄
小店刚开起来时,学生们喜逢甘露:“这附近终于能有一家可以坐下喝咖啡的店了!”她还主动跟我聊起她发现的一个“怪象”:她的店里,很少有大一大二的学生来,来的大多是研究生和博士生。
她开玩笑道,他们大概是吃过生活的苦,便不觉得咖啡苦了吧。对于学生们来说,去阿朱店里,不但能够喝到新鲜的咖啡,还能有个让自己暂时忘掉繁忙学业的窗口,不但能和她聊聊不顺心的事,还能听她讲冷笑话。扎进社区创业的年轻人相信,这样的“人情味”是社区店独有的魅力。
讲起和学生间的趣事时,她脸上露出了姨母笑。实际上,阿朱今年才25岁,来她店里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大多比她年纪要大。他们向她吐槽科研里的不顺心事,也谈年龄焦虑。有个老熟客跟她抱怨道:“我快30岁了,博士也快毕业了,却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做什么。”说这话时,眼神里带着对阿朱和她的小店的羡慕。
是的,人们对社区小店带有一种电影《深夜食堂》式的滤镜——老板寡言但有智慧,总是会以自己的方式关怀那些疲倦的灵魂。对于他们的人生命题,阿朱当然没办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她可以提供的仅仅是一杯给他们续命也好,抚慰也罢的咖啡,一个他们在“精神内耗”期的喘息地,一次于学生们而言是“围墙”之外的治愈对话。

社区小店里,似乎总是藏了很多故事。/《深夜食堂》截图
当然,也有“明知不赚钱,偏要把店开”的社区店“玩家”。
与幸姐及阿朱相比,95后子华开店的压力似乎要小得多。他在五羊邨开了一家茶、咖啡、中药元素相结合的饮品店。作为传媒工作室的老板、抖音和小红书上颇有经验的创作者,他并不打算把新媒体营销那一套用在自己的店里,原因很任性——他想要和客人逐个聊天。这样的底气,来自于他已经做好了靠其他副业来给这家小店供血的准备。
子华并没有对上一任租户留下来的铺面进行大改造,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些瓶瓶罐罐和宣纸的装饰。他的小店店面光亮、整洁,适合久坐。
他半埋怨道,刚开业时来的人太多了,远超他可以用心招待的顾客量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流量慢慢在变少,这倒让他感到舒适。
在我去他店里的那两个小时里,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店里只有一位客人。子华对这样的状态似乎“心满意足”,他称希望能把店做得慢一点,沉淀下来,才能做得长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