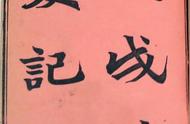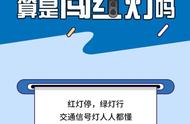清军收复新疆
亲政波折
主词条:隆裕太后
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五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始亲政。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载湉,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给载湉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

隆裕太后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光绪大婚图 拒和主战 主词条: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公车上书 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载湉急切召见,询问国外情况。后来载湉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载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载湉还读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于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即高升号事件,悍然挑起丰岛海战,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载湉认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如果导致事情很难收场,那我们自然应该出兵讨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载湉的谕旨。在后来的战役中,中国初于牙山战役失利,继于平壤之战中战败。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战役中日军夺中国兵舰,中国海军覆丧殆尽。本年,中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光绪帝朝服像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十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 求变图强 主词条:瓜分中国狂潮、戊戌变法、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诱订《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权,将侵略势力伸入东北三省。五月,载湉多次和慈禧太后一起亲临醇王府邸探视醇王福晋(即载湉生母)的病。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病逝后,载湉十一日没有上朝。慈禧太后下懿旨说:醇亲王福晋病逝,应称为皇帝亲生之母亲。六月,载湉亲自去送醇亲王福晋的灵柩出殡。[15]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强占胶州湾,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
光绪帝与梁启超、康有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四月,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载湉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
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戊戌政变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 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载湉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慈禧太后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慈禧太后的行动;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