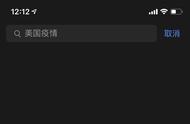作者 沈荣良
与儿子聊天。儿子提及幼年时在老家丰惠生活时的种种有趣的情景,那相隔了数十年的如烟往事,犹如在一大块白布上面了撒了一把黑芝麻,星星点点地闪烁在我的眼前。

儿子自己的小孩都已经长到他的齐胸高了,可他在我们面前依然还像个小孩,说起儿时在丰惠老家祖父母身边时生活的情景,断断续续,趣味十足:“爷爷每天早上五点必定起床,还要把还没睡醒的我也拉起来,跟他一起去跑步,跑步回来,点起煤油炉,先烧一杯开水泡茶,再烧菜泡饭。”
儿子绘声绘色欲说还休,抒发着童年的幸福滋味。
“爷爷性急呼啦地吃过一碗半生里熟的菜泡饭,剩下的给我盛了一碗让我吃着,自己就端起茶杯上班去了。”
听儿子说起煤油炉子,不禁勾起了我埋在心底的一段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越地城乡居民燃料“变革”的时期。沿袭了千多年,煮饭炒菜烹饪以柴草为主要燃料的厨下灶头,开始改变。
农村山区封山育林的严格推行,极少再有柴草挑进城里供给居民烧饭煮菜;江南水乡的人居,对于用煤制品燃料还非常陌生和拒绝,不说要限量凭票,光是生一个煤球炉子的麻烦,烟熏火燎的也遭人埋怨,煤球用起来,远不如柴草方便,不但灶具要另外重起,煤料还要制成煤球方才可烧;于是另一种炉具,煤油炉子便应运而生,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炉具,燃料可以想办法,特别是煤油炉小巧灵便,随时随地,用火柴一点就着,不管放在哪里,都可以烧菜煮面,使用的方便给煤油炉子的出现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老家丰惠古城里边出现的第一只煤油炉子,据说是一个聪明的铜匠师傅,在上海看到一只外国造的铜质煤油炉子,萌生了依葫芦画瓢自己制作的念头,把它的外形内置都搞了一个清清楚楚,画下图纸,然后带回家来自己动手制作。
两天以后,一台土制的煤油炉子居然试制成功。
他是一个铜匠师傅,煤油炉的外形,对他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只是把铜板改成了白铁皮。煤油炉的关键组合件火圈防风罩,内外三只,里面两只,听说原件是用紫铜皮冲压而成,密密麻麻排列着不到一个毫米大的气孔,只有这样才能使燃烧着的煤油快速气化,减少油烟,提高热力。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工具,他就用小口径冲头,手工划线,依线冲孔。炉芯升降的齿轮和齿条传动机构,居然被他改成一根10号铁丝做成的曲轴,与炉芯盘钩连在一起,曲轴弯头一转,炉盘升降自如。
样品一出来,古县城里马上就出现了更多的五花八门的煤油炉子。

丰惠大街离我家不远的亨号酱园西首有一家铜匠店,听说铜匠店潮师傅这段时间都在做煤油炉,每天下午我都会去站一会。铜匠店的街沿比旁边的铺面要高两级台阶,三间店面有钟表修理,箱子修理和铜匠白铁修理综合在一起。
街上的人,彼此面熟。我靠在铜匠师傅作为围栏的柜台上面,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潮师傅搭讪聊天,潮师傅并不怎么理会我,在他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闲人,也不会想到我是到那里“偷拳头”的,只顾埋头做自己手上的活。岂不知我的眼睛总是盯着他手上的工件,心里思忖着怎样仿照他的样子去做一只。
连续看了有三、四天,回家敲敲打打,再跑去潮师傅那里“偷拳头”,再回来改改拆拆,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一台土制的毫无美感可言的煤油炉终于在我的手上诞生。还没有给炉子涂上一层保护油漆,就点火使用了。
当12管炉芯被点燃以后,红色的火焰在风火圈里边跳跃抖动着瞬间转变为淡蓝色的火苗,“滋滋滋”地朝灶面上喷出来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和快乐体验。
这种煤油炉子,看似简陋,煤油燃烧借助风力,火力也很猛。适用于小量煎炒烹炸,小火慢煨,炖菜煮面足足有余。在燃料多样化的“变革”时期,确实是家庭生活好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