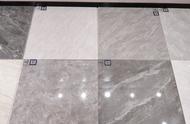文/刘向东
作文也怪,对有些熟悉的事物,甚至是亲身经历的,日思夜想,剪不断,理还乱,想写成文字,挺难;而对有些隔山隔水恍兮惚兮的事情,忽然面对,忽有感、觉、悟,提起笔来,竟顺利成篇。老实说,本篇得自辛丑秋月采风,回头看,是命里有的,诗与思,纷至沓来,特此记之。
1
白石山居,本来是华中小镇的一组建筑,偏偏在我看来,它是小镇的代名词。
初见白石山居,石阙,阔首,老风骨,新气象,沉稳,自在。门里豁然,礼壁广场,中轴线规制,尽显文化礼仪。放眼望去,神威大道,泗水名堂,至尊至善;鼎泰宫(又名华中假日酒店)庞大,坐北朝南,雪霁堂(可供六千人与会的大型商务会议中心)与与之匹配的百渡食府东西呼应。而这只是前奏,并不次要的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建筑在庭院之内,力避一览无余,在迂回中,在行进中层层展开。隐身鼎泰宫背后的,是贵宾楼、竹里馆,贵宾楼贵在精致,依山就日,接待尊贵贤德,竹里馆曲径通幽,茂林修竹,作为精致的休闲养心的商务会所,可遇不可求,若是知心相会,抚琴把酒,待明月相照,亦为上选。这种院落式的群组布局,特点鲜明,具有不可多得的艺术感染力,至少引起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期盼心理,感发激动和兴奋之情。
说来幸运,下榻鼎泰宫,我的房间305,西窗与松风馆相望。作为宫,不是宫殿,亦非宗教场所,而是白石山居生活方式承载地。松风馆由归来堂、归思堂、归隐堂、万霞堂组成,这组具有皇家离宫风格的组团式庭院建筑,每日紫气东来,气韵自生。数了一遍,再数一遍,馆前有松九十九棵,若非人为,必是天意。及至松风馆跟前,看台基高筑,柱梁式构架高挑,别有用心,直追汉代建筑,屋面和汉代相仿,也是平直的,不像南北朝以后用调节每层小梁下瓜柱或驼峰高度的办法,形成下凹的弧面层面,使檐口处坡度变平缓,给人以通天的感觉。有孩子仰头一望说,这不是日本式的建筑吗?孩子还小,还不知道,中国早期建筑特点的间接证据可从日本现存的古建筑群得到支持,日式古建筑,可以正确地称之为中国式建筑,他们大多建造于推古、飞鸟、白风、天平、弘仁、贞观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有些建筑本就出自中国和朝鲜匠人之手。
入松风馆,一杯香茶,两袖清风,神游子集经史,参禅书画琴棋。
拜三归堂,致虚极,守静笃。
待到白石山居对面的观景台上,遥遥相望,总览山居全貌,大美于心。却原来,山居置身盆地,在涞水源老城之南,白石山村以西,背靠七山,面朝白石山,平均860米海拔,从盆地中央延至七山脚下,鼎泰宫坐镇中心,雪霁堂、百渡食府分列左右,别墅群、花园洋房、贵宾楼、竹里馆环抱其后,白桦林温泉谷、蓝鲸馆休闲运动中心、房车营地、青青牧场、采薇园、花海四下散开……
好一个上风上水一方净土,绝佳宝地!
好一篇新美汉字!
我大脑中的风水术,也是忽闪的汉字。文字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是世界性的,汉字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占有的地位更是非常特殊的。我们知道文字的发展过程是从像形开始,然后演变为形意的结合与形声的组合,最后变成声音的符。在风水术里,有很多观念,表面上来自观察山水的形状,也就是风水学的“形家”,看山的样子,看水的样子,然后产生一个联想。我也把山水当文字看,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什么呢?是符号。看到山水符号的时候,我就有想法了,想法是直接从“形”来的:你看,那个山是什么样子,水又是什么样子,是龙?是凤?是金木水火土?接着我就告诉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从山水的形状与文字符号联系产生的,是一种通过假借获得的价值判断。
是谁让我私下如此敬仰,在此创建了白石山居?
一个“理想国”,得山水之真气,天地之造化,又充满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说是小镇,实为重镇,敬天爱人,承担了精神上、物质上的双重建构。
偶得大书《九和六境》,才知白石山居的缔造者,乃赵建棠先生,一位资深学者、古建筑专家。
早在2010年秋,赵建棠先生曾作《国宅赋》,他在强调“九和”时说,要“与天求和,吸宇宙之精华;与地求和,纳大地之滋养;与人求和,融众人之智慧;与宅求和,立身体之根本;与山求和,得阳刚之正气;与水求和,增阴柔之秀美;与古求和,得渊源之文明;与今求和,寻当代之时尚;与万物求和,济科学之发展。”
说到了,做到了。
他用“新而中”的理念,以特有的学识,认识—分析—继承—革新,创造了民族的、科学的、新时代的白石山居,以崇高的理想、真金白银和毕生心血,打造了民族的、科学的、新时代的建筑典范。啥是民族的、科学的、新时代的?窃以为,有民族的历史、艺术、技术的传统,用合理的、当代工程科学的设计技术、结构与施工方法,适应当代人生活时尚与精神需求的建筑就是民族的、科学的、新时代的。
建筑是什么?梁思成先生说简单地说就是盖房子,解决人住的问题,解决人的安全食宿的地方、生产生活的地方和娱乐休息的地方。衣、食、住,自古是相提并论的,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梁下宇以避风雨。为了这需要,人类才不断和自然作斗争。
到了白石山居,情形变了,恰如当年*先生所言,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赵先生和他的建筑,适应新时代发展变化,不再与自然斗争,而是求和,求九和,九九归一,与心和。
历史上民族形式的形成都不是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形成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艺术创造差不多都是不自觉的,在工匠不自觉中形成。到了赵先生和他的白石山居,也变了,变成了有追求、有秩序,有纪律的自觉的艺术,他没有个人自由主义,但有属于自己的建筑历史学与创造实力,实现了包含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交融,集中体现了当下社会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的新时代背景。
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商巨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原有很多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取而代之,在建筑上,几乎丧失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事实上也明显说明民族文化的阶段性衰落。这,或许曾经让赵先生揪心,继而苦苦求变。
中国古代建筑活动在七千年有实物可考的发展过程中,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至南北朝、隋唐至金、元明清。在这五个阶段中,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经历的萌芽、初步定型、基本定型、成熟盛期、持续发展和渐趋衰落的过程。而后三个阶段中的汉、唐、明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强盛有巨大发展的时期,与之同步,汉、唐、明三代建筑也成为各阶段中的发展高潮,在建筑规模、建筑技术、建筑艺术风貌上都取得巨大成就。这,或许就是赵先生直追汉唐的原因所在。
无缘当面请教赵先生,揣度而已。
再次打量白石山居——这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杰作,如同现代汉语诗歌一样,有它特殊的“文法”、“语汇”和言说方式。它没有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发挥新创也是受过传统熏陶的,却给人以全新的表达,全新的感觉;没有大屋顶,没有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偏向,白墙黛瓦,融入山水,有别于这派那派;历史的反应,新时代气息,融入山居每一个细节,从规划布局、环境场所、建筑规划设计,到园林景观、业态融合、服务标准、美好生活期待,有机,有序,和谐共生。
仿佛那不是建筑,不是房屋,而是灵魂的居所。
白石山居啊,甭说安居于此,只看一眼,就心仪,就心动,就念念不忘。
2
一个小小遇见,或许足以说明白石山居的环境质量,和诗意。
那是在白石山居采薇园,享过田园意趣,吃过晚饭,走在白石山的影子里,我们一行,忽然受到萤火虫的列队迎接。
小家伙个个提着灯笼,一闪一闪,微弱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照亮了眼前的路。
有人问:萤火虫,闪闪烁烁,明明灭灭,忽东忽西,在寻找什么呢?
有人说那是游子的灵魂,离开故乡太久了,东走走,西看看,找不到记忆中的家了。
其实谁都知道,萤火虫不过是虫子,只是无人做深入研究。
我以前写诗的时候,萤火虫被派上用场,从一种神秘过渡到另一种神秘。“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诗,把秋夜的寂静,失意宫女的孤独写得淋漓尽致。“的历流光小,飘摇若翅轻;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这是虞世南的《咏萤》诗,对这种发光小动物感到惊奇,寄兴吟咏,抒发了自已的遐想。
曾读到这样一首歌咏萤火虫的当代“南方童谣”,依我看不像歌谣,像是一首温暖、祥和的摇篮曲,这里不妨引来:
萤火虫,夜夜来/点着灯,结着彩/飞到外婆家里去/叫她来我家来做客
什么茶,桂花茶/什么菜,腊肉菜/今天又是团圆夜/千万莫在路上捱
萤火虫,夜夜来/飞过山,越过海/你给宝宝照个亮/莫叫宝宝又怕黑
什么路,光明路/什么鞋,温暖鞋/宝宝是个好孩子/一觉睡到东方白
在我还小的时候,萤火之夜,没有这样的摇篮曲,只是反复听爷爷讲那借助萤火虫读书的故事:那个孩子啊家里十分贫寒,晚上想读书没有灯油,夏天的时候啊,他便到外面抓来不少萤火虫,用纱袋装上,照明读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讲着讲着,爷爷拐到《三字经》上去了,听不懂了。听懂了的,是萤火虫可以照明读书。我家没有纱,抓来萤火虫,装在洗净的墨水瓶里,结果什么也照不见。那时我不知“囊萤照读”是个伪故事,只怪家里没有纱,让墨水瓶把萤火虫给闷死了。后来读法布尔的《昆虫记》,巧的是,他做过借助萤火虫照亮儿的试验。我们来看看他的记录:“假设把一群萤火虫放在一起,彼此相近得几乎互相碰着,每只萤火虫都发光,这么一来,它的光通过反射似乎就会照亮旁边的萤火虫,从而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只只虫子。可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许多光只是混乱也无法清晰地看出萤火虫的形状,这所有的光把萤火虫全都模模糊糊的混在一起了。”
原来如此,不是我的墨水瓶子问题。可能古时贫寒人家的孩子出于对读书的强烈渴求,想到夜晚借助萤火虫照字,并做过试验,后来口口相传,把失败的实验传成经验了。
法布尔之后,只要是写到萤火虫的,但凡不是虚无缥缈,只要一动真的,谁也没能绕过法布尔。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昆虫记》卷十,《萤火虫》一文只是两个附记之一,约一万三千字,特此摘录千字经典的叙述——
它有六只短短的脚,而且非常清楚怎样使用这些脚,它是用碎步小跑的昆虫。雄性成虫像真正的甲虫一样,长着鞘翅,但雌虫没有得到上天的恩宠,享受不到飞跃的欢乐,终身保持着幼虫的形态。
……
萤火虫虽然外表上弱小无害,其实,它是个食肉动物,是猎取野味的猎人,而且它的手段是罕见的恶毒。它的猎物通常是蜗牛,昆虫学家早就知道,但是我从阅读中觉得,人们对此了解得不够,特别是对它那奇怪的进攻方法,甚至根本不了解,这种方法我在别处还从未见过。
萤火虫在吃猎物前,先给猎物注射一针麻醉药,使它失去知觉,就像人类奇妙的外科手术那样,在动手术前,先让病人麻醉而不感到痛苦……
萤火虫用它的工具反复轻轻敲打蜗牛的外膜,动作十分温和,好像是无害的接吻而不是蜇咬……
我了解昆虫令对方浑身瘫痪的奇妙技术,它用自己的毒液麻痹猎物的神经中枢。在人类的科学还没有发明这种技术,这种现代外科学最奇妙的技术之前,在远古时代,萤火虫和其他昆虫显然已经了解这种技术了。昆虫的知识比我们早得多,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
常见的是,蜗牛的壳和支持物没有贴紧,盖子没盖好,裸露处哪怕只有一点点,萤火虫也能够用它精巧的工具轻微地蜇咬蜗牛,使它立即沉沉入睡,一动不动,而自己便可以安安静静地美餐一顿……可见突然的深度麻醉,是萤火虫达到目的的好办法。
萤火虫怎么吃它的猎物呢?是真的吃吗?它把蜗牛切成小块,割成细片,然后咀嚼吗?我想不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的嘴上,有任何固体食物的痕迹。萤火虫并不是真正的“吃”,它是“喝”。它采取蛆虫的办法,把猎物变成稀肉粥来充饥。它就像苍蝇的食肉幼虫那样,在吃之前,先把猎物变成流质。萤火虫进食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蜗牛不管多大,总是由一只萤火虫去麻醉。不一会,客人们三三两两的跑来,同真正的拥有者丝毫没有争吵地欢宴一堂。让它们饱餐两天后,我把蜗牛壳口朝下翻转过来,就像锅被翻倒过来一样,肉羹从锅里流了出来。宾客们吃饱肚子走开了,只剩下这一点点残渣。
……
萤火虫的发光器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前两节的宽带;另一部分是最后一节的两个斑点。只有雌萤成虫才有这两条宽带,这是最亮部分;未来的母亲为了庆祝婚礼,用最绚丽的装束打扮自己,点亮这副光彩照人的腰带,而幼虫则只有尾部的发光小点。绚丽多彩的灯光标志着雌萤已经羽化为成虫,交配期即将到来。羽化本应该使雌萤长出翅膀,使它飞翔,从而结束生理演化过程。但是雌萤没有翅膀,不能飞翔,它一直保持幼虫的卑俗形态,可它却一直点着这盏明亮的灯。
原来这才是萤火虫!
让法布尔始料不及的是,在他百年之后,由于农药等工业文明的猎*,萤火虫已经难得一见了,这揭示着生物学意义上的一个危险信号,作为公认的环境指示物种,萤火虫的退场预示着生态危机的扩大化。让人彻底绝望的是,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研究院,已经利用发光二极管发明了“机械萤火虫”,正在远处一闪一闪。
近在眼前的,是白石山居采薇园的萤火虫以及它赖以生存的蜗牛。
快来看看这些萤火虫吧。
愿小小萤火虫,还有蜗牛。与我们相伴直到晚年。
3
从白石山居向南望去,高处是白石山峰,低处是长城,开车到长城,只需10分钟。
长城是中国人抵抗沙漠和草原游牧民族的艰苦而又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从公元前八世纪起,马背上的民族来去如风若沙,使周王朝背靠沙漠草原但从事农耕的封国狼狈不堪,只好分别沿着自己的国界修筑长城。从北平到辽东半岛,是燕国长城;从北平到河套地区,是赵国长城;从河套到陇西高原,是秦国长城。公元前三世纪,六国归秦,匈奴扫平瀚海大漠,两大势力对峙。为了抵御匈奴南侵,秦王朝把断断续续的长城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防线,一千余年矗立在北疆。公元十世纪时,辽帝国向南扩张,取得了包括北平在内的幽燕十六州,进入长城之内,长城作为中国的北部防线一时丧失作用。后来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兴起,塞北是他们的本土,长城已位于腹地,六百年间长城成为摆设,甚至显得碍事。到了十五世纪,汉人建立的明王朝把蒙古人赶回老家,但没有力量控制长城之外,只好再度乞灵于长城,有新建,有重筑,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留给我们现在仍然能够部分目睹的万里长城。明王朝覆亡,代替它的是来自东北的满族民族,不光带着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做嫁妆,又逐渐将蒙古、新疆等归入版图,长城再度位于腹地,最终丧失其国防价值。
白石山居边上的长城是明长城,附近还有更老的赵长城,有人猜测是代王的院墙,也说不定。
长城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另当别论。
我要说的是,白石山居在长城之外,尽管近在咫尺,却别有历史含义。当年修长城的人哪里去了?他们拥有江山,却又两手空空,他们因长城而死,生命有永恒的特征。他们不比我们,他们修长城当作院墙,我们把长城看作风景,在长城之外。
白石山居长城如驰如奔,在苍苍茫茫的山脉之上,密集的敌楼群,数十步或百步,最远不过二百步,便是一座,两台相应,左右相救。
我们宛如当年戍边换岗的士卒,越爬越高。归来有梦,长城内外,千家灯火,万户酣梦。往上看则是浮云,是一轮将满未满之月,凛凛冷冷。在苍凉肃穆的情调中,远处依稀可辨的烽火台,如一座座熄灭多年的土高炉,在呼呼的山风里,在范仲淹那支哀伤痛绝的悲歌中: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忽然想起大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二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搭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我曾深以为是。而今看来,任何思想,都是事后的思想,再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回到真实的处境中,中国在成为拥有上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之前,分封制小国是一定要垒院墙的,防御不说,单是为了各自的特权,也是一定要垒院墙的。像长城一样的石头墙,不光中国有,据我所知,英国也有,叫“障墙”,捷克也有,叫“饿长城”。在捷克,在布拉格,汉学博士、翻译马丁在查理桥上手指不远处一个山丘对我显摆说:“看,长城,我们捷克也有长城,饿长城。”我一时懵了,什么?布拉格有长城?看我没反应过来,马丁再次指了那山丘说:“看,在那儿,饿长城。”我看见了,长城,真的是长城,在青草之上绿树之下,黑乎乎,像一只小小的尺蠖。据说,那是查理国王令一群饥饿的流浪汉修筑的,因为他听说中国修筑了长城。
鼎泰宫中,推敲沉默,一叹:
长城啊/一面老墙/方块字垒起来的史诗一行。
长长的长长的荣耀的挽歌,长长的长长的悲壮的绝唱。
我们看长城不!我们望——
尘埃零落了/青山不老/长城长/长城生长。
鸟语可以破译/而长城这个长句子/只有它自己才能拥有它自己的口吻与梦想。
曾是怎样有力的手/把长城指出/又是如何不屈的意志/调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激情与力量。
一砖一石靠梦想养育/一个梦想养育了/另一个梦想。
长城起伏/白昼把日子带回黑夜/历史又总是在更高的风中/迎接无法抗御之光。
长城长/长城生长/长城/在怎样的血肉上才能生长?
4
白石山是一定要写的,没有白石山,何来白石山居。
真要写写白石山了,才发现走马观花,缺少细节支撑。
从上山的缆车上,见满山针阔叶混交林,独自成片的,是松树,桦树,栎树,椴树,留待以后专门去研究;导游说林中有各种飞禽走兽,树下有大蘑菇,大到一个蘑菇就有八斤,留待以后去看虚实;我知道山上有美,有不完美的完美,留给看官亲自去看。
只写一种动物一种植物吧。
写一只蝴蝶,那是神灵,离地三尺。
那是我们在白石山腰森林里遇见的雨后的一只蝴蝶,同行梦瑶可证。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一只蝴蝶,在山上等我。
看它翩翩而来,担心一阵风把它吹歪了,伤了翅膀。
哦女神!请倾听这些不成调的小曲,由甜蜜的强制和亲切的回忆拧成,
请原谅你的隐秘甚至要唱给你本人柔若软贝的耳朵:
我无疑今天梦见,抑或就是醒着亲眼见到生翼的灵神?
我一无所思地漫步在林中,突然,因吃惊而晕眩,
看到两只美丽的生灵,并排卧在草莽最深处,顶上窸窣的树叶和颤动的花朵,还有山溪一条,几乎难以察觉:
在屏声、草根清凉的花卉中,或芳眼惺忪,天蓝,银白,和含苞的紫红,
他们在草圃中呼吸均匀;
他们交相拥抱,还有他的翅翼也连理;
他们的嘴唇并未触接,但也没道别,
仿佛为手感轻柔的睡眼分开,
并依然想要超越已有的吻数,
在晨旦时爱神那温柔的眼晖中:
那生翼的男孩我认得出;
可你呀是何人,哦快活又快活的白鸽?
他忠实的灵神!
此为济慈《灵神颂》第一节,其中也有一只蝴蝶。在我看来,蝴蝶那“鲜艳的双翼”指语言,是灵魂借以“托”其自身的媒介,生翼的灵魂翩翩然脱壳而去,悄若无声地飞翔于太虚之中,这样的灵魂是想象,也是心象。
庄生晓梦迷蝴蝶,我也迷,曾感发出一首《化蝶》。管它别人怎么看呢,反正我自己挺感动的——
蝶因心动而动/翩翩复翩翩/脉脉情人全是庄周
而不是谁都能脱胎换骨/千年等一回/任二胡独奏,提琴协奏
谛听到白头/两只蝶儿落下来/不在左手,就在右手
由此在白石山上见一只蝴蝶蓦然出现,一阵心慌。
另一只在那儿?
下白石山,恍惚见山脚有杜鹃,不敢确定。回家通过微信找白石山居立娟经理证实,她说有啊,春天满山都是,还发来的杜鹃花视频,如火如荼。
这又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爸爸病了,无精打采。年三十下午,我去单位值班,见花房杜鹃,想到那是爸爸最喜欢的花,便口婆心借回好大一盆,气喘吁吁抱上四楼。一向因房间狭小不支持养花的妈妈,也神采飞扬,忙着腾屋子,边干边说:“这花是为你爸爸借来的,这回你爸爸的病该好了。”那是一盆多年生紫杜鹃,足有上千花朵,多数含苞待放,刚刚绽开三分之一,映得满屋春色盈盈,生机盎然。爸爸对花而坐,如醉如痴,吩咐我去借相机,买胶卷,留下那美丽的日子。而后一个多月,爸爸伴杜鹃而食,伴杜鹃而饮,伴杜鹃而眠,没病了。
杜鹃花有四百多个品种,分红紫黄白诸色。从照片上看,白石山上的杜鹃花是红色的,名映山红,东北人叫它满山红,山西人叫它王金子,有的地方叫它兰金子,白居易的诗里叫它山石榴,在朝鲜则名金达莱。
杜鹃花生长在阴岭偏阳的山坡上,日出便照见它,中午又不暴晒,属丛生灌木,绝少孤枝,更不独处,哪里生长它便是一片,往往从山脚铺到山顶。
李白有诗曰:“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见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那是在巴蜀,按白石山纬度和海拔,应该开在谷雨之后。
杜鹃花开的时候,树木鹅黄新芽,蒿草竟生,千丛万丛花儿,似霞光从山顶流下来,如火焰从山脚向上燃,青松扶摇其上,嫩绿融于四周,山鸟婉转其间,让人顿悟什么叫春深似海。在那种境界里,真是千愁尽释,万虑皆消,心上生出无尽遐想,无限憧憬,感到世界可爱,人生美丽,生命充满希望。
昨晚读到一个资料,说是有人专门去看杜鹃,因为错过了季节,就在白石山居住下来,就那么等,静静地等。
5
以白石山居为中心,四下走走,到处都是风光,都是人文,在我看来,正是那些看上去有一点儿距离的东西,构成审美,成就了白石山居的阔大和深远,大到让它成为而今雄安新区的后花园,深远到当年的皇家龙脉。
沿水向东,用不了多远,就见精彩。
小时候读到诗人赵日升写于1957年的一首诗,叫做《拒马河,靠山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河里流的金银水,人们过的好生活。
从此记住了靠山坡的拒马河。
关于拒马河,《水经注》有记:“拒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涞源曾名广昌县隶代郡,涞山一山分七峰,又名‘七山’。《广昌县志》中说拒马河源,在县城南半里,出七山下。拒马河古称涞水,约在汉时,改称‘巨马’,有水大流急如巨马奔腾之意。后渐写作‘拒马’,相传曾因拒石勒之马南下。无论‘巨马’、‘拒马’,均言其水势之大。”
或许不光是水势大,还因为清凉。边塞诗中写幽燕之河,统称“强水”,有“水寒伤马骨”之句。
拒马河古称涞水,遗迹尚在。在涞源县沿河而下,就到了涞水县。
说来也快有三十多年了吧,春夏之交,我们一帮河北师大的同学,坐火车去涞水寻找“香雪”——铁凝成名小说《哦,香雪》里的主人公,疯子一样,边走边喊:“香雪你在哪儿?”见到小姑娘就追,追着喊:“哦,香雪!”喊得走在前面的小姑娘心里发毛,脚步飞快,以为跟着一帮神经病。香雪没有找到,到百里峡里转了一圈儿,到拒马河边走一回。
那时的拒马河,正如铁凝后来在散文《河之女》中描述的那样,是―条野河,一条散漫的河,多弯的河。每过一个弯,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让河水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绕石而过,或漫石而过;那是白沙的岸,有白沙作衬,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艳蓝,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沙滩。让人流连忘返的最是那石头,零零星星的大石头间,那些小石头挤在一起,若鸟卵,像是要孵化鸟儿。忽然有水鸟从中飞起,那鸟,多是蓝色的,也有白色的,飞走了,贴着山崖而去,又忽然飞回来,叼着虫子。蓝色的水鸟站在石头上颠尾巴,颠~颠~颠~,太好看了,你很难把它看成一只鸟,而是一小块跃动的蓝天。而那些白色的鸟,要安静得多,偏偏要站在黑白相间的雪浪石石上,并不像白云,像是寻找奇石的人,随手在黑石头上放置一小块白石头。
前些年采风,恰巧就住在拒马河边,忽然想起大画家铁扬先生多次来过这里,画拒马河,写拒马河。他老人家让人过目不忘的那些画,叫做“玉米地系列”,画面上,有的是几个女孩风一样钻进玉米地,撒着欢儿的把衣服向天上扔,五颜六色的衣服在玉米地里闪烁,而隐隐约约的女孩们,一身精光,精光的身影和玉米的秸秆交织互动,澎湃着年轻的绿色的血液;有的正往河里跑,或腾身一跃,往水里扎……
原来我以为,这不过是画家的想象力,或是幻象,谁知那是记忆,是一种生存状态。恰巧那时我随身携带着铁扬先生的散文集《母亲的大碗》,在拒马河边打开,看其中那篇《河里没规矩》,活灵活现,试着稍微改编一下,分一下镜头,就是微电影脚本——
他沿着拒马河走,寻找那个“河里没规矩”的故事。
那故事是说,夏天,中午,当地的闺女媳妇们可以和男人面对面下河洗澡嬉闹,又互不干扰。
他坐在河边画写生,不见传说中的情景,再三打听,当地人都讲得含糊其词。
那天他又在河边画画,一位放羊老人走来,停住脚步,抱一羊鞭蹲下来看着他画,看得出神。
他问老人:我画的拒马河像不像?
老人说,像是像,就是河里缺东西。
缺什么东西?
缺个“河里没规矩”。
他惊奇地站起来,和老人站个对脸。
“你是说,画个河里没规矩?”
“那有多么好,这边是女的,那边是男的,一蹦一跳的。”
老人用羊鞭在他的画面上指点这边又指点那边。
“现在还有吗,那,那个河里没规矩?”
“女人娇贵了,不般以前了。”
见他刨根问底,老人说,找个女的讲讲吧,那才有滋有味,老爷们儿讲, 干巴巴的。
他提醒他到村里去找一个叫贵姐的女人。
一位年轻媳妇把他领进贵姐家。
贵姐原来是一位古稀老人,大热的天,贵姐在炕上捂着被子,露出半截身子,肩胛骨突出着,两只乳房似有似无的。脸上的皱紋像黑白木刻画。
他不好意思看贵姐,贵姐却不在意,还是露着半截身子和他说话。
他向贵姐说明来意,贵姐脸上的皱纹立刻敞开来。
贵姐说:我十六岁过的门, 觉着这事挺新鲜,我们山那边没河,看见河,看见水稀罕着哪,大中午,闺女们、媳妇们都去,找块玉米地、高粱地, 脱得光光的,把衣服一扔,就往河里跑,不怕叶子扎,不怕蚊子咬,下饺子一样……打打闹闹,疯着那。那厢兴许就有男人,有,有去呗。你冲我喊,我冲你喊, 你冲我骂,我冲你骂。你往上一蹿,我也往上一蹿,你敢露, 我也敢露。谁叫你年轻呢,可有一条,不许你过来,更不许动手动脚,说是河里没规矩,这就是规矩,严着呢……
他好奇地问贵姐,万一有人不守规矩呢?
贵姐说:“除非他不是人。”
听着贵姐的叙述,很难想象这位瘦骨的老人,就是当年在河里“疯”过的少女,但他又清楚地“看”到一个十六岁的妙龄少女,朝着那边的男人,笑着、跳着,尽情展示着自己的青春。
一个“河里没规矩”的故事,终于在他的心中复活起来。
和贵姐分别时,那位年轻的媳妇对他说,往上走,深山里,兴许还有。
于是,他开始沿拒马河向上走,向白石山深山里走,看见高坡下一带茂密的玉米地。不远处有群女孩正朝玉米地跑来,迎着他跑。他的心怦怦跳起来,眼看着女孩叽叽喳喳跑进玉米地,眼看着出现了画面中的那一幕,一幕,又一幕……
可惜这美消失得太快,对玉米地里的下河者,他来不及做出任何记录,他便想了一个画家惯用的方式:决定请一位女孩重演一回。
他把她请到玉米地里,他请她脱下衣服:
“你看,那边就是拒马河,现在你就是个下河者。你下过河吗?”
“没有。”
“你试试吧,从玉米地里走过去。”
“我走过去?” ^
“对,走过去。”
“叶子太扎了。”
“人家下河都这样走。”
“你见过?”
“见过。她们一面扔衣服,一面跑。”
她有些为难,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了,可不似真的下河者那么自然,那么爽快,那么毫无顾忌。但总算配合着他的要求,走过去,又走回来。
画家用模特儿作为对构思的补充,但模特儿能做出的必定有限。
“玉米地系列”的一切,是在调动画家的想象和记忆,还有贵姐的描述,玉米地里的下河者才那么壮丽、灿烂。
合上书,蓦然感觉有些可惜,眼前的拒马河,不再是完完全全的野河了,不再那么散漫了。先生所记述的,我所梦想的,在而今游人如织的拒马河边,有的已经成为过去,要想重现,除非真的拍一部电影。
注视时间,时间若水。
盯得久了,水中那些白得透明的石头,像是透明的孩子在河里洗澡,阳光穿过他们的身体,没有阴影。
回想拒马河,得这样的句子:
在群山的影子下面/拒马河边,边走边唱/接近今生最初的梦境
哦/水色天光,一川石响/比清亮更清亮,比美还美
当你远去/我要来送你,带上我的骨头/到唢呐的尽头
从白石山居往西北走,是空中草原,半个多小时车程。
所谓空中草原,实为亚高山草甸,在白石山居周边山上随处可见。
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出诗的地方。
我曾经这样写它:
春来草色一万里/万里之外是我的草原/草木一秋/听天由命
要有一株苜蓿/要有一只蜜蜂/有蜂嘤的神圣与宁静/没有阴影
要有一双更大的翅膀/为风而生/要有一个小小的精灵/直指虞美人的花心
要有一匹小马,雪白/或者火红。让它吃奶/一仰脖儿就学会了吃草/草儿青青。
而草/一棵都不能少/哪怕少一棵断肠草/天地也将失去平衡
我也曾在那里与诗友大解说草:
起风了/风把草原吹过来
还记得背水滩上那些草吗/那些离群索居的杂草/因为长在石缝里/侥幸躲过了驴唇马嘴
我记得,我说过/风把它们摁倒在地/但并不要它们的命
还记得大先生的野草吗/在这只有野草的草甸子/记得,记得
当我们沉默/ 我们充实/当我们张嘴/ 我们空虚
又起风了/风把草原吹过去
更值得一说的,是空中草原的雪绒花。十几年前,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中国的雪绒花在哪里》,成为空中草原最亮丽的名片。
冯先生到空中草原的前几个月,曾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山村访问,当山民把两三只雪绒花送给他时,他被毛茸茸雪白的小花奇异的美惊呆了,那首无人不知的电影歌曲《雪绒花》油然在心中响起。可是,当山民问他:“中国有雪绒花吗?”,他含糊其辞,说好像也有,在哪儿呢?
到了空中草原,他惊呆了,遍地都是名贵的雪绒花。
毛茸茸雪白的花,淡黄色球形的花蕊,淡绿色的茎,长长短短,如同舞者。
到底是哪位仙人路过此处,把随身携带的花种撒在这儿,创造了这奇迹,这天国的花园?
心怀白石山居,再看雪绒花,更像是一个喻体。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ihxdsb,*3386405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