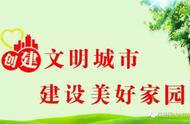江德福的几个孩子中,亚宁跟亚菲是截然不同的性格。电视剧中的亚菲虽然牙尖嘴利,但心底善良,遇事有担当,她敢为了母亲跟弟媳妇争执,敢为了姑姑德花跟老丁的儿子争执。
原著中亚宁喜爱看书,天然对弱者有一种善意的同情。
江昌义第一次出现在江德福家里时,在亚宁眼中,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江昌义 。
他大约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身农村自家织的黑不黑灰不灰的粗衣布裤。高高的个头,有一张同影集里我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清癯的国字脸,留着一种剃头刀子剃到头顶时戛然而止的头发,我们笑称“锅盖头”,他站在我和小哥身后,像个走错了门的不速之客,脸上被血充得红彤彤汗津津的,他立在那儿,一双方口的很笨拙的布鞋拘谨地行在一起,那种姿势,另他有随时倒下去的危险。
我的怜悯之情,大概就是在这一瞬间产生的。
这是原著中江亚宁第一次看到江昌义时心中的感受。第一次见到江昌义,她就在一瞬间产生了怜悯之情。这也为她以后对他的善意埋下了伏笔。

江德福疑惑着问江昌义找谁,原著中是这样描写的:
那农村青年上下嘴唇翕动着,努力了几次也没发出声音来,那双忧郁的眼睛突然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他哽咽着,费劲地叫出了一声“爹”。
江德福睁大眼睛骇然地问:你问谁叫爹?
那青年国字脸上的泪珠越滚越多,他突然蹲下身子,双手捂住了锅盖头,又大声哽咽了句“爹”
在江昌义喊出爹的时候,正在擀饺子皮的安杰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丢,一脚踢开凳子,气呼呼回了她的卧室,江德福跟着追过去。

家里突然出现这么大的变故,都是这个不速之客带来的,几个孩子都生气地盯着蹲在地下的江昌义 ,对他充满了敌意。
江昌义第一次到江德福家,给整个江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首先是安杰第二天早上坐第一班客船回了娘家。这应该是安杰婚后第一次这样不告而别。
母亲的离开让孩子们无所适从,他们认为江昌义才是造成母亲离家的始作俑者,因此,没有人给他好脸色,大家在吃饭时故意在盘子里挑挑拣拣,故意大声说话,却唯独不搭理江昌义。
只有亚宁,这个从小喜爱读小说的女孩,因为经常在小说中看到小人物被欺辱,她深刻体会到小人物的眼泪和痛苦,所以,她是全家第一个对江昌义释放善意的人 。
我的姐姐哥哥们气愤地盯住地下这个抱头痛哭的人,我的小哥甚至还用回力鞋狠狠踢他的黑粗布鞋,恶声恶气地说:你滚。
我跟着他们走了几步,又举得不太对劲,我的心不知为什么被揪得一扯一扯地痛。
江亚宁对江昌义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对他多了几分关注,她注意到江昌义总是在外面用水龙头下的水洗脸,没有毛巾,总是随便用袖子擦脸。他不会刷牙,也没有牙膏牙刷 。
他在吃饭时总是挤在一个角落里,每次只吃一碗米饭或者一个馒头,亚宁能看出他没吃饱,但江昌义从来不拿第二个馒头或是盛第二碗饭。
江亚宁的同情心再次被激发。原著中,她几次描述自己对江昌义的感受:
他成天呆在这个院子里和这幢房子里,和一群敌视他,处处给他难堪的人在一起,孤单,苦闷和难受是可想而知的。
文学启发了我的善良,我对那种恶毒的故意的举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偷偷跟他有了来往。
喜爱文学的亚宁觉得一家人对江昌义太过分,她同情他,偷偷跟他来往,她把自己的新毛巾给江昌义,给他拿牙刷和牙膏,把牙膏挤到牙刷上,教他刷牙的姿势和动作 。
每当这时 ,江昌义就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

江亚宁对江昌义释放了自己的善意和爱心,她以为自己在帮助这个可怜的,被大家排挤的人。她为自己能够帮助到他而快乐。
单纯善良的江亚宁却没想到,她就像《农夫与蛇》中的农夫那样,明明付出了善意,最后得到的却是狠毒报复。
多年后 ,江亚宁也曾经回忆过自己当初对江昌义的善意,特别是她教江昌义刷牙的场景。
现在想来,这实在是对他另一种形式的折磨和摧残,像是一条吮吸过水的鞭子,刷刷地抽在他年轻结实的肢体上,这甚至比我的哥哥姐姐们更恶毒。
但我实在是出于一种善良,是经过文学启发的善良,如果非要算是恶毒,也算是善良的恶毒。
当一个性格偏执的人在极度绝望或无助的环境中,未必会对来自身边的善意照常接纳,相反,他甚至会以为这是对他的羞辱。
《守婚如玉》中的华莎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大学同学小敏是个富二代,知道她家庭条件不好,总会把自己的衣服和首饰送给她穿。华莎平常总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但是最后她却控诉小敏之所以给她衣服,就是为了显摆,就是为了博得她的感恩心。
华莎和江昌义,他们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都是那种用自己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善意的人。
自古善良会换来善良,大多数人都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但有一种人, 他们的思维却跟平常人不一样。当我们付出全部为他好时,他未必会感恩,不感恩倒也罢了,甚至他还会恩将仇报 。所以,以心换心只是说大部分人,却不能代表全部,因为有些人的心是换不到的。否则也就不会有“白眼狼”这个词语。
亚宁很不幸,遇到了江昌义,她心疼他,竭尽全力想要帮助他,如果她知道,自己全心付出的善意会被恶意揣测,会在多年后遭到报复,她又该是何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