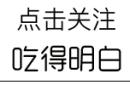执笔法,历来受到书家的重视,在历代书法著述中几乎是一个必谈的问题。从唐代孙过庭的“执笔三手”、韩方明的“把笔有五种”,到林蕴的“拨镫四字法”、陆希声的“拨镫五字法”,再到五代李煜的“七字法”,直至清代戈守智《书法通解》中列出的十二种执笔名称及图样,执笔之法经流传和载录可谓日益繁难杂碎。20世纪80年代初,沙孟海在《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一文中,针对这些书法文献记载提出异议,他将从古至今的执笔法以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梳理,认为唐代及唐以前都是斜执笔,如今竖脊端坐、笔管垂直的姿势则是随着宋代以后高案高椅的使用才出现的,“如果认为从古以来执笔方式就是这样,或者认为今天我们把钟、王等人执笔方法学到手就能解决书法上一切问题,就能成名立家,那是错误的,没有历史观点”。沙氏的这一论点在当时可以说是拨开了笼罩在诸多书家眼前的迷雾,对那些专注于承习笔法之正的书家而言,着实具有警醒作用。


应该说,在沙孟海之前,至少于民国初年,已有少数书家学者开始对历代的“言笔法之书”提出质疑,对书家执迷于笔法的做法表示不满。例如,张之屏在写成于1920年的《书法真诠》中认为,历代有关笔法的撰录“谬诬相承,转相神圣”,“遂致美术几同魔术焉”。再如,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1932年出版)“伪托”这一卷中专列书法文献三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关笔法技巧的,余氏的辨伪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依托于名家的“言笔法之伪书”大多抄缀敷饰而成;二是笔法的解说和传授繁难芜杂,甚至神乎其神。

但是,沙氏的疑辨与张、余二人之辨相比较,自有其相异之处:首先,张氏所论是以运笔法为主,余氏所质疑的“言笔法之书”也并不单单指向执笔法,还包括运笔法。其次,余氏辩驳“言笔法之书”,其背后的观念驱动因素是“重学理、重史法”,余氏对书法史著理论性、逻辑性、系统性的强调使其将质疑的目标明确指向拼凑抄撮而成的“技术之书”。而沙氏替执笔法革除旧说的原动力与之有别。沙氏的建立新说,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启发:一是古代人物故事画中所绘的写字执笔方式;二是古今坐具的改变。
关于人物故事画,沙氏在文章中有较详细的交代,不仅点明自己所观察的绘画作品有哪些,如相传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相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宋李公麟《莲社图》、梁楷《黄庭换鹅图》,以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画残片、甘肃安西榆林窟第二十五窟唐代壁画等,还提及为自己提供绘画资料的学者友人,如启功、王伯敏、段文杰、中村不折等。但是,关于古今坐具,沙氏只讲古代是席地而居,今天是高案高椅,在蜻蜓点水式的说明之后并没有作更多的介绍。本来,这样的蜻蜓点水或许并不成为问题,也不会引起疑问,对于我们现今的读者而言,古今坐具不同或已是常识性的知识,不需要过多介绍。但是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学界尤其是书法界对于古今坐具的形质及改变等远未达到普遍认知的程度。事实上,有关古代坐具的情况是伴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至50、60年代之后才渐为学界知悉的,而被更多数人所了解则要等到70、80年代之后有关古代生活用具的大型图录的出版。
50年代以来,考古界对六朝、唐代、宋代墓室进行大量发掘,各个时代的生活用具屡有发现,随着对用具实物和墓室壁画所绘图形的研究逐步具体深入,研究者对古代家具的演变和造型开始有了清晰的认识。例如,1955年于南京近郊江宁赵史岗、黄家营、丁甲山等处发掘的六朝墓中,获得了陶隐几(凭几)和陶案等模型。1970年在南京象山7号墓、1973年在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陶榻,其外形和尺寸都是模拟当时的髹漆木榻,显示出当时人们凭几坐榻的习俗。在上述考古发现后不久,陆续有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公开发表。有关唐代家具的考古资料,虽然发现得还不多,但已可考察出家具形体由低向高发展的趋势。1955年,唐天宝十五年(756年)的高元珪壁画墓于西安被发掘,该墓室北壁绘有墓主坐在椅子上的画像,这是考古发掘中所见年代较早的纪年明确的椅子图像。经五代到北宋,则逐渐形成了新式高足家具的完整组合,其中较为重要的实例如河南禹县白沙北宋墓壁画中的高足家具。此外,绘有类似家具的壁画或雕砖家具画像,在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有发现,可以看出桌椅等高足家具在一般民众生活中已经流行。坐具由低变高自六朝起已有萌芽,其原因有多方面,研究者考证认为:一是因为匈奴、羯、鲜卑等少数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其垂足高坐的生活起居习惯影响并逐渐改变着汉人传统的席地起居习俗和礼制;二是此时期建筑使用的斗拱日趋成熟,也对坐具的高度产生影响。
如果说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的发表,还只能使考古新发现和新成果在考古学界等相对狭小、有限的学术圈内产生影响的话,那么,有关家具的大型图录的出版发行,则把古代家具的丰富资料推介给更多的研究者和更广泛的读者群。特别是1981年以来由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联合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共五卷,至1987年第五卷出齐)中,刊出了大量有关古代家具的图片资料,以最直观、最形象的方式展示古代家具史。
至此,我们再联系沙孟海写于1981年的《古代书法执笔初探》,沙氏能找准生活用具的历史演变这一关键因素,为执笔法由斜执到直执给出正面的解释,这显然是受到了50、60年代以来考古新发现和图录的启发,只足沙氏没有明说。与沙孟海相比,张之屏、余绍宋在他们那个时代,却没有以上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这些有利条件,虽然他们能意识到历代笔法之说不可尽信,甚至有“几同魔术”的尖锐批评,但始终没能像沙氏这样作出简明、实在并切中要害的分析,而从正面瓦解诸多习书者执于一端的盲从心理。可见,考古学对于沙氏的书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考古学,一方面是就它作为“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而言,另一方面则是就它作为“沙盂海个人的学术背景”而言的。在沙氏一生的学术研究和艺术生涯中,考古学始终是其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诸多考古学者也与沙氏有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沙氏在1952年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文物调查组组长之后,直接参与到考占发掘工作中,对浙江的考古事业具有开创之功。并且,沙孟海也是最早将考古学知识、考古学方法运用于书法研究的学者书家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已借鉴考古发现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碑帖的书手与刻手”等问题上颇有创见。关于执笔法的探讨,可以说是沙氏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再次结合考古发现进行书学研究的又一成功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