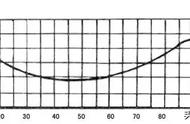01
走进都市
一九六九年六七月间,晴朗的蓝天上,几朵雪白的云正悠悠然朝着东方滑移,像是迎接初升的太阳。
喜鹊在“喳喳”地叫着,它们从椿树上飞到屋顶上,从屋顶上又飞到大院东边的枣树林里。几只华丽的小鸟也在椿树枝丫上飞来跳去地凑热闹,“叽叽啾啾”唱着动听的歌曲,音符有长有短,节奏时快时慢。
平时很爱干净的老妇人把院子里和大门口扫得比往常更干净了,她又特意洒了清水,空气里透着一股泥土的清香,让人感到非常清爽。
今天杨玉梅没有到队里干活,她正在小屋里拾掇自己。她换下了平日里常穿的红条纹粗布上衣、白粗布裤子,穿上玫红色的确凉短袖衣服和一条浅灰色凡立丁裤子。要知道,这套衣服可是从远方大都市带回来的,小县城和农村的人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穿了。
玉梅开心地把垂到衣服下边的辫子甩来甩去,羞怯地站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笑了。镜子里的人好陌生呀,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自己!她不由地哼起了《朝阳沟》里的曲调“难忘我今日里……”
她的心要飞了,飞到遥远的大都市,那里有火车、汽车,有楼房、工厂。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去地里锄草、上粪、推水车、拉平车、割麦打场;再也不用怕火辣辣的太阳把她美丽的脸晒得像非洲人一样;再也不用织布纺花、鞋底做鞋帮,因为她以后就穿当时刚时兴的塑料底皮鞋了,就像现在脚上穿的一样。
她家就住在村南边第一排房,大门外有一条小河,河里水不多,但清水常流。小河那边就是队里的一大片玉米地,今年玉米长势很好,生产队社员们都在玉米地里拔草。一个大嫂问:“今天咋没见玉梅呀?”“玉梅不来多冷清,没人给咱们讲故事了。”“是不是相亲了?”话音不落,一个女孩疯跑过来,气喘吁吁:“快……快去看吧!玉梅家来了两个人。”
“来两个人有什么稀罕?”
“一个老婆婆和一个高个子洋小子。”
人们“哇”的一声都跑出玉米地,一窝蜂涌到玉梅家。有的假装上厕所,有的说来喝口水。这些男女老少先后进了屋子里,果然屋里坐着一个高个子青年。他头戴一顶白色太阳帽,戴着黑色墨镜,身穿一件包着黄边的水红色背心、一条灰色喇叭裤,最惹眼的是他手腕上那只锃堂的手表。
“你是从哪来的?”“你来俺村干啥了?”“你是玉梅的什么人?”……众乡亲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逗得小伙子很不好意思,他极力地应付着,“我,我们是同学。”“哟,同学呀,俺们咋没听说过?”他一直低着头,不敢看这些人,宽大的墨镜也遮不住他一脸的窘态。
这门亲事是前一阵亲戚提的,小伙子叫金川,老家媒人说他是西安哪个钻探队的技术员还是专家,媒人也弄不明白。只说是小伙子的假期快到了,双方约定好今天九点让玉梅随金川坐车先到白河,坐船过黄河,坐火车到西安。
儿行千里,最放心不下的是父母。爹妈把玉梅送到村东头的珠龙河桥头上。桥下边有一群赤身的小孩儿在打水仗,看见这个洋男子喊了起来“骑洋车戴手表,不打粮食你吃屌。”“你走吧不送你,鸡蛋壳合住你,格叉棍顶住你,驴粪蛋供奉你。”
“他们说什么?”金川听不懂他们说啥。
“他们说送送你。”
“玉梅,”母亲抹着眼泪说,“妈不放心,也不知道你去的什么地方。”玉梅上了汽车,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坐汽车。
车开了,越走越远了,母亲还站在桥上擦泪。母亲知道女儿心野,玉梅上学时,有一次部队来挑女兵,玉梅第一个报了名。当玉梅把这喜讯告诉母亲时,劈头盖脸挨了一顿臭骂:“小女孩儿家不说本本分分的在家织布纺花,心咋那么野!”玉梅央求道:“人往高处走嘛。人家争都争不上,妈,你就让我去吧。我报了名了,星期三去公社体检哩。”“报名也不准去,谁想去叫人家去,咱不去。你要敢去当兵,你今天走,明天我就上吊!”年轻的玉梅经不住母亲的吓唬,也只好作罢。老人家一边往回走,一边自言自语:“唉,走吧,女大不中留呀。”
02
追梦
两天一夜的行程,第二天晚上八点多到了大都市西安。美丽的西安火车站,宽阔而干净。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操着各种口音,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来往往,买票排队上车下车。偶尔有一群或几个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老外“叽哩咕噜”不知说的什么。还有一些皮肤黑得像锅底的人,一说话露出一嘴洁白的牙齿,让人看着害怕。
这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语言,玉梅就好像是到了外国。因为在这之前,她连县城也没有去过。她心里矛盾复杂,忐忑不安,她不知道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前方是天堂还是魔窟。一阵微凉的晚风拂面,她蓦然回神,立马劝慰自己,大城市是你日思夜梦的地方,现在你也是这个大都市的一员了。
她跟着前边这个男人走在解放大道上,林立的洋楼、雄伟的城墙、古钟楼,大燕塔、小燕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玉梅和身边这个男人认识也才三四天,他们还没有单独谈过话,玉梅不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和她交谈,她甚至怀疑这个男人会不会神质不健全。现在她只知道眼前这个以后会和她一起生活的高大男子,名叫“王金川”。
他在前边走,她就跟距他三四米的后面拐来拐去,金川进了一个小巷,她跟着他进了小巷。金川走进一个小屋子,她就立在门口。门口外横七竖八地躺着乘凉的人,赤身裸体的、穿短裤的、背心的、手里拿着扇子摇着的。
金川放下行李好半天也没叫玉梅进屋,玉梅也一直站在门口。从屋里出来一个低个子男子,“进来吧,洗一下。”后来才知道他是金川的哥哥。
房子总共有十平方大,是横条形的,右边一张双人床,床上数不清睡有几个人。屋中央是一个半截柜,柜右边放一台缝纫机,屋里的空地方也仅能立两三个人。靠右墙根立着一个小梯子,是上楼用的,楼上还有一层,因房顶是斜坡式的,到楼上只能蹲着行走,是立不起身的,楼上有一张床,是大哥一家的卧室。玉梅的婆婆有五个孩子,大哥大嫂又有三个孩子,共住在这十平方的小屋子里。
西安的天气更热,屋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且不说金川在哪睡觉,就说从外地带回来的这个新娘子玉梅就没地方安插,被安排在门右边的一张躺椅上。躺椅是竹子编织的,非常凉爽,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金川把玉梅领到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有个共用水管,洗了把脸。一大片住户只有一个公用的露天厕所,上厕所要排队。
玉梅躺在躺椅上思绪万千,想起母亲说的话,想起全家人桥上送她的情境,她无言可诉。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她想不明白大都市怎么会是这样,她不知道自己路在何方,她该问谁。
屋里屎臭味、汗臭味、屁臭味让她喘不了气,浑身不舒服。她感到浑身发燥、浑身发痒。她从椅子上坐起来,翻来覆去地乱折腾。金川的母亲拉着了灯,她老人家大概知道是咋回事。她在屋里乱找,找了一个大针,又在椅子上扎起来。天哪,一种从未见过的圆虫子乱爬,他们把这虫子叫臭虫。当婆婆用大针扎了几个以后,发出一股奇怪的臭味。这种虫子爬进了椅子的缝隙里,扎是扎不完的。
玉梅凑合到天亮,看见婆婆弄了一大盆开水浇在躺椅上,然后放在太阳下面去晒。
03
西安的生活
嫂子又生了个大胖小子,他们现在已经是三儿一女了,再加上婆婆的五个孩子,家里脏衣服大堆小堆,脏鞋脏袜子到处都是。玉梅这个从农村来的姑娘,洗洗涮涮的活不成问题,她有的是力气,做饭看孩子都是小事一桩。再说她本身就爱美,见不得哪里脏兮兮,随手都拾掇了。
丈夫金川回到西安只停了三天就上班走了,婆婆托人给金川和玉梅办了结婚证。结婚还算有点小仪式,炒了四盘菜,让本家和亲戚老乡坐了一会儿。新房没什么布置——房子是借的,一张床、一张桌、一床被烟烧了个大洞又补上补丁的被子。金川和玉梅彼此还很陌生,并不熟悉,结婚那天,他带着玉梅去新庆园划了一回小船,这也许就是他们结婚时单独在一起最浪漫的回忆了。
不久大哥、大嫂要调到河南“五三一”工作,临走时把只有两个月大的孩子和另一个四岁的孩子都留在了西安,让玉梅帮忙带。玉梅明白现在想找工作是无望了,帮哥嫂看孩子就是正事。公婆还要上班,家里的弟弟妹妹还小正在上学,她的生活被繁重的家务填满,她哭了多次想回老家,可是已经身怀有孕,回家已成奢望。
这天,玉梅又在收拾那些脏衣服、脏鞋袜,倒腾了一大堆准备去洗,可用水不方便,要到百米之外的公用水管去提,她拖着*七个多月的身子,也不知提了多少桶水,从早上一直洗到下午两点多。下午收完衣服觉得不舒服,吃了晚饭早早去睡觉了,可怎么也睡不着,肚子开始一阵阵地疼痛。因是头胎没有经验,只感觉要解大便,公厕很远,到厕所还要排队,解不了大便又回来,回来又去,反反复复折腾一晚上,一夜没睡。
正好这段时间嫂子休假在家,一直到早上八点钟玉梅发现见红了,她才去告诉嫂子。嫂子吃惊地说:“啊,那是快要生了,走,赶快到医院去。”当时家里也没有别人,更没有什么代步工具,一路疼一路走到了医院,嫂子就回家照顾自己的几个孩子了。她身边没有一个人,痛苦地承受着一阵接一阵的疼痛。从昨晚一直熬到十二点,没有喝一口水,终于艰难地生下了一个女孩子。
她松了口气,闭上眼睛想要休息一下。但因胎盘没有娩出,医生一直在她肚子上按来按去,突然听到“唉呀”一声,“还有一个,肚子里还有一个娃,是双胞胎!”玉梅顿时像要死了一样没了一丝力气,昏迷中求医生说:“求求医生,我不生了,不想再生了。”医生说:“你怎么这么傻,哪能不生,谁也不能替你生孩子呀。”天哪,金川呀,你在哪里,有谁能帮帮我呀?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她除了咬着牙,拼命孤身生下另一个孩子,别无选择。两个都是女孩,大的三斤六两,小的五斤四两,生日是三月初六。
因是早产没有准备,弄脏了被单,护士大发雷霆,赶着让她出院。几天来身边没人照顾,连一口开水也没人打。邻床的家人帮着打点。有好心人给了她几块面包蛋糕,她肚子饿,几口就吃掉了。同病房的产妇都有丈夫、婆婆、娘家母亲陪着,只有她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病房里有时寂静的连掉根针也能听见;有时也能听到婴儿的哭声,婴儿都在暧室里,只要一个啼哭,全员齐鸣,就像一群青蛙在叫,但她觉得那是歌声,很悦耳,让她不再寂寞。
第六天,婆婆到医院办出院手续,当玉梅看到手里出生证上“大女已亡”四个字时,呆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强迫自己定了定神,可那四个字老在她眼前跳动,她望着婆婆:“怎么回事?”婆婆告诉她:”大的生下来就有病,我们没有告诉你。”她心里很纳闷,没有听说孩子有病,即使是有病丢了,医生也该给她说一声呀。她怎么也难以相信自己的大女儿死了,这件事至今始终是个谜。
04
家暴
玉梅的老公爹是个低矮瘦弱的老人,皮肤黑黑的,一双大眼皮双了好多层。他有五男一女,他在市外上班,每周六下午回来,回来时总要带一些孩子们爱吃的东西,然后就坐在屋门口盯着儿媳们看,等着媳妇们叫“大大”。大儿媳没那习惯,就是不叫他,气得他到婆婆面前发牢*。婆婆煮了一大锅排骨让全家吃,这也是公公回来带的,全家人都解了馋。可老四每到周六下午就发愁,老四说:“你们都过星期天,我又要过难关了。”
晚饭后玉梅带着孩子们去看电影了,影剧院热得人上不来气,今天演的是《柳暗花明》,躁动的人们安静了下来,剧情正高潮时,突然停电了,人们又乱烘烘地跑出来,小弟弟、小侄儿吵着要喝水。
这时,玉梅带着孩子们回家喝水,当她推开门时惊呆了,惨不忍睹的一幕出现在她眼前:老四弟被头朝下、脚朝上吊在房梁上,还是赤身裸体的,他大汗淋漓,身上伤痕流着血。老公公手里拿着正在冒烟的粗香头,往他的儿子身上一下又一下地烫。老四惨叫着:“大大,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他的母亲就坐在旁边看着,很坦然,好像没看见一样,似乎老四根本不是她的儿子。玉梅忙往后退了一步,把门又关上了。惨叫声传到了外边,邻屋大叔推门进去劝:“老哥,不敢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还没等大叔把话说完,老公爹“扑嗵”一声跪在大叔面前,用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求求你,别管我家的事行不行?!”老公爹又是作揖又是磕头,邻屋大叔也只好走开了。
老四身上的伤痕无数,新旧伤都在往下淌血水,汗水、泪水一起往下流。狠心的父亲还在继续,儿子的惨叫声还在继续……
家暴已经习以为常了。那天玉梅在楼上哄孩子睡觉,老四的叫声又开始了,“唉哟,不敢了,轻点吧!”孩子被吓得直哭。老公爹打人是不让人劝的。玉梅要从楼上下来也不行,老公爹已经把下楼的活动梯搬走了。一直到老人家无力坐到地上,玉梅才下楼来。
又一次玉梅刚进门,老四“扑嗵”一下跪在她面前,“嫂子,求你给咱大讲一下情吧,让他今天饶我一回吧。”玉梅不知如何是好,手忙脚乱地说:“我试一下吧。”老头子一回来就坐在门口。看着老四上下打量,一张阴沉的脸上带几分凶气,暴风雨马上就到来的感觉。玉梅把女儿抱起放在老公公手里,“大大,我去做饭,你先抱抱孩子。”老头子接过孙女,脸上从阴转了晴。这天老四过了一个快乐的星期天。以后仍然照打不误。
后来听邻居们讲,他家的几个儿子也都是这样成长的,刑法可多样化了,把老三儿子打得昏迷过去用凉水浇醒再打,用大针扎身上的肉,板上钉钉子打,用剪刀剪肉,灌辣椒水……打完了,他会问孩子“疼不疼?”,如果不回话,会把他挷到床上用小勺别牙齿。玉梅的丈夫金川也不例外。直至现在也不知当时这些孩子们犯的什么错,奇怪的是弟兄们没有一个记仇,从没有说过挨打事情,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要不是玉梅亲眼所见,她真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家暴。
05
在煤矿的日子里
一九七二年四月末的一天,阴沉的天空洒着罗面雨。玉梅抱着两个月的孩子,去找孩子的爸爸金川。金川还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玉梅坐月子的时候,他没能回去。去的时候婆婆把她母女俩送到钢川车站,又坐客车到崔家沟煤矿。金川到站去接她娘俩。翻了一架山又过了一条沟也没看见钻探队。再往前走过了一个小土丘,才看见对面有人走过来和金川打招呼:“接媳妇了!”
玉梅跟着丈夫进了一间小屋子——一个破得不能再破的小屋,阴暗潮湿,十字架支了一个小窗户,只有一张小床。金川专门从钢川买了一个闹钟放在窗台上,滴滴嗒嗒地响着,连屋子里也闻到一股煤灰味。一觉醒来发现窗户纸被听房的人撕破了。闹钟也被人偷走了,金川怀疑是房东吵了一架,结果被房东赶了出来。
后来金川和李师傅商量在山半坡朝阳地方合伙各挖了一孔小窑洞,还有一个小院子,屋边栽上了小树,旁边还有一个小灶房,垒了一个小灶台。非常有生活情趣,像是小时候孩子们过家家。
玉梅和邻居李嫂也成了好朋友,谁家做好吃的,都要给对方送点,心里有苦了也相互倾诉。李嫂的一条腿是丈夫给打断的。他们这些矿工不是正式工,都是劳教人员,犯了错误下放到煤矿改造的。有的是走资派,有的是红卫兵、造反派,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富农。甚至有的是因为名字起的太反动了,比如说“蒋成立”……土匪、流氓、懒汉,啥人都有,如今玉梅才知道上当了,原来金川根本不是什么钻探队的技术员,可以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这天,玉梅端着饺子给李嫂送,老李端着碗跪在媳妇跟前,左一个小宝贝,右一个小乖乖给李嫂赔礼,李嫂只是哭。老李一口一口喂媳妇。听说矿上的人把媳妇往死里打,过后又低三下四求媳妇原谅。金川也是个能干能打的人,才当上班长,他的外号就叫“老虎屁股”。
有一次,金川和玉梅正在西安大街上走,玉梅看见一个熟人,大个子,很是帅气,一个漂亮的女孩挽着他胳膊。当他扭脸看见玉梅和金川时,先是笑了笑,准备打招呼说话,可又止住了。玉梅看着那个人也没说话,她和金川一直朝前走有二十米的地方,玉梅才说:“你为什么不和刘太东说话呀?”“啊?刘太东,他在哪?我没看见。”都是在矿上又都回来西安,见了面本该是很亲热的。玉梅指了一下刘太东站的地方,金川把手里提的东西递给玉梅,一个人直冲马路对面,差点撞上一个三轮车。金川冲向大个子青年:“刘太东别走!”金川抓住刘太东领口,刘太东吓得不知说啥好,让他女朋友先回去。女朋友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哭。金川把刘太东送进了派出所,他说他知道刘太东是没请假偷跑回来的。玉梅只是后悔不该和那人说话,不该把这事告诉金川,真对不起刘太东和那位漂亮的女孩。也难怪人们都说金川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一大早金川做好早饭,家里仅有一个玉米面馍,他没舍得吃,把馍放在灶台上烤得焦黄给玉梅留着。这时山下有人喊:“金川,团部柴队长叫你下来一下。”“柴队长叫我干啥?”“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好的,我马上就到。”金川金子般的男高音在山崖边回荡着。
玉梅赶快起来,站在山崖边看着丈夫一溜烟似的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玉梅想着,说是今天去钢川给孩子照百天相,现在又跑了。
谁曾想,这一走就是两年。
原来在一九七一年的某一天,金川像平常一样带着工友们在井下干活,打炮眼。下午快要下班了,金川走出洞口摆弄着放炮器,多数人都出了井口,只有刘国斌和杨海还在里边工作。准备工作做好后,金川又进去让那两位工人上来,马上准备放炮了。金川刚走进工作面,“轰隆隆”,炮声响了,井下一片漆黑,三人全被煤层埋在下面,生死未卜。当人们赶来救援后,已是一死两伤。刘国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年仅二十六岁。后来查明真相,是一个叫杨人的矿工,他违规操作按响了放炮器,金川是当班班长,当时又正值安全大检查,杨人和金川就是在那天的安全大会上被带走的。
06
别泪
自从金川那天离开了家,玉梅再也没见过他,她要疯了,整天以泪洗面,不吃不喝,整天呆呆地坐着,有时哭一阵子。她真的不能没有他,晚上她还在听他下班回来,她好像听到了他熟悉的脚步声;白天她常坐在门前那个石头上看着他常回家的那条小路,她相信自己一定能等到他回来。她总是听到他吹口琴的声音,一会儿又听见他在唱《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唱段,声音依旧那样浓厚熟悉,这段戏是他的拿手戏,他高亢的男高音在山间回荡;有时她又闻到他的烟味,看见他的身影在大石头边一闪而过。
山坡下那条河对面是厂部,有篮球场,人们在打球,玉梅又在球场搜寻金川的身影。忽然她看见金川在人群中穿来跑去抢球投篮。对,那个穿黄背心、蓝裤子的就是她的金川,她坚信自己的眼睛,她的金川回来了!她飞似的冲下山,趟过那条小河奔到球场上,却找不到她的金川了。她漫无目的地走着,嘴里念唠着:金川,你在哪,一走就再也不见你了。有时她又以为自己在做梦。
那天晚上影剧院上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珍妮探监看哥哥那场戏,她觉得分明是在演自己,看着看着她失声痛哭起来,因为团部通知她明天去探望金川。她要去见亲人了,她要把委屈和许多话对他说。
第二天热得很,矿部派张健帮她抱孩子,陪同她一起去探监。孩子闹了一路,因好多天吃不下饭,玉梅瘦了很多。到了铜川下车后,玉梅少气无力地跟在张健后面。记得那天她只吃了八根冰棍,其它什么东西也咽不下。
进了监狱的大门,里边的人安排他俩在门口等,他们进里面带人。金川被他们带出来了,人家交待“见面只能谈五分钟,你们要抓紧时间”。眼前的金川瘦了许多,两人相见后面对面站着,谁也不说一句话,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张健说:“抱抱孩子吧。”把孩子塞进了金川怀里。“孩子脸上这么多红疙瘩,是蚊子咬的吧?”“嗯。”小家伙一路闹腾,现在见了她爸又睡着了,摇也摇不醒。
“五分钟到了,结束谈话!”金川又被人领走了。玉梅瘫坐在地上。亲人呀,我怎样才能留住你呀!
得知金川判刑两年后,她要回家了。这几个月来玉梅带着孩子,大人又没粮吃,都是众人送的。小孩子没奶吃,也是朋友送的,玉梅没什么还人家,就帮大家洗衣、缝补衣服,还大伙的情。
矿领导很内疚,不应该叫家属亲眼经历这种不幸。矿领导特意给她申请了三十元路费。她抱着孩子怯生生地走进领导办公室,说明来意,那位干部站起来吼道:“你怎么有脸要钱呀,你男人是犯人,是犯了法的罪人,可不是战场上的英雄!”……他说了一大堆很难听的话。玉梅辩解道:“他是因为工作失误犯的法,我不是犯人吧,我是贫下中农的好子女,我是好公民,我是优秀共青团员,我有啥罪,你这样吼我!我家离这儿远,这是领导照顾我申请的钱,你不给就算了。”那人站起来走了出去,回来时态度一下变了,他用温和的口气说:“给你批了三十五元,路远还带着孩子,不容易呀。”此刻,玉梅的情绪突然闸不住了,心酸、委屈的她失声痛哭:“我不要了。”抱起孩子要走。“哎,哎,别走,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不对,多给你批五元钱。”他拉着玉梅,硬把装钱的信封塞给了她,问:“坐下,你是哪里人?”玉梅擦了把泪,“河南人。”
“河南什么地方?”“沁阳。”
“沁阳哪公社?”“崇义。”
“崇义哪村?”“水运。”
“啊,咱们不但是老乡,还是一个村的。你男人叫王金川,我叫王金辉,我们还是一辈的。”
“怎么这么巧呀。”玉梅心里很不是味儿。
“你什么时候走呀?”“就这几天。”
“明天有拉煤车往西安去,六点多你到厂部食堂门口等。”
第二天清早,玉梅告别了她亲爱的土窑洞,那是金川一铁锹一铁锹挖的,冬暖夏凉,又干净又美观。来到食堂门口,想不到正在吃饭的百十个人同时放下碗,全部站起来,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玉梅,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他们把她送上了那个拉煤车,车开了,他们一起挥手向她说“再见”。
07
画梦
都说崔家沟是一个劳教所,却不知这里更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汇聚了全国各地带罪的精英人才。玉梅在那里的日子里,就认识了不少有才华的青年。谢青松,上海上浦画世家;张万林,北京京剧演员;高帅,剧作家;高塬,西安籍诗人;张辉,造反派头头,二十八岁副县长……不见不知道,亲眼目睹了这些还未成家的二十多岁青年,青春而幼稚,一点也不像坏人。他们被下放到整天不见天日的矿井下改造,他们也有远大理想和梦想,他们也渴望爱情,盼望阳光,但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在很遥远的地方,都是虚无缥缈的梦。
井下矿工,断胳膊断腿是常有的事,有的没了手脚,有的毁了容,更有的为了煤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也随之消失,没有人记得。
京剧演员张万林保存了三百多张漂亮姑娘的照片,据说有许多都是他谈过的对象。他向玉梅表白,现在只要能找个农村的,哪怕是讨饭的、离婚的、寡妇,自己也愿意,玉梅懂得他的意思,故意岔开话题应付他。
这天,张万林拿来一本《红楼梦》和那些姑娘的照片,玉梅非常担心这些人的到来。这些事还就真的来了,张万林把手搭在玉梅的肩头上,玉梅像触电一样跳起来,“把手放下,规矩些!”
张健从山下挑水进来,他是金川最要好的朋友,自从金川离开后,过上几天他总要担一担水上来,总担心粮票和孩子的奶粉。张健把水倒入水缸里,沉着脸问张万林:“你来干啥?”“我来给嫂子送书的。”每当这些男人来时,玉梅总是借故去李嫂家,有时也弄得好朋友没趣。
谢青松的画太漂亮了,她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拿来两个大画夹,他的画太多了,她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有一张自画像,一片松林深处有一个草棚和一堆破被子,窝棚旁边的草丛中一头野狼,正看着他的行动,他坐在铺盖卷上看着它流泪。还有一张是狼蹲在那里,他钻在被窝里,背景是冬天,身旁是雪,眼角往下流着两行泪。她深深地被他的画感染了,决心要学画画。青松从上海回来给她捎了“九宫格”,教她先画人物。还带来了许多火腿肠和咖啡。这时她好像淡忘了思念丈夫的痛苦。
那天她正在洗头,当她把长发往后一甩的瞬间,张万林突然抱住了她,“你太像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的白桃花了,我要画你,我太爱你了,尤其是甩头发的动作最像了。”玉梅扒开了他的手,“谢老师,我尊重你,你是知识分子,又是共产党员,请你自重。”他松了手。“青松,我把你看成亲弟弟,咱不能对不起我的丈夫。”“对不起,姐姐。因为我喜欢你,刚才……我要画你。”“可以。”
他为她画了许多姿态各异的肖像画,给小孩也画了好多。他教她画画的技艺要领。谢青松高高的个子,衣着整洁大方,朴素雅致。戴一幅眼镜,文质彬彬,说一口北京话,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洋气高贵。她知道谢青松喜欢自己,她也喜欢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谢老师,但,她不能对不起丈夫,不能见异思迁。他心中的丈夫比谁都好,无人能比。丈夫是她心中的英雄,尽管当初他骗了她,尽管他鲁莽地像张飞,她早已从内心接纳了他,无法改变,无人替代。
08
雪上加霜
七二年秋末,玉梅在哥嫂的安排下,带着孩子来到河南孟县机械厂。这下离母亲又近了,孩子可以撇给母亲来带,金川的事情也没敢告诉母亲。为了感谢哥嫂,每月二十八元的工资,都如数交给了他们;下班回来就帮哥嫂料理家务、洗衣、担水、做饭、看孩子。生活有了着落,也有了盼头,心里也有了些许的安慰。
天有不测风云,突然有一天母亲托人捎信“父亲病重”。母亲一贯是报喜不报忧,玉梅一刻也不敢耽搁,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时,亲爱的父亲已经再没说出一句话,再也没睁眼睛了。全家人跪下给医生磕头,但一切已无济于事,医生说:“看得太迟了,人不行了。”玉梅跪倒在父亲的病床前泪如雨下,老天啊,你为什么不睁眼?命运呀,你为什么如此不公?生活哪,你为什么对我这般残酷?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吗?为什么厄运偏偏降在我们家!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可活着的人生活还要继续。三个妹妹两个弟弟都还小,家里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玉梅把自己仅有的五十元钱拿出来,和母亲一起安葬了父亲。
这个月,二十八元工资没有上交给哥嫂,哥嫂立马翻脸了,把玉梅分出了家。母亲知道后,带着年幼的孩子,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一大麻包玉米,从沁阳用平车送到玉梅所在的机械厂,让她换粮票吃饭。因为没地方放,玉梅把玉米寄放在哥嫂家。当玉梅去用时发现玉米已被哥嫂卖得一粒不剩了。玉梅和他们讲理,这个可惹恼了婆家人,他们根本不和她说理,甚至就要使暴了,可怜的玉梅只好作罢。
盼星星,盼月亮,七四年丈夫终于刑满释放回来。但玉梅并没有盼回来救世主,金川回来后先去见了哥嫂,再回来见到玉梅后就不那么友好了。玉梅还未来得及对丈夫诉一诉委屈,金川直接取下身的皮带抽打在玉梅身上,边打边吼:“你哭,你哭,我叫你哭个够!”玉梅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尿失禁尿到床上。“你这样懒,我打死你!”不由分说对着玉梅又是一顿毒打。想不到呀,玉梅苦心等了丈夫两年,盼他回来,没有一句安慰的话,一见面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厂里领导和一群女工姐妹砸开门,姐妹们心疼地抱着玉梅痛哭。大家纷纷劝她:“这样没良心的东西,你和他过什么!太气人了!”
“离吧,别过了。”
“他一拉石头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凭啥打我们的人?”
“让公安局来把他挷了!”
厂长说:“写材料,我要告到公安局!”
但最终玉梅也仅是和金川分开住了,并没有把他怎么样。金川是她的丈夫,她刚刑满释放回来的丈夫,她不忍心。
09
苦尽甘来
那天下着大雨,玉梅刚从车间干活回来,正在宿舍和姐妹们织毛衣。姐妹们还劝她:“不给他织毛衣,那没良心的,把你打成那样,你真是不长心。”玉梅无言反驳,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突然,浑身湿淋淋的金川出现在女宿舍门口,他被雨淋得像刚从河里捞出来似的,衣服上水还在往下淌。“我的裤子被石头挂破了,给补一下。”他一边小声说着,一边用手抹去脸上的水。
看着金川可怜的样子,玉梅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她又心软了,没骨气地跟着金川回到了他租的房子里,给他缝补裤子,缝好后又把屋子里简单拾掇了一下。“我走呀。”“别走了,”他一把抱住玉梅,倔得像头牛的金川终于低下了他高昂的头,他知道错了,恳求玉梅晚上留下来。
晚上,当金川看到玉梅破旧的内衣已经不能遮体时,他紧紧地抱着她,“衣服真不能穿了,脱掉扔了吧。”他哭了,“这还能穿吗?”他把内衣像纸一样一缕一缕地撕掉,“给你十元钱,明天去买件新的穿上。我现在每天都能挣十来块钱,一个月就是三百块呀。”他兴奋地说:“你知道吗?咱们*一月才三百元工资。”“*是伟大领袖,你是拉石头小子,还能跟*比呀?”“*不是说,工作不分工种,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拉石头建大桥,也是建设祖国呀!”“好,你光荣,你伟大!”……
金川回来几个月了,终于抽空和玉梅回了趟她母亲家,看望岳母和自己的女儿。女儿已经两岁了,可爱极了。金川要抱她,女儿认生,怎么也不让他碰。“小宝,叫爸爸。让爸爸抱抱,给你买桔子吃。”女儿害怕地把姥姥搂得更紧了,“他不是爸爸,是叔叔。我害怕叔叔,让他走,不要来咱家。”“傻孩子,这是爸爸。”玉梅接过女儿哄了半天,小女孩才让爸爸抱。血浓于水,亲情是谁也割不断的,熟稔后的女儿调皮地在爸爸的脸上拔眉毛,金川欢喜得不得了。母亲在一旁落了泪。“妈,人都回来了,你哭什么。以后咱家就要好起来了。”“你们吃啥饭,我去给你们做饭。”母亲擦着泪钻进了灶房。
一对苦命鸳鸯,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以后的日子有盼头了。
一九七三年河南孟州、吉利开始架一座黄河大桥,需用大量的石材,这对金川来说,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二十六岁的金川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买了一辆二手平车,随拉石队去北山装石头,再往黄河工地送。当地的农民工建立了一支送石队,车队排成了一条长龙,金川总是排在最前头。
“长鞭呀那个一甩哎,
叭叭响哎~,
赶起了大车出了庄,哎嗨哟……”
拉石头的工友们一个个汗流浃背,风雨无阻。从北山拉到工地一车石头一元钱,一天每人能拉五车,金川能拉六车,一个月下来能挣一百八十元,可不是个小数字。玉梅抽空也去帮丈夫拉石头。
工地上好一派繁忙的景象,大吊车伸着长有力的臂膀,吊着石头、水泥桩,铲车也在轰轰地响着。技术员、工程师忙着测量、计算。当地许多老百姓没事了就跑来看施工场面,他们也稀罕这些大型机械。
那是一段苦尽甘来的日子,也是一个充满希冀的日子。
拉石头挣到了钱,金川买了头小毛驴,金川把毛驴当宝贝一样,他在当地租了一间小草屋,小屋有多个用途,人驴同屋,做饭都在一起,玉梅还在单位宿舍住。玉梅下班回来,也帮着金川拉石头、喂牲口。送石头从工地回来,金川扬鞭坐在车前沿,玉梅坐在后边车棚里,鞭子“叭叭”甩得脆响,工友们都羡慕这对年轻的小夫妻。金川又唱起了《艳阳天》插曲:
“长鞭呀那个一甩哎,
叭叭响哎~,
赶起了大车出了庄,哎嗨哟……”
玉梅也在后面跟着哼。不折不扣的男高音在群山间回荡,好幸福!
玉梅平时在工厂上班,下班回到宿舍抽空就赶着织毛衣,还让同事帮着织衣袖。天冷了,可不能冻着自己的丈夫。毛衣终于完工了,她感谢工友:“小荣、小英,谢谢您们帮我,要不我还得好多天才能织成。我去给你姐夫送毛衣呀,回来捎好吃的犒劳你们。”
“你去吧,晚上不要回来了,就住在那儿吧。”小荣说。
“我才不住他的烂驴棚呢。”玉梅言不由衷还嘴硬。
“我看不由你,要不咱打个赌,到那儿你准回不来。”
“去吧,快去吧,去给老公暖被窝吧。”女工宿舍里笑声一片。
玉梅把毛衣送给金川时,金川穿着那件枣红色毛衣,简直变了个人,帅呆了!这才是玉梅心里那个高大威猛的男人。
10
婚变
这天街上乱哄哄的,有人在喊救命。大街两旁站了许多人,没有硬化的街面上刚下过一场大雨,路中央四个人扭打在一起。三个人把一个人摁倒在泥窝里翻来滚去。这是金川和他大哥、大嫂拿一根绳子,要捆老四兄弟,金川穿着深筒胶鞋,他们对着老四又踢又打,老四像泥母猪一样在泥窝里挣扎,发出*猪般的嚎叫。当玉梅赶来劝阻时,金川瞪着吃人的眼睛:“滚几八远一点。”两边街道的人们只是观看议论,没人敢去拉一把,因为“是人家家务事”。老四被挷在一棵大榆树上,哭喊着。
第二天,老四终于病了,发着高烧,玉梅在灶房烧了一碗鸡蛋面送给老四时,他嘴里还在喊着:“这个仇我非报不可,王金川,你记着。”
“吃吧,以后你好好上班不就行了吗。”玉梅说,“我走了。”
玉梅刚转过身,就被金川堵在门口,“你他妈的来这儿干啥?来这卖好哩!*的小心你……”玉梅没理他,侧身挤了出去。
前些日子,金川也托人进了这个机械厂,且和玉梅分在了一个车间。
玉梅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犯胃疼,前一晚和金川商量好,准备今天抽空做胃镜。因车间有点紧活,要干完才可以去医院。金川却走过来说:“玉梅,给你商量个事,咱们明天再去医院吧,春香要我带她去有点事。她那人张开口了,我不能不去,咱惹不起,他哥在厂部是劳资处长。”玉梅气愤地说:“咋了,劳资处长是她哥又怎样?再说人家没有男人?你为啥要陪他去?不行,昨天说好的……你你……”
“老哥,走呀!你咋那么慢呀!”春香在门外喊叫着。
“来了!”金川不管玉梅的感受,骑上摩托车,带上春香,绝尘而去。换作是别人,玉梅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火气,但这人是春香,那就不会是什么正经事。
春香是这里出了名的浪荡女人,不但衣着暴露,张口就是低级下流、不堪入耳的话;但在男人面前嘴又甜得像抹了蜜,“老哥老哥”,不叫哥不说话,金川被她叫得是心花怒放,神魂颠倒,不知东西。他们之间很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经常凑在一起说些低级下流的话和被窝里的话,偏偏金川就是爱听,听得哈哈大笑,他非常喜欢这个风流的小妹。时间久了,金川下班都不想回家,春香也不回家。她不管有人没人就往金川的怀里靠,根本不在乎玉梅的存在;一天要换好几身衣裳,每换一件都要在金川面前臭美一番。她还经常让金川和她一起上夜班,让金川替她干活。她晚上偷厂里的木料,让会做木工的金川给她做了两个柜子和一张床。她从不买菜,见了人家卖菜、卖水果的就连偷带拿。春香让金川晚上十一点去修缝纫机,他就不敢不听。
金川觉得这个小妹太有情趣,太有本事了,自己的女人变得一无是处。春香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和你老婆生活在一起,连自行车都不敢骑,就她的命主贵。”他照搬不误把老婆骂了顿:“就你的命主贵,别人都不怕死,要你我瞎了眼了!你看春香想要什么都能弄得来,人家没掏一分钱做了几件家具,你敢不敢?”玉梅反驳说:“她什么都是好的,放个屁也是香的。偷人的事,我不会干!”“你能干啥?你就是个搅屎棍、吃醋王。她咋你了,你为啥那么恨她?这日子过不成了!”他抡起斧头砸了茶几、缝纫机和衣柜,“离婚,走!”
那天金川一回家,就把平时最亲的小儿子挤到柜角处,“啪啪”扇了几耳巴,“我打死你,你怎么那么材坏!”
“怎么了,爸爸?”孩子双手抱着头,惊恐地看着爸爸。
“谁叫你站到门口往下尿,你故意尿到人家春香头上!”接着又是一顿暴打。
“爸爸,我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孩子的辩解只会助长金川的怒气。
“你疯了,你把孩子打成这个样。”玉梅也疯一样地护着孩子,替孩子挡着他爸的棍子。“她放个屁你都信,你听着你把孩子打成这。那一次她说孩子放了别人自行车气,你就把砖立在那里,让孩子跪在车间。你和那个浪女人在孩子面前打情骂俏、哈哈大笑。你是不是孩子的亲爸!
金川“啪啪”打自己的耳光,一边说一边哭:“我不活了,受不了!”他把头往墙上撞,在屋里到处找绳子要上吊。孩子们吓地哭叫着:“爸爸不敢,不敢呀!”孩子们跪着求他,他又操起菜刀吼道:“都跪着别动,谁敢再叫唤阻拦我,全家人一个都别想活!”
此刻的玉梅反而很冷静,不害怕,全家人都在等待惨案的发生。他真的挽好了绳结把自己吊了起来。玉梅软瘫在沙发上没动。倒是孩子们到处找剪刀、找刀,哭着喊着“爸爸呀,爸爸呀!妈妈呀,快救爸爸呀!”他被吊得难受,玉梅找到菜刀把绳子割断,金川跌坐在地上,孩子们赶快给他喂水。他一直“咔咔”咳嗽。他又拿起一把椅子砸自己的头,孩子们夺掉后,他自己站起来,冲向大雨瓢泼的夜幕中。出走对他来说已是习以为常了,孩子们努力也是无效的。
一天金川突然回来说:“走,离婚。”玉梅还以为他像以前一样说气话吓唬人,没有理他,他更来劲了:“快点,这次谁要不离,不是她娘养的……”玉梅放下手中的活,和他一起走进厂办公室,“处长,给我们开个证明。”处长就是春香的哥哥,他笑着说:“开什么证明呀?”金川更嚣张了:“离婚证明,不能过了!她妈的,我遇到个搅屎棍、扫帚星……”处长没好气地说:“你咋是这个样呀,现在是在我办公室,你就骂人家一大堆,一个大男人哪有这样骂自己老婆的?可想你在家里是怎样的横行。”金川原以为处长是自己人——情妇春香的哥哥,想不到人家不但不向着他,反而把他批评了一顿。
玉梅为了孩子们本不想离婚,看来这次他的心真的变了,不单是家暴那么简单了,丈夫的外遇比家暴更折磨人。她咬咬牙,和金川走进了民政局……
11
自食其果
金川如愿和春香走到了一起,他们终于达成自己的目标和心愿。两人形影不离,幸福到了极点。金川情愿包揽所有家务,情愿为春香按摩洗脚。他喜欢听春香撒娇,并现学为春香做她最爱吃的几道菜。两人经常手牵着手出现在人多的地方,还故意抱着亲几口。“真够浪漫的”,众人都看不惯,背地里骂他们:“不要脸,为啥不在家情情气哩!”
金川想儿子了,对春香说:“明天星期天,叫我儿子小丰也过来吧?”春香满口答应:“太好了,让你儿子小丰和我儿子小兵一起玩,咱明天重吃啤酒鸡。”
中午金川在厨房做菜,他光膀子大汗淋漓,春香把做好的啤酒鸡端放在桌上,摆好碗筷。金川发现小丰碗里是鸡头,小兵碗里是鸡腿,有些不高兴。没等小兵吃完,春香又往小兵碗里夹另一个鸡腿。这下气坏了金川,他掀翻了桌子:“你她妈的也太不像话了吧!”春香也不甘示弱:“你找事哩,我让你儿子来我家吃饭就是高看他了!这鸡是我掏钱买的!”
“自从我来到这里,把每月工资交给你。”
“交给我是应该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弄的鸡没让你吃?”
“别说你弄来的鸡了,一股贼腥味。”因为这鸡是春香偷偷在别人家鸡窝里掏的。这下春香不愿意了,上前打了金川,两个人扭打成一团,两个孩子在一旁哭。
尽管金川对春香再好,可是他每个月上班的死工资哪满足得了好吃懒做,花钱如流水的老婆。她依然偷鸡拔白菜家常便饭,进舞厅入赌场随心所欲。哪个有钱男人只要被她瞄上了,想方设法也得让你把钱装在她的口袋里,人家就有这个本事。
她认识某公司的老板夫妇,整天姐长哥短地叫着,想法子亲近他们。老板夫人叫利红,是公司的会计,妩媚得像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春香经常和她出入赌场。财务科每天要收大量现金,利红为了省事,经常偷懒把这些钱随身背在包里,而春香总是殷勤地替她背包。可交账时总是短几百元钱,利红是个马大哈,也不想那么多,不够了就自己往里面添上几张。时间久了也有点怀疑春香。
有一次,春香和几个女人在利红家打牌。利红刚买了件衣服有点小,对春香说:“春香姐,我买了衣服,样子和布料都很好,就是小了,你去试一下。”“好,在哪里?”“在我卧室大柜把手上挂着。”屋里其他人都在打牌,春香穿了衣服正要照镜子,突然发现衣服口袋里有一摞钱,赶紧随手装进自己的内裤里。这时利红突然想起口袋里有钱,马上跑过去,看见春香正往身上塞东西。利红慌忙问春香:“口袋里的钱呢?”春香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口袋里乱掏,“没有呀,哪有钱?你看,我可是刚把衣服穿上,扣子还没扣上呢。”利红吃惊地瞪着一双大眼睛,“那就奇了怪了,我往衣服里放了五千元,这是明天给工人发工资的钱。”利红急了,又在口袋里摸了一遍没摸到钱,生气地吼道:“我就不相信钱会飞了!今天搜不到钱,咱们几个在场的人谁都别想走!”场面很尴尬,大伙心里都有底。可春香坐在地上又哭又骂又撒泼赌咒。利红不忍心,又放走了这个贼。
春香每回下手都能得逞,贼胆就更大了。又有一次在一对盲人夫妇家里打牌。柜子里放着这对夫妇摆地摊算卦积攒的八万元钱,装在一个花布包里压在衣服下面。打牌人散了,盲人妻子去取钱发现连包带钱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人们都猜是春香拿的,盲人夫妇好话说尽,春香就是不承认。这位盲人老太太坐在春香家门口指名道姓骂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用,无奈只好报了案。最后公安在春香家搜出了那个小花布包,把这个人人喊打的贼带走了。
颜面扫地的金川,此时此刻终于想起了玉梅的好,玉梅的温柔善良,玉梅的勤劳贤惠,玉梅的知冷知热……为什么自己被狗屎糊了眼,把这么好的妻子赶出家门。
12
再续前缘
玉梅离开了伤心地,去了一个远方的城市,后来又把亲爱的老母亲也接来了。有了母亲的帮忙照顾,玉梅舒心多了,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人也精神了不少。
玉梅也有烦心事,最讨厌有人来提亲,凡是上门者不容分说,都叫玉梅一口回绝了。令人可恨的是有个陌生男子,几个月来老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起初玉梅并不在意,那天邻居叫她一起到公园转转。在公园荷花塘边的小路上迎面走来一个男子和邻居说话,玉梅往前几步要走了,邻居赶上玉梅,边走边说:“这是我表哥, XX公司的领导,家里有车有房,还有不少存款,他和老婆离婚半年了,叫我帮他找个本分的女人。”玉梅听出话中有话,忙把话题岔开了。这才想起这段时间那个男子经常出现在她视线里。
有一天在影剧院看电影,不知是碰巧,还是有人安排,那男子就坐在玉梅身边,他主动问:“你也来了?”玉梅礼貌地“啊”了一声。“老师,你今年多少岁了?”玉梅装没听见,那个男子不死心,又问了一遍。玉梅这下没好气地回击他:“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查户口呀!”弄得他非常难堪。
上班干活,下班做家务、辅导孩子学习,日子平静而祥和。
这天兴华机械厂机加工车间,正在开展一次特技比赛,比赛项目是“高速切割”。以每分钟八百转速切割直径八十五的圆钢。技工们正在作赛前准备,现在要把原来用“白钢”切刀改为“合金”切刀,由原来直形切刀改为三角带小圆,刀刃不可太锋利,要浑厚,技工要胆大心细,磨刀要讲究。这需要做到统一精准配合,缺一不可。
玉梅开始操作,车头飞快转起来,一条条铁硝像火龙一样在空中飞舞,铁硝由红变蓝,带着绿,发出耀眼的光,场面非常美观,画家也画不出的画面。玉梅享受着工作的喜悦,陶醉于这样的美景。
“杨玉梅,电话!”外边有人喊。玉梅走出车间,抓起电话:“喂,谁呀?”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是我。”玉梅的第一反应,是金川。无论分开多久,离得多远,她永远记得他的声音。玉梅没有回话。
“是我呀,你听不出来吗?”玉梅还没作声。她心里“咚咚”直跳,她已经慌了神,她不知道金川为什么现在会给她打电话。
“喂,喂!怎么不说话呀?怎么,听不见呀,我是金川,我现在已到你这里车站了。我不知你在哪住,你来接我一下吧。”对方一直在说话,玉梅已经放下了电话。由于慌乱,话机没有放好,随着耷拉下来的电话线左右摇晃着,就像玉梅此刻忐忑不安的心。她好不容易让自己忘了他,忍痛割爱把他从心里赶走了。他已经有了新欢,现在又来这里干啥?难道是出差路过?还是想孩子了?她使劲甩了甩头,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玉梅不愿去车站接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尽管她带着孩子们过得很清贫,但是工作顺利、孩子听话,生活倒也愉快。她坚决不能让他来打乱她平静的生活,她说什么也不能接纳他。玉梅从厂里回来,就一直坐在屋里的沙发上发愣。
不知何时,金川已经站在了家门口。玉梅缓缓地抬起了头,眼前的男人衣服又脏又破,人也清瘦了不少,头发也稀疏了,胡子拉碴的,她心里莫名的有点心疼。他像往常做错事回来一样对着她笑。好半天,玉梅才说:“你连声招呼都没打,现在你来干啥了?”他笑着说:“等一会我告诉你。”金川四下打量了一番,放下手中的提包,提起门口的两个桶,下楼拎了两桶煤球上来了。他把煤球加到炉子里,默默地坐在了玉梅的身边。屋子里一片寂静,许是刚换上的煤球煤气太大,玉梅忍不住咳嗽了几声,金川赶紧起身给她倒了杯热水。玉梅接在手里,也没喝,屋子里又安静了。
孩子们放学回来了,“爸爸”“爸爸”叫个不停。“来,看爸爸给你们捎了什么?”他从包里掏出两条粉红色的裙子给两个女儿,一把冲锋枪递给儿子。三个孩子又蹦又跳,丝毫没有怪爸爸的意思,好像爸爸真是出差几天刚回来。玉梅心里明白,孩子们是渴望爸爸回来的,他们不希望妈妈一个人操持整个家太辛苦,也不想成为别人嘴里“没有爸爸的野孩子”。玉梅默默地站起身进了厨房。房间里爷儿几个的欢声笑语不时飘进玉梅的耳朵。
晚餐比平时多了两个菜。饭后,孩子们吵着要一家人去看电影,但是玉梅没让去,也没有让金川留下。尽管金川苦苦请求留下来,孩子们也哭着要妈妈原谅爸爸,玉梅也哭了,但她还是咬咬牙,把金川关在了门外……
时间过得真快,孩子们又长大了一岁。
一天夜里四点多,家里电话响声打破了夜的宁静,玉梅惊慌地爬起来抓起了电话,“谁呀,这个点打电话?”“你叫玉梅吧?我是金川一个厂的。金川被机器砸住了,伤得很重。”“现在在哪?”玉梅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焦急地问:“他现在人在哪?”“正在人民医院抢救!”玉梅撂下电话,披上外套,鞋带也顾不上系,冲出家门往人民医院赶。此刻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金川呀,你千万不能有事,你一定要好起来,孩子们都在家盼着爹回来。你一定要好起来,我也会加倍对你好的……

作者简介
赵秀珍,笔名览月,女,一九四八年生于西安,后随养母在河南农村长大,现居济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