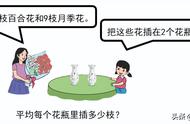2014年,春节。
武汉大学中山医院的产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她对外宣称的名字叫“陈小凤”,有着一张沉默的脸,颧骨高高突起。她很瘦,哪怕是怀着孕,也只有80几斤。
陪在她身边的只有一个男人,她的丈夫郑清明——一位普通的农民,脸上带着风吹日晒的痕迹,老实且木讷。
在和医生沟通的大多数时间里,陈小凤都缩在厚厚的被子里,露出来的一双眼睛中,坠着深深的麻木。
尽管在医生的口中,她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30周,双胞胎,身下一直在出血,还是中央型前置胎盘——
通俗一点讲,就是胎盘位于宫颈口前面,堵住了两个孩子出生的大门。用医生的话说:“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出血。”

陈小凤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医生、护士、同病房的家属,乌泱泱的人群挤在陈小凤的病床前,不知道该怎么走向下一步。
因为啥?没钱。
医生给郑清明算了笔账:因为孩子是早产,出来后需要到新生儿科观察,而产妇手术、输血都要花钱,要是一家人平安出院的话,最少也要5万块。
5万块,可以保住一大两小三条命,但郑清明掏遍了全身,只交上了5400块。
这些钱,也还是七拼八凑,借来的。

产科主任李家福与郑清明沟通
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条件,医院给陈小凤制定了最便宜的治疗方案。为了省钱,手术之后,甚至没有给她上镇痛泵。
麻醉渐退,术后的疼痛向这个瘦小的身躯涌来,陈小凤始终一声不吭。
手术结束了,钱还是得交,甚至比预想的还要多:孩子出生后的情况并不理想,新生儿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一个小孩的费用要5至10万。
两个孩子,需要将近20万。
一张张催款单堆在陈小凤的床头,每一张都在冲着他们喊:钱!钱!钱!
但陈小凤没有医保,郑清明一个庄稼汉,家里穷得叮当响,能上哪里筹钱。

陈小凤丈夫 郑清明
听到消息,郑清明的大哥也带着一万块救命钱,急匆匆从农村老家赶了过来。但在巨额的医疗费面前,这一万块也只是投进了汪洋,打了个水漂,就消耗殆尽。
绝望之下,同一个病房的产妇家属支招,可以用房子抵押贷款。
兄弟俩看到了出路,立刻决定分头行动:一人在这里守着陈小凤,一人回家取房产证办贷款。
但因为相关政策规定,银行贷款的路子没有走通,兄弟二人只能去求助身边人。
此后,郑大哥回到了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借钱——
两千块钱,一千块钱,几百块钱……五万块钱找了几十个人借。
皱巴巴的一把钱攥在郑大哥手里,从百元到十元,面额不等,却同样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