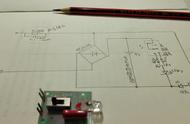娘的冬月

十一月十四,就是娘去世四周年的祭日了。按我们魏家湾的风俗,过了三年今年就不做周年了,然后整五整十的年份在做周年。三年内过年不能贴春联,三十半夜里,要去上新坟,初一早晨不能早开门,要避丧。
第一年,头七,三七,五七,尽七,百日。第二,第三年的大年初二,和祭日,亲戚都要来上坟烧纸的。我家亲戚少,最多坐五席,我姥娘家一席,姑姑和姐姐家一席,孩子的姥娘家一席,老亲戚一席,加上院里几个叔叔弟兄,都往圈外打算,省的挤挤巴巴坐不下。
想起来这个风俗很好,古人都是守孝三年,在坟塚旁边搭棚而居。西北有的地方是父母去世,孝子三年不剃头须。三年不长不短,一个缓冲期,在时光流逝的某一刻叫你想起,又是一种慢慢的放下过程。眼泪逐渐的风干,哭嚎声随着纸灰的余温褪去,所有的记忆和思念都藏在了心里,不经常提起,却从未忘记!
记忆里时令进了十一月,娘就会留心听天气预报,在北风来临之前,要做一件大事,打袼褙。
早晨鸡叫头遍,母亲就起来了,去厨屋里掀锅添水生火,拉着风箱熬一锅稠稠的玉米粥。然后把早早找出来的,穿不着了的旧衣服,布头,被里被面都放在凑手的地方。把吃饭用的矮桌子,擀面条用的案板,都预备好了。去锅里用瓷盆盛来热乎乎的玉米粥。母亲挽起袖子,用手蘸下粥先在桌面上抹些许的粥,然后贴上一层旧报纸,在均匀的抹一层玉米粥,就开始把大小合适的布头贴上去,大大小小,方圆各异的贴一层抹一层玉米粥。一定要涂抹多次,叫玉米粥浸润到每一丝布的经纬里,每一层之间都紧密的粘连在一起。反复的拍打涂抹,筹划每一块布都能用的上,等打完一板桌面,抓紧在打案板,力争在玉米粥热乎的时候弄完,只有在玉米粥热乎的时候,粘性才够劲,打出来的袼褙既平整又挺妥。我在被窝里看着母亲忙碌问了一句“娘要是一块布上没抹上粥,会怎么样”。母亲笑着说“会起泡,纳出鞋底来不结实”。等母亲都弄完了,天还没亮,我也又困了,迷迷糊糊中听着母亲,出来进去的收拾刷锅。把桌子案板都摆在墙根阳光最好处,袼褙上会有几只顽强扛冻的苍蝇,飞一下马上落下,等袼褙干了,苍蝇也不知那里去了。
一家人做几双棉鞋早就计划好了,在供销社买来了,白斜纹布包边用,买来黑条绒布做鞋面。纳鞋底的针是最大号的,纳鞋底的线绳子,是早早就割好的,很结实。有一年实行放风筝,我也用报纸,高粱杆糊了一个,就是用纳鞋底的线绳子,把风筝放起来的。过后母亲还是把线绳子都收了起来,我还不晓得割这一把线绳子,有多麻烦。
晚上,我在灯下摆弄作业,母亲就开始做鞋了。按着誊好的鞋样子,把袼褙铰成鞋底鞋帮。鞋底要好几层袼褙,用滚烫的水沏到面粉中,打一碗浆糊,把每一层袼褙的边,都用白斜纹布涂上浆糊把边包了,这样做成棉鞋,就是白色的千层底了。纳鞋底是最费工夫的,母亲带上顶针,把几层袼褙底子,细细的纳在一起,每一个针脚错落有致的排列,等穿上新鞋踏过,身后的鞋印上的针脚,就成了点点的纹饰。
冬天的村庄,寒月高悬万籁俱寂,每天晚上也不出去疯跑了,就在灯下围着母亲。开始点煤油罩子灯,也点过嘎斯灯,后来就有了电灯,电不经常有,电走了就点蜡烛。灯光里,母亲或纳鞋底,或做鞋帮。一双鞋做好要好几天,为了确保过年的时候,大人孩子都穿上新鞋,母亲白天去村小学,没有功夫,都是晚上熬夜。
纳鞋底,线绳子穿过鞋底有嗤嗤的声音,做鞋帮,絮好棉花,做鞋口上的穿鞋带的口眼,要用小锤子哒哒的砸。有时候伴着这声音,也侧耳听窗外的风声,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我八九岁的时候,个子和哥哥差不多高了。母亲疏忽了我的成长,还把我的鞋样誊的比哥哥小一号,做好了试的时侯,是光着脚丫试的,刚刚好。过年初一早晨,早起穿好新衣服,穿鞋的时候,很是费劲。母亲过来帮我提鞋,我有点急眼了“穿不下,穿不下还提,不穿了”。母亲只咂嘴“怪我把鞋样子誊小了,这怎么办呢。哎!”
我看母亲着急了,“要不穿旧的吧,”我说着甩掉新鞋,穿上旧鞋。簇新的新衣服,映衬下穿着旧鞋特别乍眼,很难看。
“不行,太难看了”母亲拿起新棉鞋,把手伸进去,“要是帮子稍微松点就好了,我怕你不跟脚,哎真是的”。“要不在试试吧”!
我看母亲着急的样子,心疼了。把脚指蜷起来,把袜子提紧用力一蹬,竟然穿上了,跳了跳跺跺脚,就是有点夹的脚疼。母亲用手摁了摁“到头到堵,今年穿明年肯定不行了”,母亲直起腰,长舒了一口气。
从那以后,我很少惹母亲着急生气。作为一个儿子,不能给你荣耀和体面,我只能用听话来尽点孝道了,只是这个最简单的,也做不到了,“子欲孝而亲不待”,是最叫人悲伤的事。
又是一个冬月,我在异乡,这几天晚上老是梦见母亲。戴着眼镜坐在门口的阳光里,小狗窝在一边。又梦到母亲在一条河的旁边,走一天路,后边是一片桃树林,母亲转过一个路口就不见了,我赶紧跑着去追,腿沉的几乎迈不动。想喊也喊不出声,急的我一身汗,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一声“娘”,梦醒了。
冬月夜静灯火昏,
大雪时节乡音闻,
伤魂最是家千里,
泪看高堂少一人。
愿母亲在另一个世界,平安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