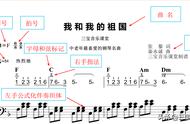该说粉浆了。做浆面条最重要的就是打粉浆。粉浆也叫浆汁,粉浆不宜太酸,酸则倒牙;亦不能太淡,淡则无味。
在老家一带,酿制粉浆多选用豌豆,也有用绿豆和黑豆的。豌豆在簸箕里被母亲一粒粒挑拣出来,残缺、有虫口的,统统弃之不用。
做芝麻叶浆面条的前几天,母亲就把挑选出的豌豆泡在了清水中,等浸泡了一夜,绿豆充分膨胀后,将其放入小花磨里磨成粗浆。


母亲找来一大块蒸馍时垫在笼箅上的细布,把粗浆一股脑全部倒进布兜里,用葫芦瓢从缸里一瓢瓢舀水冲洗,滤下来的浆水都流进了瓦盆里。
经过反复几遍冲洗,眼看着布兜里滤下来的水变清了,这才展开布兜将浆渣倒进锅里。一大盆浆水静静地置放在案板上,在时间的沉淀中最终明晰成了上下三层。
最上面的一层清澈如水,没有任何用途,被母亲一瓢瓢舀出倒掉。中间一层为二浆,是浆水中的精华所在,也是做浆面条的主要原料。
母亲将有用的浆水舀入瓦罐里,加入俗称“渣头”的酵母后,用塑料布将瓦罐密封,耐心等上一两天后再打开,罐中的浆水经过发酵已经变成上等粉浆,看上去色泽白中泛青,闻起来浆味酸中带香,如一坛醇厚绵长的老酒,沁人心脾。
母亲的浆面条最简单纯粹
却最令我难忘
开始做浆面条了,母亲用勺子从瓦罐里舀出浆水倒进铁锅里,再加两瓢清水,开始烧锅。
盖上锅盖,母亲转身就去和面糊了。浆面条只有稠了才好喝,面条不够,只有用面糊来凑。等锅里的浆水快滚未滚之时,上面会泛起一层细细的白沫,此时需要用筷子在香油瓶蘸些香油滴入锅中,再用勺子轻轻搅拌,浆沫就会消失,浆水变得细腻光滑。

等锅中浆水再次滚开,先将芝麻叶撕开丢入锅里,等上一会儿,再把锅排上的面条抖擞开放进去,用勺子搅匀。大火煮一些时,母亲抄起一双筷子,在锅里拨愣几下,最后撒上葱花和盐,浆面条就可以出锅了。
此时饥肠辘辘的我,端着碗靠在灶房门口,眼巴巴地望着灶间氤氲的热气,面条的醇香再加上芝麻叶的浓香冲击着我的鼻孔,生生能把人的馋虫给勾了去。
母亲笑吟吟地给我盛了一大碗,我也顾不上烧嘴,连喝带吃,连面带菜,风卷残云就下了肚,一直喝了几大碗,吃到肚子圆才肯罢休。
一大锅浆面条有时候一顿吃不完,等下一顿时母亲就把剩饭烫一烫,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乡谚说:“浆面条热三遍,给肉都不换”,足以说明“剩浆面条”的独特魅力。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母亲做的浆面条是最简单也是最纯粹的吃法。
那些家境殷实的人家吃浆面条则比较讲究,不仅要滴上一些小磨油或者辣椒油,还要挖上一勺提前调配好的水煮黄豆掺芹菜丁,面条白,芝麻叶黑,芹菜绿,黄豆黄,辣椒红,如此搭配可谓是色香味俱佳。
制作浆面条的佐餐小菜并不复杂,挑选一些籽粒饱满的黄豆泡上一夜,加入花椒、八角、盐煮熟;芹菜去叶、根洗净,用开水焯透后切成小粒;将花生放入油锅中炸透,用擀面杖擀碎。将黄豆和芹菜丁拌在一起盛入碗内,便搭配盛成了一道爽口的佐餐小菜。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梁永刚,男,1977年生,河南平顶山人,散文作品《风吹过村庄》2016年4月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现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