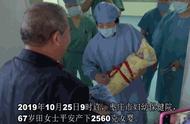《轮到你了》截图(以下截图可能涉及剧透)
1.
用“恶”来解释的问题都掩盖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有一个标准的解释,认为纳粹大屠*(令人悲哀的是,纵观历史,放眼全球,这样的屠*还曾在许多文化中上演)昭示了人能够对同类施加的“恶”(evil)。
这种“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蕴含的恐怖如此巨大,没有语言能够传达。这个标准的观点有许多人主张,“恶”这个概念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可怕的行为:
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
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身为科学家,我想理解是什么让有些人把同类当成物品来对待。人为什么会残酷地对待他人?我运用的概念不是“恶”,我运用的概念是共情。
和“恶”的概念不同,共情是具有解释效力的。解释人何以能对彼此造成极端伤害,同时又不仰仗那个过于简单的“恶”的概念。让我们把“恶”替换成“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
共情腐蚀的一个原因是人产生了激烈的情绪,比如强烈的愤恨(resentment)、复仇的*、盲目的仇恨,或是保护的冲动。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情绪,由它们引起的共情腐蚀也是可逆的。然而还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引起共情腐蚀。

《轮到你了》截图
共情腐蚀产生于人把其他人当作了物品,这个洞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布伯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当1933年希特勒掌权,他也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席位。
布伯写过一本名著,题为《我与你》。他在书中对比了两种存在模式,一种是“我—你”模式(你和另一个人产生联系,为的就是这联系本身),另一种是“我—它”模式(你和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产生联系,为的是利用对方达到某个目的)。他主张用这后一种模式来对待别人是对人的贬低。
一旦共情关闭,我们就完全处于“我”的模式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和物品产生联系,即使和人产生联系也只把对方当作物品。其实大多数人偶尔都会这么做。我们也许专注自己的工作,完全忘了办公室外面还有个无家可归的人。
无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身在其中时都见不到“你”——至少见不到一个有着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你。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追求自身的关切,他很可能就会丧失共情。这时,他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
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形态,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好几年的怨恨和伤害(这常常是冲突造成的),又或者是因为比较持久的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
(有趣的是,在这个一心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人或许反而会做出一些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之类。但就算他的行为是正面的、有价值的、宝贵的,只要他当时专心致志不想其他,就仍然可以定义为丧失了共情。)


《轮到你了》截图
2.
恶之平庸下的“个体责任”与“自由意志”
把“恶”字替换成“共情腐蚀”,真的能把恶解释清楚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什么别的解释?我们已经抛弃了宗教里“恶”的概念,因为我们认定了它不是真正的科学解释,那么余下的解释中最有名的就数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用“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所做的分析了。
阿伦特曾在耶路撒冷列席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审,艾希曼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osung fer Judenfrage)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庭审中,阿伦特发现这个男人不是疯子,也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就是个相当普通的人。为此,她才提出了“恶之平庸”这个说法。
恶之平庸的概念还指出了一些普通的因素,但是它们相加就会导致恶行。这个概念源于所罗门·阿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在研究中揭示了“从众”的效应:被试会因为别人都说某条线段较长就也这么说,虽然他们眼前的证据刚好相反。
沿着这个传统,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又展示了为了“服从权威”普通人愿意对他人施加电击,即使电流强到足以*人。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属于这个传统,参加实验的学生在一座模拟的监狱中随机分配到看守或囚犯的角色,那些扮演看守的学生很快表现出了残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