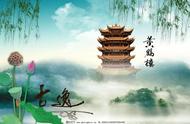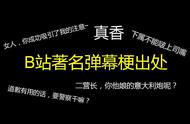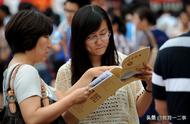图1 《美术杂志》最后一期为“辟卡梭特辑 Pablo Picasso”,1937年7月
有意思的是,梁锡鸿一度的亲密盟友、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创会成员李东平,1936年抛出一个新概念——“新中国主义”,他为读者列出了四条标准:1.打破传统的观念;2.否定一切过去陈腐的技巧;3.应站在现实的中国社会去做基础;4.要民族精神的表现。
对此,李东平的解释是:“我们所谓新中国主义是不分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因为艺术精神总是共通的缘故,可不分技巧、表现,我们可通称为绘画。只要我们的一切表现是我们民族现实姿态的时候,适合我们的社会生活时,都是‘新中国主义的绘画’。总而言之,我们若要实现我们的 ‘新中国主义’的时候,则最低的限度应该接纳以上四项的要求,然而问题的结果,最后还是要依我们的手才能做成!新中国主义绘画的产生是过去艺术的送葬曲。”
这个概念难以自洽,既要反对传统,又要弘扬民族精神,既要现实中国的特殊性,同时又要坚持现代绘画的文化普遍性。这正如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名称一样,其本意是希望和巴黎、东京的独立美术协会保持价值观的一致,但却不得不加上“中华”的前缀。对于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而言,国家认同与现代艺术的价值认同势必要采取一种妥协的形式,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时代悖论。但我们仍能领会李东平的真实用意,他的“新中国主义绘画”的实质,依然是想强调“依我们的手才能做成”的文化精英的立场,他们并不打算向庸俗而流于功能化的宣传艺术妥协。(图2)

图2 李东平,《某家的破落》,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出品,《广东美术》,1937年
1939年初,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岭英中学新落成的两幅壁画:梁锡鸿、何铁华合作的《建国》以及倪贻德的《抗战》,是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和决澜社解散之后,这两个现代美术社团的成员合作的一组“公共艺术” 作品,如果我们放宽“集体创作”的定义的话,香港这组壁画的创作,未尝不是这群“在野”的现代艺术家针对官方体制的“美术工场”组织形态的一次发声,反映了时风转移的强烈信号。(图3)

图3 叶灵凤、何铁华、倪贻德、梁锡鸿合影,香港九龙,1938年12月28日
对于刚刚从武昌黄鹤楼大壁画现场出局的倪贻德而言,在香港创作《抗战》壁画不仅是一时的谋生之举,也是他试图重新阐释和推广“新写实主义”理念的一次努力,然而最终的画面效果并没有让他感到满意。而梁锡鸿、何铁华合作的《建国》,则表现出强烈的风格创新意识,无意间也对应了李东平“新中国主义”的折中方案。
《建国》壁画中仿效莱热画风的中山装男青年形象,以巨人尺度屹立于城市的废墟中。根据何铁华的解释,这个巨人象征着“建国的智慧精灵:他有深思的设计,稳重的态度,强*魄力,坚贞的德行,及抗战必胜建国必胜的信念”。如果不仔细辨认的话,我们很难从满布画面的拼贴元素中总结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抗战的宣传艺术作品。何铁华在总结这幅壁画的创作经验时,殷切地告诉读者:“绘画的最重要性,是在如何表现,而绝不在表现什么。”
《建国》壁画与其说是为遵循抗战建国的政治目标而作,其实也不妨看作这场突发的战争,给这两位现代艺术家提供了创意灵感和创作“大画”的机遇。近期的研究表明,这幅壁画多处“引用”了日本、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画家的画风和造型元素。与他们亲近的评论家也声称,这幅画所采用的是“贴糊绘(collage)”手法,受到了欧洲现代画家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恩斯特(Max Ernst)的影响。而倪氏创作的《抗战》壁画中那位中国军官骑乘的战马,直接参照了《现代世界名画集》封套上超现实主义画家基里科的作品。
两幅抗战壁画的创作和传播过程,都反映了这批现代艺术家在抗战初期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参与抗战宣传,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他们仍想维护作为现代艺术家的价值观和创作方法。在此之前,梁锡鸿、何铁华并无此类拼贴风格的大画创作,此后也没有出现过,在抗战初期涌现的众多抗战美术宣传品中,这幅壁画在画风上的标新立异和晦涩的内容表现,一定是让当时的观众颇感错愕的。
虽然迄今为止这两幅壁画尚未获得学界的充分关注,本文还是将之理解为民国时期洋画运动的一个断裂点,它预见了此后现代洋画的一般命运,这类强调个性表现的画风往往被视为画家道德堕落和政治落后的行为。如果说,在此之前洋画家种种标榜自我的激烈行为和言论,还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扬弃旧道德、旧思想的时代急先锋,这也是中国的洋画家们通常将自己视为“先锋”的重要理由之一,而此后,这类不识时务者将不断遭遇道德指责甚而政治惩戒,他们也没有机会遇到像香港岭英中学校长、留美博士洪高煌这样趣味独特的赞助者。
与何铁华振振有词的说明正好相反,此后绘画的重要性,恰恰不是体现于艺术家自由表达的形式问题,而是表现为内容的政治正确性,而这种政治正确性也很难准确把握,因为它越来越关系到特定党派一时一地的政治主张和表达方式。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这几乎是一场关乎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豪赌,唯一没有悬念的输家,是这批主张形式重于内容的前卫艺术家。
二
1939年初,梁锡鸿和何铁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那正是他们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但他们的导师倪贻德已经有所领会,1938年8月间,因为躲避日军轰炸而缺勤,时任三厅美术科代理科长的倪贻德,在武汉被他昔日的文学领路人、此时的行政长官、三厅厅长郭沫若勒令去职。真实的原因还有待推敲,很可能他在大壁画创作中的自作主张触怒了领导。倪贻德不得不放弃正在筹备中的黄鹤楼大壁画的创作,黯然前往香港,与梁锡鸿等人汇合。倪的离职并非一般性的违纪事件,郭厅长极有可能小题大做,借此案例警示三厅的艺术家们,文艺界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改变,作为一名献身抗战的国家的艺术家,必须无条件地放弃以往散漫享乐的生活方式,恪守军令,一心奉公,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
倪贻德去职之后,三厅迅速组建了被称为“美术工场”的画家组织。这实际上是对倪贻德主持的美术科的改组,艺术家们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宣传画的批量生产,工作之余参加政治学习,在日军即将攻陷武汉之际,这个创作集体迅速完成了黄鹤楼大壁画的制作。
在黄鹤楼大壁画的创作过程中,一种崭新的军事化集体创作模式开始酝酿成熟:国家对艺术家的管理、聘用实现了普遍化和制度化。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和美术工场的建立,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全国性艺术家组织的建立,同时浮出水面。这是现代中国首次实现威权政治与艺术宣传的全面合作。这一模式,并非战时中国的发明,它的母版主要借鉴自苏联,而在战前已经成功实践这一模式的国家尚有德国、意大利以及中国的敌战国日本,中国只是一个在战争中匆匆加入的后来者。
我们注定要用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态去回望1938年的武汉。中国在缺乏盟国支援的情况下,凭借悬殊的兵力与不宣而战的日本展开了殊死较量,武汉保卫战是中国在进入持久战之前的最后一场重大战役,生死决战,其意义对交战双方自不待言。与战场上的全面失利、节节败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实现了政治动员的奇迹。在孤绝无望中,国共两个党派实现了政治和解,建立起跨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自左翼、右翼和中间阵营的知识分子流亡至武汉,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宣传抗战的工作中。
1938年初组建的政治部就代表了国民政府强化政治动员的迫切愿望。而承担该项核心任务的政治部第三厅,一时间吸纳了包括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冯乃超等亲共的留日知识分子。以蒋介石、陈诚、陈立夫、董显光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官僚,在1938年持有足够强烈的意愿来达成全民总动员的目标,政治审查制度也相应放宽,国家机器与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得以顺利合体,这集中体现为第三厅出色高效的宣传动员工作。
在恐惧和悲愤的情绪中凝成统一抗敌意志的中国军民,迅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同情与声援,武汉也一度被称为“东方马德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线中的一个亮点。应该说,这样一种国际关注度和参与度是战前艺术家所未曾体验过的,艺术家的创作既是爱国救亡的政治宣传工具,又是体现全人类追求和平、反法西斯暴政的国际阵线的一环。可以说,短短数月内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关注度也提高了,因为陈依范等人的积极奔走,中国的抗战宣传艺术作品甚至还被送往欧美、苏联等地进行国际巡展,这是20世纪30年代寄梦于巴黎派和独立沙龙的中国艺术家们所不敢想象的。
就艺术语言而言,具备高度实验性和完成度的宣传艺术品大量涌现,这尤其体现为漫画家们的成熟表现。他们与政府和军队配合默契,善于将流行的插画风格整合到与抗战相关的一切时事题材中,漫画家们组织、行动和变通的综合能力在美术界也赢得了至尊地位。1938年,拥有“漫画家” 的身份成为艺术界一时之风尚,而其中的佼佼者也包括了此前主要从事洋画和版画的艺术家,如李可染、梁白波、赖少其等人。
在漫画成为主导性风格的风潮中,我们看到战前长期掌握画坛话语优势的洋画家遭遇了被边缘化的尴尬局面,除了接受这一风尚的影响之外,我们也能体会到他们暗自较量的心态,而参与壁画创作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洋画家们在战时的有效策略。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显然对洋画运动构成了整体的压力。20世纪30年代,艺术界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壁画的讨论,但抗战之前壁画在中国并未获得充分发展。决澜社的洋画家们意识到了洋画运动面临的危机,在这场由新兴媒体摄影、漫画、木刻所带动的文艺大众化浪潮中,他们实际上处于被动状态。作为一种转型方案,一些洋画家开始对壁画等公共艺术形态发生兴趣,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以及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的壁画频繁出现在艺术杂志的报道中,如倪贻德从1933年到1937年间持续在媒体上介绍从墨西哥到苏联的壁画创作。
与墨西哥、美国和日本相比,国民政府当时资助的壁画项目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国政治的脆弱生态,政府从未获得相对持久的和平环境,出台条件优渥的艺术赞助政策来推动公共艺术的创作,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壁画运动那样。而获得国民政府赞助的梁鼎铭主持创作的战画室壁画,以及张云乔在上海一·二八阵亡将士纪念馆绘制的壁画等,这些壁画项目或者囿于国民党的内部教化功能,或者受限于作者的表现力,很难说具备动员大众的成熟功能。
战前最值得关注的一次街头艺术实践,或许是洋画家司徒乔1936年10月在鲁迅葬礼现场的突发性行为,他为游行队伍临时创作了一张巨幅鲁迅肖像。在遍及全国的对鲁迅葬仪的摄影报道中,伟人的巨幅肖像为文化界的精英们所簇拥,在送葬人群中处于视觉中心,恰如其分地提升了现场的仪式感。这一图像也回应了民间压抑已久的复杂情绪,民众普遍要求政府采取主动姿态反抗日本侵扰,文艺界的派系纷争也汇合在了这一历史现场。现代艺术家以公共艺术作品的形态主动介入激情澎湃的街头政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而围绕鲁迅肖像的送葬队伍的人群中,有不少人在一年之后逃难到了武汉,成为三厅抗战宣传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从视觉呈现的效果而言,1938年武汉的黄鹤楼大壁画超越了这些战前的案例,反映出明确的壁画实践方法和意图。在理解和阐释这种视觉风格的渊源时,我们除联想到田汉作为总设计师,可能对瑞士象征主义画家贺德勒的壁画《一致》有所借鉴之外,也很难排除受到了墨西哥壁画家里维拉的影响。
这一议题也关联到抗战初期宣传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风格的突变性。如前述梁锡鸿主笔的《建国》壁画借鉴了日本画家的超现实主义画风,还有才华横溢的女画家梁白波对墨西哥插画家珂佛罗皮斯画风的成功借鉴,都是战时风格突变的案例。而黄鹤楼大壁画的创作始终在敌机轰炸的侵扰下推进,危机情境下的集体协作,可能也提升了艺术家表达构思的活跃和开放程度。
从制度层面考察,黄鹤楼大壁画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从任务下达,到组建构图小组、提交领导审议,确认终稿后分配任务,最后上墙绘制,以这种层级明确的行政管理方式创作一幅国家主题的壁画,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可谓首创之举。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幅壁画的倡议者和监制,更准确的称谓是“导演”——政治部三厅主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田汉,由这位剧作家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来构思一幅抗战主题壁画,无疑是一个殊堪玩味的现象。
本文以倪贻德作为一个贯通全局的关键人物,正是为了深入探讨这幅大壁画所隐喻的国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冲突性。在这层意义上,倪贻德是踌躇于国家主义与个体价值之间的一个悲剧性角色。他和庞薰琹等人于1932年组建的决澜社,以及梁锡鸿等人在东京组建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是在中国艺坛推广现代艺术理念的急先锋,重视艺术自律的价值观横亘了倪氏的一生,甚至延续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但是作为一名秉持历史进步观的创造社作家和美术批评家,他又时刻笼罩在时代话语的潮涌与激荡之中,在艺术理论的表述上也表现出矛盾色彩。抗战前后他在洋画创作中所提倡的“新写实主义”,这也是他用来形容黄鹤楼大壁画的风格转向的理论话语,就反映了他这一充满矛盾的思想处境,而在对这一理论话语进行历史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条现代艺术观念的跨语境传播路径,其中交织着从法国、苏联、日本影响至中国的复线结构,呈现为左翼文艺路线和纯粹艺术观之间激烈竞争的历史进程。
作为由倪贻德、王式廓等留日艺术家主持创作的一幅宣传画,黄鹤楼大壁画的创作现场也反映了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与这批留日艺术家同期登台的,是作为敌方的日本画家组成的战争记录画的创作团队,这批隶属于日本海军、陆军的知名画家,其中如藤岛武二、藤田嗣治、石井柏亭、中村研一等人,在战前或是这批中国艺术家留日时期的导师,或是对他们的现代艺术创作给予过深刻影响与启发的重要艺术家。这种师生交谊在1938年迅速蒸发,中日现代美术的官方交流也就此截断。而中日艺术家在宣传美术的创作理念和手法上显现出的异同点,是本文的关注点之一,笔者试图在东亚现代美术史的全景视野中考察这段颇不寻常的美术师生之间展开的宣传战。
在这个利用新媒体进行战争宣传的环节中,中国的戏剧家田汉、电影人钱筱璋、漫画家叶浅予与日本出版人名取洋之助、日本战地摄影师小柳次一对黄鹤楼大壁画的图像寓意进行了各自不同的阐释,使得这幅壁画在其物理性存在之外,还凭借着现代化的图像传播手段,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景观。日方将这幅壁画作为占领图像进行广泛传播,以现实武力(占领武汉的日军)遭遇虚拟武力(画面中蒋介石所率领的迎击日军的中国军队)构成画面的戏剧性内容,从而突出了日军对武汉进行的军事占领,以及对华作战即将赢得全面胜利的夸耀心态。而中方的宣传物如叶浅予主编的《今日中国》画刊,则将壁画编排在抗战美术的丰富生态中加以介绍,在文艺界空前团结的大氛围下突显出这幅壁画作为中国军民表达抗战信念和实现全民动员的视觉象征。
黄鹤楼大壁画中以蒋介石作为画面中心人物进行表述的方式,也引发了笔者对抗战初期大量涌现的领袖像的关注。抗战初期蒋氏肖像的大量出现,与其说反映了政府自上而下的成功动员,不如说更反映了怀抱不同政治信念和艺术价值观的艺术家,此时被激发出的强烈的国家认同,以及对战胜恶敌、赢得正义与和平秩序的普遍期待,而艺术家在创作现场所经历的崇高体验,凝聚于创作中,作为政府首脑和军事统帅的蒋介石的形象,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家认同的象征物。因此,在这一情境中大量生产的领袖像,既可作为国家主义的视觉表征,又是艺术家源自内心、主动择取的爱国心的由衷表达,不能否认其中包含了个性化的创意和情感内涵。不对这段历史进行细读,我们可能就无法在李可染创作的巨幅蒋介石肖像和他1949年后的红色山水之间辨识出内在的血亲关系。
国家认同既造成了如此强大的磁场,在1938年让众多不同派系、不同政见的艺术家齐集武汉,挥师向敌,抗战卫国的正义立场已不存疑义,但如何在党派斗争暗流涌动的复杂境遇中选择“进步”的立场,就见仁见智了。换言之,思考现代中国的前途,这是抗战初期艺术家主体性中更为深层和不确定的因素。黄鹤楼大壁画创作过程中艺术家的区域性分流,就直接见证了抗战时期艺术家的三个主要阵营的形成过程:王式廓在完成了壁画小稿后,即通过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奔赴延安,成为解放区美术创作的骨干力量;倪贻德在壁画尚未开工之时因违反军纪遭郭沫若开除,此后转道香港回到上海,成为“孤岛”艺术家中的一员;而李可染、周多、丁正献等人则随三厅前往重庆等西南城市,国统区艺术家的阵营也由此成型。
既然艺术服务抗战已经是普遍的信条,那么在不妨碍大原则的前提下,各政治阵营对于艺术家的吸纳与招募就成为武汉撤退前后的必然趋势。而倪贻德此时退守“孤岛”,则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一个中间地带。如何在保持个体的生存权利和自由创作的前提下,将国家民族意识和现代艺术的形式语言融入创作中,是这位现代艺术家在“孤岛”时期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而他在上海开办的尼特画室,以及与丁衍庸、关紫兰、赵无极等人举办的数次联合画展,则反映出他并不甘心于现代艺术式微的现状,而试图团结同人的一种努力方向。
三
“孤岛”时期的上海也酝酿出一些新动向。倪贻德最重要的一位现代主义盟友,一向沉默寡言的关良,于1939年9月创刊的《美术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三位一体主义》的文章。对于抗战时期“美术家往哪儿去”这个问题,关良的回答有三点:领导时代,发展团结力,充实自己。对于第二点,关良似乎是从好友倪贻德参与的黄鹤楼大壁画创作那里获得了启示,他提出“今后的艺园里,应该努力提倡集体的创作,各尽所能地去耕耘”。关于如何“充实自己”,他的解释是:“坚定个人的意志,清洁个人的人格,提高个人的艺术水准,要作到如此的功夫,以为我们美术界同人的基础。”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关良向倪贻德赠送了两幅水墨画。以昆曲《义侠记》和京剧《游龙戏凤》为主题的这两幅小品(图4、图5),很可能是画家关良向友人最早公开的一批戏剧水墨画。次年初,他在香港举办了首次展览,展示了他的水墨画新作。这一新动向是否对应了关良所谓的“充实自己”,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经历抗战洗礼的现代艺术家群体中,“国画家”关良20世纪40年代在陪都重庆的声名鹊起,是个罕见的成功案例。作为洋画运动的中坚分子,他认同倪贻德提倡的“新写实主义”,强调形神合一的单纯化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他比决澜社中早夭的张弦走得更远,致力于现代艺术的本土化实践。和丁衍庸、谭华牧等20世纪20年代早期留日的洋画家一样,他们很早就认识到“东洋回归”是在亚洲实践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启示。在此后的京剧题材水墨画创作中,他将野兽派的形式实验与中国文人绘画的笔墨经验、造型趣味熔于一炉,更以发扬国粹的门面为命悬一线的现代主义开辟了一条生路。

图4 关良,《义侠记》,水墨设色,1939年,私人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