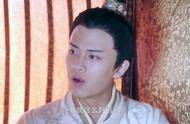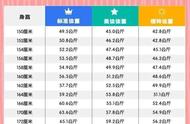2023年田林县壮剧艺术节开幕式演出。张友豪 摄
一
我时常想,北路壮剧在田林人心中有多重要?
这个成形于清乾隆年间的戏剧形式,有着独特的唱腔和表演程式,是操北路壮话方言的地方戏曲。它的音乐风格古朴、余韵悠远,说唱中包含大量壮语独有的方言俚语,朗朗上口、寓意丰富。
北路壮剧上演的剧目大多来自壮族群众的生活实践,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至今长盛不衰。如《壮家有戏》中的唱段“台上帝王将相,台下左邻右舍……”就源于真实生活,透出一种天真自然的野性之美。
今年5月8日,田林县壮剧艺术节盛宴再启,憋了足足3年的群众欢呼雀跃,从四面八方赶到田林县城,与桂滇黔三省(区)的众多壮剧团齐聚一堂,汇成欢歌笑语的海洋。
初夏的气候不停地变着脸。一开始还算清凉,一场戏演到中途气温陡然飙升,灼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广场上挤得满满的人们,有的打起了伞,有的戴上了帽子,但更多的是任由阳光暴晒,满身大汗入迷看戏的人。突然间,大雨倾盆,有伞的人举高雨伞接纳陌生人躲雨,没伞的用手搭棚或是寻找物件挡雨,还有人干脆将塑料凳子套头上,继续在大雨中专心致志看戏。戏台上,演员们看着现场氛围有增无减,演起戏来更加激情万丈。
听戏的人里有老人、青年、孩童,有壮族、汉族、瑶族、苗族等各族群众,还有来自区内外的媒体记者与游客。“虽然台上的戏文和身旁群众的交谈都听不太懂,但是看大家这么投入,笑得开心,让我也忍不住跟着高兴起来。”一位记者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田林作为广西土地面积第一大县,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同饮水,共耕地,齐欢庆,通过打老同、契兄妹、拜干亲等多种方式,融入彼此生活,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铺展开一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美长卷。
如今的田林县,共有120个业余壮剧团,演员约4000人,基本实现一村一戏台一剧团。在村中的壮剧团里,夫妻同台、父子同演、姐妹上场的情况十分普遍。时常能见到一起排练壮剧的夫妻,回到家里还用戏里台词对话,家人问话也用一句“听啊——”的壮剧唱腔回答,痴迷到近乎“走火入魔”。
二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田林县旧州镇那度村的杨六练组建了“龙城班”,在旧州搭建木台演戏,用北路壮话方言演出戏剧。100多年后,杨六练的后代杨连、杨散兄弟又将北路壮剧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带领那度村剧团走村串寨,在广西的隆林、西林、凌云等地以及贵州的册亨、兴义、安龙和云南的富宁等地巡回演出,每村唱个三天三夜,直听得村民意犹未尽又挽留再演。当时,壮剧的剧目少,杨连又将小说改编成戏,经他改编的有《二度梅》《仁宗不认母》《五子拜寿》《包公奇案》等,一经演出,悲的能使观众流泪,喜的笑到合不拢嘴,深受群众欢迎。
相传,那度村剧团每次演出路上都靠一匹大黄马驮道具、服装、乐器等。有一次,因为接连赶路,大黄马劳累过度,突发疾病而亡。剧团的人伤心不已,杨家兄弟更是忘不了多年任劳任怨随着壮剧人“出征”的大黄马,便寻思着用马的腿骨制成两把二胡,让它陪伴剧团一直演出下去。
马骨做的二胡声音洪亮且深沉、悠扬,成为剧团独特的乐器。那之后,田林的每个剧团都制作马骨胡,作为北路壮剧指定乐器。至今,他们兄弟二人所制的马骨胡,仍存有一把收藏在那度村,激励着壮剧人不断前行。
2006年,以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壮族师公戏为代表的广西壮剧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与田林县共建中国壮剧传承研究基地;2014年,原文化部授予田林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壮剧)”称号。
随着北路壮剧会演影响力逐渐扩大,更多新颖及贴切反映现代农村生活的曲目,精彩生动地展现在群众面前,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创作了《驮娘江的故事》《扶贫轶事》《祭瑶娘》等壮剧剧目,并在《祭瑶娘》的基础上创作出大型壮剧《瑶娘》。2016年,由壮族和瑶族青年的恋爱故事表现民族团结主题的壮剧《瑶娘》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并完成了40场巡演,好评如潮。

田林群众冒雨看壮剧。黄卫平 摄
三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那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的感触,都会印在记忆的深处,像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作家吴伯箫的话,十分贴合我对壮剧的感受。
我的家乡在田林县潞城瑶族乡央郎村马郎屯,北路壮剧已经在这里传唱了上百年。我第一次看壮剧表演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乡里读初中,寒假回村的时候看到人们在台上咿呀唱念,既新奇又开心。尽管台上的演员演技并不出彩,戏服也格外陈旧,但喧天的锣鼓声、悠扬的马骨胡声,还有那亮开嗓子吟唱的声音,让寂静的小村瞬间热闹了起来。那个春节,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戏台上不分昼夜地上演着各式剧目,吸引了周边村屯诸多群众前来观看。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看戏相识相交,最后结为伉俪。
我也在看戏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她不是我们村的人,只是听闻这里有壮剧表演,就专程前来听戏。因为年纪相仿,我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不仅讨论台上的演出,也交流学习上的心得。这美丽的相遇,让我至今每每听到北路壮剧的曲调,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她当年的模样,还有村子里摆开戏台的场景。那是我的青春,也是我的乡愁。
我的母亲极爱壮剧,不肯错过县里任何一次壮剧艺术节的举办。而我因工作的关系,每年都无法陪同,但我总会在艺术节现场拍摄大量观剧群众的照片,并从中寻找母亲的身影。
有一年,我的二姐作为村剧团演员到县里参加壮剧艺术节的展演。因为演出的要求,二姐提前出发了。88岁的母亲以为二姐担心她的身体,悄悄走了不带她,于是自己跟着村里的车进了城。到了县城之后,晚会已经开始,母亲找不到方向迷了路,而我又有任务在现场走不开。等我终于忙完找到母亲时,她老人家早已又累又饿。我心疼地埋怨她,她却咯咯地笑着说:“我都这个年纪了,看一次算一次,可不能错过了。”
一语成谶。一个月后,母亲因为感冒引发器官衰竭,撒手故去。那次看演出就这样成为她人生的“最终场”。而我也只能在此后一场场的演出中,追忆那个远去的身影。
四
悠悠壮剧,生生不息。经多年的精心培植,北路壮剧已成为田林县的民族文化瑰宝和乡村振兴的“灵魂”。不仅在田林的“壮族祭瑶娘”“吼敢”“销正月”“休垌节”等民族节庆上大放异彩,更以北路壮剧带动瑶族铜鼓舞、抛绣包,以及壮、汉、苗、瑶等民族山歌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化枝繁叶茂,带动了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最开怀的时刻当属众人在壮剧艺术节期间同欢长桌宴了。从街头到街尾,长桌一溜排开,满满当当地摆上五色糯米饭、糍粑、腊肉等特色美食,色泽诱人,香飘四溢。天南地北而来的人们,围坐在一起,觥筹交错,相互祝福,好不热闹。
一路走来,北路壮剧从民间走向“官方”,从“荒野”走进专业,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不仅壮剧艺术节的档次在不断提升,田林县还划拨财政专项资金,在社区、农村广建戏台;出台政策,每年拿出10万元经费,鼓励编写规范剧本,并每年扶持每个业余剧团1万元。
在北路壮剧文化精气神的带动下,田林县域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50亿元、60亿元、90亿元台阶……2023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5%。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登台演戏,已成为不少田林农民的生活新常态。这些年,排练的环境好,演出的机会多,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北路壮剧;加之县内各中小学校汲取壮剧所弘扬的真善美营养,把壮剧融入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帮助北路壮剧活态传承不断档。
“宁可不吃肉,也要看壮剧。”老乡的一句话突然点醒了我,原来北路壮剧在田林人心中是粮食,是美酒,更是奔赴美好未来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