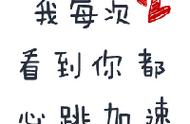2002年12月10日,一位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他就是至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非典病人,也是后来被学界命名为SARS的病毒的起点。自此,中国人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2003年6月20日,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从北京北郊一所名叫“小汤山”的非典医院里走出来。
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
本文刊载于《民生周刊》2013年第1-2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忘却的“非典后遗症”10年过去,对于脑海中不断回放的非典遭遇,55岁的她依然能够清楚地记住每一个片段。那些本应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如种牛痘般深植在她的脑海中……
5.12地震、甲型H1N1流感……除了主治医生,其他人无暇回顾非典,甚至不知道“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存在。
“一开始是膝盖疼,接着脚后跟,然后是两个肩膀。发作的话,就跟骨头里长刺一样,连床都不敢沾。”2013年1月2日,在北京市望京医院住院处关节三科的病房里,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杨志霞正在接受治疗。
与她同时住院的还有方渤、张文荣等“老友”,他们普遍患有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症等疾病。而给他们打下相同烙印的,是2003年那场世人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非典”(SARS)。
这个群体是10年前SRAS劫难的幸存者,也是10年后痛苦延续的承载者。在“后非典”时代,他们以“非典后遗症患者”的身份默默淡出人们的视野。
现在谈到非典,杨志霞语气中已流露出些许的抵触情绪,眼神不时飘向窗外的斜阳,声音踌躇而缓慢。
10年过去,对于脑海中不断回放的非典遭遇,55岁的她能够清楚地记住每一个片段。那些本应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如种牛痘般深植在她的脑海中……
“人活着,不就过个人气吗”
“4月21日、4月26日、5月1日、5月3日。你说多短,14天。大家都说该翻篇了,可不是你们家的事你翻不了篇。”提到父母、弟弟、丈夫相继离世的日子,窝在病床上的杨志霞往后靠了靠,牙齿不自觉地咬住了嘴唇。
在她的记忆中,2003年的春天是“白色”的,道路空了、商场空了、公交空了、酒楼空了,还有她原本热闹的一大家子——11口人,9人感染非典,4人因此丧命。
事情始于2003年4月12日。因照顾发烧的母亲、半身不遂的父亲,杨志霞兄妹三人,以及各自的爱人,轮流照顾老人去东直门医院看病、输液。
“当时,满世界都在说非典,可没见周围谁真的得了。”听着四起的传言,杨志霞惴惴不安,本能地不敢把“恐惧”说出口。
但随着父亲、丈夫、哥嫂、大侄子、弟弟、弟媳以及自己相继发热,还有医护人员悄然穿戴上的口罩、防护眼镜、隔离服,不安的情绪在这个家庭蔓延开来。那时,杨志霞的大哥小声说了句“这回咱家事大了,要完了”。
为了给母亲宽心,那年的4月17日上午,杨志霞拿着《北京晨报》读道:“北京目前只有30多例非典且全部为输入型,没有原发的。”
似有某种预感,在大哥的建议下,全家决定“去医院检查也要吃饱饭再去”。17日中午,杨志霞闷上米饭,大哥做了爆羊肉、炒芹菜和西红柿鸡蛋汤。“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家的最后一顿团园饭。”
被确诊后,在北京市胸科医院治疗的数十个日夜,杨志霞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和同屋的两名病友总是斜靠在床上,等待黎明,等待医生,等待输液……
“谁也不敢睡,困了就聊一句,聊到5点,就觉得又活过了一天。”
虽然除了已经病逝的母亲,大部分亲人都住在胸科医院,但离开吸氧机就无法呼吸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们相互探望、照顾。即使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也是楼道里有人喊了声“杨志霞,给你爱人火化了”。
后来她才知道在那场疫情中,中国有5327人被确定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死亡。他们兄妹曾带母亲看病的东直门医院,早在3月16日就接诊了一位曾去香港探亲的李姓老人。这位老人正是后来被公开的北京第二位非典确诊病例。
“人活着,不就过个人气吗?现在家不成家了。”
病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杨志霞将自己封闭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说话、拒绝交流,流泪成为唯一的宣泄方式。半夜,儿子被哭声吵醒,她只能淡淡地说:“没事,我想你爸了。”
“活多少年,就要受多少年的痛苦”
看着每顿吃着两毛钱的白菜、拿着奖学金奋力读书的儿子,杨志霞开始寻找活着的希望,发誓拿着低保也要把孩子供出来。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俗语,恰恰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2003年8月,非典消失后的第二个月,科技部设立了一个“863科研项目”,针对SARS展开后续研究。东直门医院、望京医院、北医三院等多家医疗机构成为科研工作承接单位,并开始寻找非典治愈者进行筛查。
就在这次免费检查中,2004年初,一直双腿酸疼的杨志霞被确诊为患有股骨头坏死。听到妹妹的消息,正在排队等待筛查的杨志霞大哥瘫坐在检查室门口……
“当时一拍片,大夫说你两腿全部坏死。”无法接受现实的杨志霞,一路从北医三院哭着回到家。
2004年3月,为了保住双腿,杨志霞再次住院,接受保守的“介入”治疗,即往大腿根的动脉血管里打药,促进骨头周围的毛细血管扩张,一定程度上缓解缺血性坏死的危险。
“治了40多天,发现治不起了。除了医保,自费要4800多块钱。”因为丧失劳动能力病休在家,原是燕莎友谊商城后勤部员工的杨志霞,每月只有900元左右的收入,其中还要确保儿子300元的生活费。“大哥也是一样的病,谁也帮不了谁。”
在治病过程中,她很快发现自己不是个体。病房内外,还有方渤、吴如欣、李朝东、李桂菊、王春秀等病友。
之后的两年,在陆陆续续的筛查中,共有150余名“非因公”非典后遗症患者在北京各个地区显现出来,其中包括杨志霞的大哥、嫂子、弟媳。
这个150余人的群体,有着相同的特征: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以及抑郁症。
“你活多少年,你就要受多少年的痛苦。治这儿了那儿坏了,治那儿这儿坏了,没完没了。”久病成医的方渤,如此解释为何医学界称股骨头坏死为“不死的癌症”。“身上就这么几个关节,都换了,这人不成机器人了吗?”
今年61岁的方渤,曾一度是媒体的宠儿。2003年,作为“被成功治愈的非典病患”,他曾上过央视“面对面”、“东方时空”等栏目。
当年,方渤家8人感染住院,出院时只有6人。翻看曾经的视频,他满头黑发、身材微胖,虽然因为非典失去了妻子,却满怀新生的希望。影像中,他拉着全家去捐献血清,自己签署协议,愿意死后捐献眼角膜,捐出遗体用作医学研究。
但是,半年后,方渤几乎与杨志霞同一时间发病,双腿疼痛,呼吸不畅,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恶化。2005、2006年,他分别做了两侧的股骨头置换手术。2009年,医生从他破碎的右肩关节取出了指甲盖大小的碎片。
现在,他头发花白,两髋各爬着一条30厘米长的疤痕,身形明显瘦弱。“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一张动态的名单”
确诊后,包括杨志霞、方渤在内的更多非典后遗症患者聚集起来,他们从陌生到熟悉,从希望到绝望,从孤单到相守。他们从非典中死里逃生,却从此与疾病同行。
在不断的治疗和自我学习中,这个毫无医学基础的群体发现,造成非典后遗症的“元凶”,是曾经救过他们性命的“糖皮质激素”。
“每天14瓶液,从上午8点,连续输液到凌晨两三点。”目前仍需拐杖支撑身体的吴如欣回忆,而她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名为“甲强龙”的激素。
在那场突发的危机中,为了抢救生命和控制疫情,由钟南山院士首先提出的糖皮质激素疗法曾被大量用于紧急治疗,但此方法曾因各地用量不同等原因,引起广泛争议。
它如“双刃剑”般,一面挽救了很多非典病人的生命,另一面却因为不当的用量导致部分患者出现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在北京市政府登记的名单中,非典后遗症患者约有300余人,其中因公、非因公患者各占一半。
“这是我的残疾证,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走路超过10分钟腿内侧就开始疼。”靠着退休金,和老母亲蜗居在出租屋里的吴如欣总在想象,如果没有非典,如果没有后遗症,她的人生轨迹又会如何。
在2006年,方渤等病友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非典后遗症患者中,中重度抑郁症患者达到39%,80%因病离岗,60%出现了家庭变故。
采访中,小汤山医院、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曾经的主要负责人均表示,接收的转院患者中,由于有的在本院外治疗不规范,使用了大量激素等,给后续治疗带来了不少困难。
朝阳医院院长助理、呼吸科专家童朝晖回忆,2003年卫生部推荐方案中建议的日用量是320毫克。而在此后媒体的公开报道中,这一日用量在个别医院被大大超出。
“当时看到一些激素的使用方法和用量,我就觉得有可能会出现骨坏死的后遗症。”2003年5月,因为医护人员紧缺,望京医院骨科专家陈卫衡作为党支部*,被派往潘家园妇幼保健医院,深入非典一线。
发现问题后,他开始建议望京医院治疗组降低激素的使用量、加入中药应用,并在2003年撰文提醒政府不当使用激素疗法可能带来的后果。
“当年8月,我就参加了卫生部召开的第一次非典后遗症工作会议。”陈卫衡介绍,非典过后,卫生部医政司很快注意到激素治疗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
2004年2月开始,陈卫衡作为北京市卫生局“骨坏死与骨关节病”专家组中医组组长,每周前往小汤山疗养院为“因公”感染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治疗。
“当时对于‘非因公’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确实从卫生部也好,卫生局也好,都没有表示要扩大到社会人员。” 陈卫衡说。
同时,他也强调,2003年底,因为科技部启动与SARS相关的科研项目,一些医院开始从科研角度,利用科技部的资金,为筛查出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提供一些治疗。
据媒体报道,2004年3月底,卫生部正式成立非典后遗症专家组;2005年,北京市卫生局正式承认非典时接受激素治疗会引发后遗症,并于当年6月9日下发《关于贯彻落实感染SARS并发后遗症人员治疗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一方面是政府开始关注了,一方面是患者的反复诉求,在双方面的促成下,免费治疗得以扩大到‘非因公’群体。”
在陈卫衡的办公桌上,《民生周刊》记者看到了几份不同时间下发的《关于增加非典后遗症确诊患者的通知》。
“这是一张动态的名单。” 陈卫衡说。2008年,望京医院成为北京十几所非典后遗症患者定点医院之一,而需长期接受治疗的患者就达五六十人。此外,从2008年起,中国红十字会每年都会向每个后遗症患者提供一些补助,有工作的4000元,没有工作的8000元。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你身上呢?”
“人们都说不会遗忘,不会忘了我们,但是我做完手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面对媒体采访,方渤止不住地哽咽。2008年,他被诊断为抑郁症,曾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用破酒瓶戳伤了自己的额头。
在非典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被变化过快的世界遗忘。5.12地震、甲型H1N1流感……除了主治医生,其他人无暇回顾非典,甚至不知道“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存在。
在这个群体中,康复好的人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平静的生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还在遭受疾病的折磨和精神的自我歧视。
“他们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三月风》主编张立洁,偶然间走入这个群体。2006年末,她随残奥冠军平亚丽等残疾人代表一起到小汤山疗养院慰问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的“因公”非典后遗症患者。
“他们对于英模们的演讲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反而对落实工伤保险这样的实际问题更关心。”作为媒体人,张立洁敏感地意识到这群人的不同,也惊讶于曾经的白衣战士坐在轮椅上,精神萎靡,行动不便。
有救治的“因公”非典后遗症患者尚且如此,那“非因公”患者呢?从此,她将目光转移到“非因公”群体。
在接触中,张立洁了解到,与医务工作者相比,这些“非因公”非典后遗症患者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必要的医疗、物质支持。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你身上呢?”多年来,她用这个问题拷问自己,也拷问着别人。问题的答案,促使她拿起相机记录下这群人。
2009年5月,《SARS背影——被遗忘的非典后遗症人群》照片,在广州美术馆展出。这组照片中,每个主角看上去十分平和,但几乎鲜有人知他们凝重的眼神背后,有一段痛彻心扉的往事,一份余生保障的渴望。
2009年下半年,因为展出照片的牵引,两名大学生找到张立洁,希望针对非典后遗症群体做一个社会调查。在机缘巧合下,时任央视“新闻1 1”主持人的白岩松看到了这份调查报告。
“自从央视播了我们的情况,媒体才慢慢知道非典后遗症,才开始有人关注我们。”至今,非典后遗症患者仍感谢“无心插柳”的张立洁。
采访中,方渤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一家不愿露名的企业已答应出资,帮助这个弱小的群体建立基金。“虽然资金很少,但总归是个盼头。”
“千万别到让人伺候那一天。一旦住院动手术,我们请不起护工;一旦出现意外,同样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家人怎么办?”比起自己的身体,让方渤更揪心的是两个女儿。
当年,女儿、女婿同时被诊断为非典后遗症,为了不相互拖累,他们双双选择了离婚。再以后,小女儿远嫁东北……
“人不能十全十美,也许就是我的不幸,才能保佑我家孩子过得好。”经历这么多波折,杨志霞的言语中多了一丝“宿命”的意味。“现在最高兴的事,就是小孙子的出生,我应该会过得充实了。”

出品:民生周刊(ID:msweekly)新媒体事业部
记者:陈沙沙
责任编辑:刘烨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