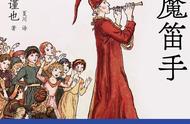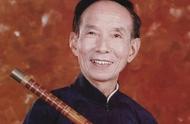重回巴黎进行阅兵的外籍军团
二战结束后,刚刚光复的法国政权开始醉心于殖民帝国的重建。无论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还是远东的印度支那地区,都急需大量法国殖民地部队进驻,以巩固法国对这些传统势力范围的控制,重新树立“法兰西的荣耀”。为了再次掌控这些殖民地,法国外籍军团作为法军殖民地部队的精锐之师,其历史传统注定它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二战初期,维希政权为讨好纳粹德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军团中近1万名德国士兵遣散,规模将近部队员额的一半,造成了外籍军团实力的重大损失。同时,一部分的外籍军团部队加入到自由法国战斗序列(尤其是外籍军团第13团,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创建之初唯一成建制加入的外籍军团部队),外籍军团的国际化性质及其勇猛顽强的作风,对于当时主要依靠殖民地部队作战且面临士气与盟国信任问题的自由法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军团力量薄弱的现实与领导层的重视,使得外籍军团的征兵工作在战后立即被法国军方视为当务之急。

解散后被缴获的外籍军团军旗
然而,在二战战后荼毒过的欧陆,各国人民普遍厌恶战争,而且适合入伍的青少年本身也极为缺乏,被各国政府视为战后重建的重要人力资源而加以严格保护。以外国人为主要作战力量的外籍军团面临着征兵无门的窘境。而德国作为外籍军团传统的兵员出产地,那些年龄尚轻却有着丰富从军经验,且在盟国占领下饱受社会排挤及占领者猜忌的退役德国军人是其易于招募的不二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军方在自1945年大举攻进德国本土时起,便在德国境内秘密开设征兵点和转运中心,以向外籍军团大量输送德籍佣兵。为了能够在保密前提下满足军团的大量征召需要,大量法国征兵人员被派到德国境内,以各种手段吸引德国青少年秘密地参军入伍:
“在(德国)投降后不久,打着法国红十字会标记的海报就在帕拉提纳的每个车站贴得到处都是,都是邀请德国青年加入外籍军团的。在朗道的一家小旅馆里,说着一口地道德语的热心法国人把入伍合同展示给德国人看,慷慨地把一瓶瓶好酒往他们喉头汩汩灌下,承诺给他们一份不错的薪水以及年老后有保证的退休待遇,描绘着5年服役期满后的大好人生。”
为了能够更有效率地征召士兵,征兵官员甚至组团深入到盟军战俘营中,利用德军俘虏的绝望心态,说服他们为军团服务来换取出路,如当时一名受到征召的俘虏兵的回忆:
“1946年5月23日,有一个委员会到了我们战俘营里。他们讲着蹩脚的德语。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军团里干了20到25年了。他们跟我们宣讲加入外籍军团的事情。他们许诺说我们会吃得很好,有跟法国士兵一样的待遇、休息和假期。我们必须参军五年。我当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离开战俘营,在那儿人是会被活活饿死的。我跟其他22个人一起签字加入了外籍军团。”
然而,随着1946年印度支那战争的爆发,军团所提出的兵员要求激增,即便是德国人也害怕被当做炮灰投入到另一片血腥战场之上,征兵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征兵人员甚至开始公然采取欺骗讹诈的手段,迫使德国青年签下入伍合同。正如一份德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各地甚至出现了“在车站附近徜徉的神秘女孩,勾搭着年轻人来招他们进外籍军团”,而她们正是征兵官们“出于纯粹蓄意的目的”而安排的。
在不莱梅(Brême)发生的一则事件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范例。根据1948年6月2日法国驻德大使致占领军方面的一则照会,有多名想去法国做劳务输出工作的德国年轻人,被外籍军团强行骗召了进去:
“其中一名年轻人,就能否前去法占区应征充当赴法劳工的事,请教了法国在科隆(Cologne)的领事。
在非法进入法占区之后,他被拉斯塔特(Rastatt)一处劳工营地接收,然后通过多瑙艾辛根(Donaueschingen)的营地,到达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的移民营地,在那里跟150位其他赴法劳工候选者一起前去法国移民办事处。但只有5名候选者被录取了。其他人则被送到了弗赖堡。在那里他们被安置在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着的营房里。
在到达当晚,他们受到邀请去参加一个‘告别德国’晚会。他们被安排围坐在铺着洁白桌布的餐桌旁,可以随意点酒水吃喝,后来又被引到一个人人都能找女伴的大厅里。他们又是喝酒又是跳舞,甚至还给他们安排了小房间,让他们可以跟女伴们厮混。
晚会最后,一些营地工作人员现身并且要这些此时已酩酊大醉的年轻人签下一份说明参与了这次晚会的所谓发票,以便营地向上头报销此次消耗的酒水和生活用品。
由于当时的参与者已没有人清醒到可以确认这一‘发票’的抬头,所以每个人都稀里糊涂地签了字。之后他们就被带回了宿舍里。
第二天早上早饭后,他们在11点时被集合在营地的操场上,并在点名后被分成了若干小组。
一名法国军官向每个小组发言,就他们签字志愿在外籍军团服役五年而致谢。
昨晚签下的‘发票’被远远地向每个抗议或表示质疑的人展示出来。反抗看起来是毫无用处的,这些小组一直被扛着卡宾枪的波兰和捷克籍士兵看守着。”

训练营中的外籍军团志愿者
一个亲历者在转运过程中逃脱了,并且把所发生的事报告了不莱梅的法国领事。他的声明后来被另一个青年脱逃者的证词所证实。当时的法国驻德大使圣哈罗丁被这一消息震惊了,他立即要求军方就此进行调查,但是却遭到法国陆空军总参谋部秘书长矢口否认:“我们看不出为什么要对这些德国青年采取这种强迫措施来逼他们参军,要知道我们每周都要在那些官方的征兵点里回绝上百个应征者呢”。可是,1949年初,在德方当局的支持下,这些脱逃的证人的证言被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自由民主党官方刊物《西德月刊》(Westdeutsche Rundschau)刊登了出来,以抗议法方利用希望赴法工作的德国工人进行外籍军团征召的行为。他们的声明见刊后,得到了上千正在军团内服役的德国人从印度支那发来的回信佐证。这使得法方军政府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之中:他们一直极力回避提及征兵问题,但这一报道不仅揭露了这一情况在德国的存在,还昭示了法国征兵人员的欺骗伎俩。而在1951年底外籍军团在德整编转运中心关闭之前,类似的法军“拉壮丁”故事一直在德国各地流传。大量青少年无声无息间悄然失踪,造成了德国居民的私下的担忧与恐慌: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外籍军团让我们担惊受怕。我们刻意无视这一‘外籍军团’(Fremdelegion)的一切存在。你们法国人也是,你们对此也不甚了解。在当时,有太多的规则被打破了。当年轻人进到这些征兵办公室之后,第二天就会消失无踪。他们的父母四处寻找他们。这就好像盖世太保回来把他们统统抓走了一样。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了。这种情况维持了好几年。有许多曾经的党卫队员选择了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法国人需要这些健康能打的年轻人来代替他们自己在印度支那打仗。他们从不多提问题。只求能提供更多的炮灰,所以通过军团的‘甄别’程序并不算困难。那些党卫队的罪犯利用了这一情况。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事,但我们不能张嘴吐露实情。”
即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判断,对于当年那些背着“战俘”、“党卫军”、“纳粹”罪名的德国年轻人来说,外籍兵团对他们的征召究竟是灾难还是幸事,他们在印度支那战场的遭遇到底是惨祸还是报应。当时的德国新闻界估计称有5万德国人在被招进外籍军团后战死越南,最近的研究认为至少有2621名可以确认查证的德国人在越南阵亡——这个数字其实要大大少于真实情况,因为军团军人有权以虚假的国籍身份入伍。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尘封在法国外交部秘密档案之中的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与证词。但无论如何,在好不容易恢复了和平的欧洲,在已经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德国,大批本该在战后重建中赎罪并为和平做出贡献的青年,却被引导去走上了为殖民战争而流血的道路,这无疑是一出悲剧。这场在战后德国无人承认却又人尽皆知的秘密征兵,犹如一场现代版的哈默林“吹笛人”故事。外籍军团吹起了花哨的笛声,引诱着德国的年轻人们消失在遥远的远东战场。对于他们身为战败者、被占领者的德国同胞而言,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童话始终萦绕在占领时代的社会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