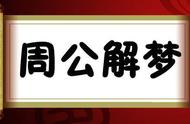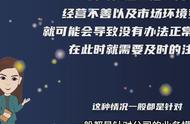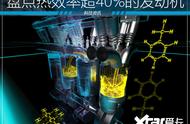在佛教里,像《大智度论》、《善见律》、《大毘婆娑论》,都曾提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梦。以《毘婆娑论》的记载,来说明五种做梦的原因:四大不调,身体种种不顺的时候,容易做梦。例如梦到山崩,被盗贼追赶,或者梦到猛狮凶虎,甚至梦到自己遨行天空,不小心跌落凡尘。总之,病人所梦到的梦境,大都是恐怖、惊惧、骇人听闻的情形。思维的梦大都和平常生活有关,诸如感情、情绪的不安,小自生活的细节,大至工作上的各种状况,都可能会夜入梦中。这种梦境,常有男女感情、朋友交往,甚至争吵、激辩等情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