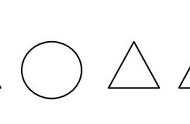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冬眠”之名有一种荒凉沉寂之感。影片中的世界也确如冬天沉睡的大地一般,缺乏生机和希望,没有劳作的痕迹,没有耕耘的必要。也许,这片土地在等待一个合适的节令,破茧而出,蓬勃生长

《冬眠》由努里·比格·锡兰执导,哈鲁克·比尔吉奈尔、梅丽莎·索岑、戴美特·阿克拜格等主演,于2014年6月在土耳其上映,2019年6月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退休演员艾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经营着一家小旅馆,与妻子尼哈尔的感情已不复当初。他的妹妹,则沉浸在离婚不久的痛苦之中。随着冬天的到来,白雪覆盖大地,旅店成为他们的庇护所,同时也成了一座舞台,上演了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
《冬眠》的片长将近200分钟,曾获得第6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是一部盛名在外的电影。当然,熟悉导演锡兰的观众都知道,时长充足并不意味着情节丰富、戏剧张力饱满。因为,时长可能是由大量的日常对话、争论、生活场景的纪实性还原而填满的。甚至,对于《冬眠》《野梨树》之类的锡兰作品来说,似乎存在一个艺术上的诘难:在拿掉大段的对话或辩论之后,这些电影能够艺术自足吗?如果能,为什么要卖弄深刻,折磨观众?如果不能,电影本身的特性和优势又何在?
好在,《冬眠》中的对话并不高深,而是在日常性的琐碎与跳跃中不经意地闪烁着洞见。可以说,在影片的情节框架之外,这些对话似乎在演奏一个个独立的乐章。这些乐章有效地丰富了影片的情绪内涵,但又努力不以喧宾夺主的姿态打乱观众的观影进程。甚至,这些对话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故意减缓情节的推进速度,使观众有机会在情节停顿时得到思想驻足的片刻——而真正的挑战在于,那些散落在对话中的情感或思想刺激,可能与观影者的心跳不处于同一个频道,甚至与影片的主题相隔遥远,因而难以让观众产生共鸣的感动。

这就注定了《冬眠》的观影不会是轻松流畅的,不会如微风拂过湖面般轻柔惬意,而是如越野车行驶在戈壁一般,偶尔有险峻奇谲的风景,但也经常性地陷在沙坑里,需要下车推行一段。或许,崎岖而颠簸的旅程结束后,观众内心深处会留下只可意会的情感撞击,并形成宽广的涟漪荡漾不已。
《冬眠》虽然情节简单,涉及的人物却不少。考虑到锡兰一贯的处理手法,影片中的人物往往会在处境与选择、人生态度与价值观上形成多元的映照关系。这样,每个人发出的声音汇合成一曲多重奏,但这曲多重奏的主旋律又是清晰有力的。解读《冬眠》的切入点,正是对人物处境与选择的充分理解。

具体而言,艾登沉醉于虚幻的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之中,并因此显得有些倨傲和强势。尼哈尔则想通过做慈善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却不愿正视慈善的现实支撑来自于丈夫的物质保障,甚至从未反思过这些善举的意义以及对于他人的尊重。艾登的姐姐满足于慵懒而闲适的生活,不愿奋斗,也没有人生目标,但自我感觉良好。哈姆迪虽然贫穷无依,但对于尊严和礼节极为看重,为人谦恭克制。至于哈姆迪的哥哥,身处底层,却对于他人的施舍极为敏感,对于尊严的维护近乎偏激。
影片中的人物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衣食无忧者如何填补内心的空虚与人生意义的苍白(以艾登为代表),衣食无着者如何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守护尊严(以哈姆迪为代表),暂时安稳者如何提升自我的人生价值(以尼哈尔为代表)。这三类人物,虽然在经济地位上有着天渊之别,但虚无均与他们如影随行,他们要么在拼命抵抗虚无,要么在偏执中陷入虚无。

正因为处境与选择迥异,影片中的人物基本上无法交流,而是秉持着各自的价值立场和世界强硬对决,与他人形同陌路或者貌合神离。例如,尼哈尔一语道破艾登的伪善:抛出良心、道德、理想、原则、生活目标的大旗,来虐待、伤害、羞辱别人,贬低别人。可是,尼哈尔为了彰显自己的道德高贵,拿着一笔巨款无来由地送给哈姆迪,不同样是伪善吗?因此,影片关注的焦点并非仅仅是人的物质困境,甚至也不是精神困境,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彼此难以沟通、无法共鸣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没有现代性的荒诞与黑色幽默,也不是社会意义上的阶级差异或对立,而是每个人对于尊严、人生意义的不同理解所致。
影片的时间背景是冬天,“冬眠”之名有一种荒凉沉寂之感。影片中的世界也确如冬天沉睡的大地一般,缺乏生机和希望,没有劳作的痕迹,没有耕耘的必要。也许,这片土地在等待一个合适的节令,在默默地积蓄力量,为的是在某个时刻破茧而出,蓬勃生长。但我们也知道,《冬眠》不会为观众提供虚假的乐观和虚幻的圆满,人物也许会进行一番突围的尝试与努力(如艾登与尼哈尔),但那些疏离与隔膜仍然存在,人生的重大空缺依然在难以察觉的暗处张着血盆大口。(龚金平)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面向社会长期征集优秀稿件。诚邀您围绕文艺作品、事件、现象等,发表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的评论意见。文章2000字以内为宜,表意清晰,形成完整内容。来稿一经采用,将支付相应稿酬。请留下联系方式。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投稿邮箱:wenyi@gm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