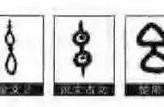kiwi
看起来很像猕猴桃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寻常见到的猕猴桃,果柄多已掉了,若是还带着柄,就和kiwi这种鸟更像了:

kiwifruit/猕猴桃
新西兰人以kiwi来称呼这种水果,正和我们以猕猴来称呼这种水果一样,都是找个和它像的动物,借其名字来用。

猕猴
前面说到kiwi是新西兰国鸟之名,这种鸟虽然是鸟,却没有翅膀,样子怪得很。但它的名字kiwi却并非要说它样貌“奇异”,而是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参照它的叫声给它起的名字,这就好像如今很多人以猫的叫声“喵”来直接指称猫一般。而kiwi这种鸟的中文名,本来或按发音译作“几维鸟”,或以较为传统的方式命名作 “鹬鸵”——我猜是因为它长了个鹬一样的长长的喙,而体型则像鸵鸟;另外也有直接称为“无翼鸟”的。
至于“奇异鸟”这种叫法何时兴起、起自何处,一时无从查考。不过既然台湾地区最先弃“猕猴桃”这一唐代已有的称谓不用而改用 “奇异果”,那么大概“奇异鸟”这种通俗的译名,也出自台湾。以“奇异鸟”来译kiwi,本也不错,发音相近,意思上也说得过去——鸟而无翅,确实奇异。但将“奇异”二字挪用到猕猴桃上,却有些奇异了。
不过对于内地的水果商来说,要把进口的猕猴桃卖高价,“进口猕猴桃”这样的叫法总是不太好使的。要想改变事物的价格,先要改变事物的名称。于是新西兰进口猕猴桃变成了新西兰奇异果,身价倍增起来。据此推想,也许当年台湾弃“猕猴桃”而用“奇异果”,也是进口商人的营销手法在词语上的体现吧。
车厘子自由的来龙去脉日常事物的名称忽然发生改换并非中国独有之事。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八十年代,也见证了类似的变迁。“那个时代,‘法式面包’变成了‘バゲット’(注:以假名拼写的baguette,读作“拔盖都”),而‘意大利面’变成了‘パスタ’(注:以假名拼写的pasta,读作“帕斯塔”),通过这些词的变化,大家应该能对当时的氛围稍微有所理解吧。”在《“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潮流》这篇追述日本消费文化变迁的文章中,井出幸亮如此写到。
意大利面在日本变为“帕斯塔”(パスタ),正如樱桃在中国变为车厘子(cherry)。现在我就等着看,哪一天北京的草莓开始改叫“士多啤梨”(strawberry)。
然而这个来自香港话的“车厘子”并不像来自台湾国语的“奇异果”,能像上文那样讲上一大通。这个纯然的音译并无深意,虽然它在营销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让“进口大樱桃”听起来更洋气,卖个更好的价钱。
闲话不多讲。熬过了连天的沙尘和雾霾,3月29号那天我看天气正好,吃过早饭就动身出发了。十点四十五从鼓楼大街地铁站出来,走不多远就是“新民菜市场”。这里的早市十一点半打烊,据多位点评网友讲,临收摊时车厘子最便宜,可以10元两斤拿下。

地铁鼓楼大街站,出来走两步就能看到新民菜市场
进市场走了一圈,立着车厘子10元一斤牌子的摊位一家也没看到。摆着车厘子的摊位连问了几家,有80一斤的,有65一斤的,最便宜也要55一斤——但个头明显比80一斤的要小不少。
心里正犯嘀咕,看到一个摊位立着块牌:“西梅10元两斤”,摆的却是紫色的李子和大红李子。
我凑上前去问老板:“这个怎么卖啊?”
“十块两斤,不挑给三斤。”
我要了个塑料袋开始挑选。
“这西梅是哪儿产的?”
“新疆的。”
“两种都是吗?”
“都是。”
“两种有什么区别?”
“这种是红心的。”老板指了指红李子说。
我拿了两个紫色的李子,三个红李子,递给老板称。
“七块。”
十块两斤,七块就是一斤四两,五个李子绝不会有一斤四两。
我微信付了账,至此,老板已经确定我是一个分不清西梅和李子、也弄不清斤两的白痴了。
人对白痴有时是有同情心的。
“我看网上说有便宜的车厘子,怎么没看到啊?”
“那些都是存货了,不好。”
“存货?”
“对,都是过季的,不好,发苦;现在是吃山东樱桃的时候了。”
怎么才初春,就“过季”了呢?
原来中国冬季市场上销售的,都是来自南半球的车厘子,其中又以来自智利的占比最高,接近九成。每年11月到1月是智利的春夏时节,也是智利车厘子成熟上市的时候。今年智利车厘子丰收,比去年增产了近40%,供给增加了,价格自然会降低。有国内媒体报道,一月初长沙市面上的J级车厘子,就有每公斤售价只要20元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