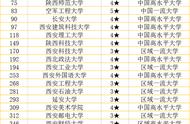感谢黄敏捷老师赐稿
本文原载《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私雇代役
——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
文丨黄敏捷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讲师

摘要:宋前期,民户为逃避职役重难,采取私自雇人代应州县役之法,朝廷对此屡禁不止。熙丰行雇役法后,以往的私雇代役人转换成为官雇役人,人数与专业性都得到发展。元祐时期朝廷试图恢复职役轮差之法,但承认私雇代役,于是州县役的代役人通过转换官雇、私雇,长期留于州县,渐与胥吏混同,使得衙前与州县役不再成为乡户之困,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私雇代役现象遂有下移至乡役之势。至南宋,乡役雇直全被挪用,朝廷亦无法禁绝民户私下雇人代应保甲乡役,私雇代役由此成为南宋民户应对职役困苦的另一途径,且向义役渗透,成为南宋官府安排职役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后代职役雇役化的经验来源。
关键词:职役 代役 免役法 义役
唐代时开始,官府轮差乡户负责乡村的治安、收税等工作,或在州县充当办事人员,这种义务承担的“职役”,至北宋前期已成为困扰地方社会与宋朝基层统治的严重问题。宋人为解决此问题而掀起的历次役法改革也因此引起学界重视。[1]但前辈学者多从制度流变的内容讨论差役法与雇役法,而对两宋民间在制度外的应变则罕有关注。只是,役法条文的规定并不能看作是社会经济运行状态的直接而简单的投射。宋代役法在实践的终端,并不如人们熟知那样差雇界限分明。在朝廷行差役法时期,基层社会相承一套私雇代役的办法——被差乡户通过雇佣代役人,摆脱亲身应役之困;当朝廷行雇役法时,主户则向官府交纳役钱,由官府代为雇役。由是,无论朝廷采取何种役法,对于相当部分民户而言,差别不大。
本文所说的代役,是指受雇佣为他人代行职役义务之行为,代役之人如受官府所雇,代役对象为全体应役主户,称为官雇代役;若为私人雇请,为特定应役主户代役的,则为私雇代役。南宋时,州县与民间开始探索“义役”这一新的应役形式,其中一些义役组织以义田之收入“佣闲民之无职事者,以服其役”。[2]此类受乡民集资雇佣的代役方式,本文也将之归为私雇代役的范畴。作为基层对朝廷政策变动的应物,私雇代役行为游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州县因私雇代役人的存在,获得了较熟练的办事人员;又因民户的私雇行为减轻了差役对基层社会的滋扰,兼得行政效率与基层稳定之利,所以州县在朝廷禁止私雇代役时对之心照不宣,由是官方记录中较少见到相关记载;代役人因脱离了农业生产而被士大夫斥之为“游手”、“浮浪”,故私家记述又难免偏见。笔者欲考寻现有资料,探明在宋代不同职役制度下私雇代役形态的变化及其对基层社会、官府乃至朝廷政策的影响,借以观察社会变迁与宋代税役制度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私雇代役现象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私雇代役之现象,前代较少。与宋代职役相对的唐代色役与杂任,虽有纳资代课之做法,但多表现为官府影占纳课,并非真正雇人代任杂职,更非民户私下雇人代役。[3]就目前所见,唐时只有“烽丁”一役出现过应役者因农忙临时雇人上烽现象,或可视为两宋代应职役者的滥觞。[4]
宋前期私雇代役现象逐渐发展,有其原因。入宋以来,地方公共事务明显增多。一是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增加了州县财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的任务;朝廷为监控地方财政,也提高了对州县账籍管理与传递的要求。二是两税法以财产为宗,其计征之繁难远超此前的定额人头税;三是宋廷为保障税源,认可并保护土地的产权交易,“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5]一方面使产权交易的手续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使官府办理产权交易的事务急剧增加。加上随之而来的宋代民户逐渐滋长的产权意识,使得围绕产权问题的诉讼增多。[6]以上变化都要求地方官府内部有更细密的分工,更专业的吏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7]但与这种日增月长的需求相对的是,政府的机构与人员配备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上述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基本由政府强压职役人员来弥补——宋政府的行政机构,最基层只及县,县以下广大乡村管理的资金、人力皆从职役出;甚至在州县层级的官府内,也存在大量由从主户中抽差的役人,承当官府的日常公务与地区间长距离纲运等工作。乡差应役人是“田野愚戆之人,不能干事”,[8]不但使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弊病丛生,而且这种轮差乡村上户,要求他们无偿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亦破坏民户的正常生产与财富积累,导致宋代职役问题超过夫役,成为人户的重要负担,即所谓“郡吏之不足,役及上农,而使之*竭财,而毙于冻馁”。[9]
与唐代色役按丁佥派不同,宋代的职役按户等、资产轮差,应役者为多少有些恒产的主户;与离乱频仍的唐末五代相比,宋代有较稳定的生产环境与相对高的预期收入,所以面对差役带来的破家荡产之害,主户对举家逃亡隐匿又比前代农民持更谨慎的态度。[10]不过,宋代活跃的商品经济、较高的生产率、较细的社会分工以及雇佣劳动的发展,[11]使宋代民户除贿赂官吏或托庇于形势以外,多了一个化解职役压力的手段,那就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能者代役。
宋代的职役名目繁多,若结合服役层级与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主要服役于州县各机构,本文将之称为州县役;一种服役于乡间,主要负责催税与治安,是为乡役;第三种为比较特殊的衙前役,主要由上户充任,负责纲运、主理公使厨库的运营等。
乡役在宋前期主要包括耆长、里正(户长)、壮丁等名目,大多被视为轻役,里正在宋初催税任务不太繁难的情况下,更是“号为脂膏”,[12]因此代役需求不多。衙前役对应役者的财产要求颇高,且在仁宋时已经采用先投名,不足方轮差的原则,[13]有能力与意愿代役之人一般已经通过投名入役,博取坊场酬奖,因此代衙前役的现象亦较少见。因此,宋前期的私雇代役行为往往出现在州县役领域。[14]
现存资料较集中记载私雇代役现象的是近边与川界弓手之役,如庆历二年(1042)诏书中说:“以河北、河东弓手为军,……而诸游冗之人,皆愿雇代人入籍。”[15]之所以会在那些地区、会在弓手这一役种出现代役行为,主要由于这些地区的弓手役对民户干扰极重,与内地不同。宋夏战争时凤翔府通判言,近边弓手“并不限十月初、正月终,但遇边上有事宜紧急,便许府郡勾集防护”,[16]不仅随时可能被召集,妨害农时,且从事的是军事行动,危险性比内地弓手高得多,因而“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心恐,不自安”,[17]川陕、河北、河东弓手私雇代役的需求遂高于内地。朝廷对这类代役现象也试图禁止,却未能奏效。如真宗时规定“禁两川诸县弓手雇人代役,犯者许邻保纠告,重绳之”,[18]仁宗时又“诏两川弓手自今不得雇人代役。……时吕夷简……言川中豪民咸佣夫以代杂役,多得惰农,每执杖悉不得力,故有约束”。[19]“自今”一词透露出当地对私雇代役的禁令一向执行不力的实情。
另一个较明确存在私雇代役现象的领域是州县曹司诸役。由于两税法背景下州县曹司之役对书算技能要求日高,故此在乡户文化普遍不高的地区,涉及书算、簿记工作的手分、贴司等役种被视为重役,私雇“惯熟官司”之人代役的现象遂无法禁绝,而州县出于完成工作的需要,也不想去禁绝。章惇说,“州县曹司旧法差役之人,……其所差人,往往不会行遣,惟是雇人代写文书,所差之人但占名著字,事有失错,身当决罚而已”,[20]可知熙宁以前被差乡户私下雇人代写文书并非罕见。或许正是宋前期私雇代役与投名应役的存在与发展,启发了王安石等人不再象仁宗时期那样以“均役”为解决职役问题的着力点,转而以官雇代役人作为役法改革的突破口,以征收役钱作为官雇役人的资金来源,使发自民间的代役现象成为政府推行的正式规则。[21]
二、熙丰后期至北宋末私雇代役领域的变化
熙宁二年(1069),制置三司条例司首次提出募役法的原则:“昔于乡户差役者,悉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以所赋钱禄之。”[22]这是朝廷首次全面以官府名义雇募代役人,也是首次给代役行为以合法地位。往日的私雇代役人或通过投名,或被州县官府“勒向来受雇行遣人充手分,支与雇钱”,[23]成为官雇代役人,代役行为被纳入官府管理体制之内。
熙丰时期,官雇代役人来源各异、数量庞大,官府对他们的雇募与管理,为北宋后期到整个南宋的代役体制构建了基本框架,也为元祐时期的私雇代役提供了人力上的准备。到熙丰后期,北宋前期困扰民户的衙前与州县役,随着官雇代役人的持续存在并且日益胥吏化,渐与乡户远离,民间对此类役种的代役需求消减;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民户的私雇代役需求遂有下移至乡役的趋势。
(一)州县役代役人地位日渐巩固
元祐元年(1086)二月六日,朝廷下诏全面恢复差役。但诏令中对代役的态度却颇值得注意。诏令一方面批评雇役法“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失,变姓名,别往州县投名”,只会给官府带来损失;但另一方面又说“不愿充役者,从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也就是允许私雇代役,只是“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却官物,勒正身陪填”。[24]可见,作为诏令的起草者,司马光虽极不信任代役人,但熙丰年间(1068-1085)形成的民户对代役的依赖又极难扭转,于是,私雇代役成为一种折衷办法。允许私雇的实质,是在官府与代役人之间增加了被差乡户的家产这一层担保,也就是把约束代役人的费用与官府损失的风险转嫁给了被差乡户。同为旧法大臣的刘挚对此规定颇为不满。他说:“役人正身不愿者,今来兼许雇人。而嘉祐旧制,如耆长、弓手之类,须正身充役。”[25]他这番话说明,司马光虽以恢复嘉祐旧制为号,但与刘挚等官员相比,他对行雇役多年后形成的社会状况还是有相对清醒务实的认识。以司马光的威望与身份,他对私雇代役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新的信号。
与反对雇役的元祐重臣对代役人的戒备心态相异,州县对代役人却十分欢迎。恢复差役的诏令行下后,马上就有州县利用朝廷允许私雇的规定抵制乡差役人、留用熙丰时曾受官雇的代役人。王岩叟说:“诸郡县官员有自来雇募到承符、散从官、手力之类在逐厅,今例合差乡户抵替减放。逐官有以乡户生疏,雇人惯熟,不容乡户正身自充,须令雇召。”他建议朝廷宜有约束。[26]但由于元祐初新党势力尚未完全退出朝廷,[27]加上旧党中一些熙丰时期曾任职基层的官员,如户部尚书李常、详定役法苏轼等人都对全面恢复差役有所保留,[28]因此详定役法所建议朝廷发下的所谓约束,倒更象是默许:“郡县官员如敢抑令本厅新差役人出钱,指名雇觅自来使令之人充代祗应者,……重行黜责。如役人委寔情愿雇人者听。”[29]最后一句无疑给了州县上下其手的空间。于是州县或“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钱,作情愿雇募”,或“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换别差,必得惯熟如意而后止”,[30]使那些熙丰时期已经在衙门取得丰富经验的“惯熟如意”的官雇代役人,表面上虽被乡差役人所代替,但实际上却以“役人委寔情愿雇人”的名义,转换成私雇代役人,继续留在州县服务。
到元祐元年(1086)十月,几经激辩,朝廷又放开了对私雇代役弓手的禁令,诏“弓手正身不愿充役者,许雇曾募充弓手得力之人,仍不得过元募法雇钱之数”。[31]至此,州县各役,皆可私雇,熙丰时期的代役行为,在元祐以私雇的形式,大部分保留。绍圣初,杨时追述说:“浏阳之民未罢役以前而雇人代充者,皆月计其直,然每有踰期不偿,而至于理诉者,时时有之。”[32]雇主与代役人由于工钱纠纷而闹上州县者“时时有之”,说明元祐恢复差役、承认私雇的短短数年,私雇代役现象之膨胀。
元祐二年(1087),随着元祐政府日渐发现财政对役钱收入的依赖,加上民间对差役频繁无可休替的怨声日高,朝廷又恢复部分役钱的征收与州县役的官雇, [33]此后,虽细节上有所变动,但元祐政府承认私雇代役,并在州县役层级差雇兼行的政策一直延续。州县中代役人之位置由此更加稳固,他们通过转换官雇、私雇的身份,长期混迹州县,继续其吏员化趋势。[34]
(二)乡役代役需求增加
熙丰时期,官雇落实得较好的是衙前与州县役。衙前、州县役的重难部分如纲运、接送、主管官物等职责被分拆出来,由军吏、得替官员等人承担,后为各朝沿习;[35]稍轻的州县曹司之役,元祐以后其代役雇直也基本得到维持。这预示着上述公共服务自后已基本由官府自行提供,不须再轮差乡户。
但是,乡役层级的情况则复杂得多。由于北宋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加上朝廷的控制力到县以下就迅速减弱,况且乡役人是否专业,对官府而言影响也不及州县役那么切近,故熙丰时期的乡役就已无法保证完全官雇,[36]乡役雇直亦是被挪用最多的部分。自熙宁后期开始,以增强治安为主兼有乡兵功能的联户组织——保伍系统,以及为推行青苗法而组成的结甲组织,开始与职役系统中的乡役部分融合,也就是乡村中以轮差的保正、保长、甲头系列逐渐取代要雇募的耆长、户长、壮丁等乡役名目,负责催税、承受文引和其它基层管理工作。[37]在衙前、州县役维持官雇的背景下,这套新形成的“保甲乡役”[38]体系加于民户的负担逐渐突显。于是,又开始有不愿亲身应役之民户,寻求私雇代役之法。熙宁五年(1072)八月,中书门下奏,“保丁……私为人代名上番,杖六十”。朝廷需要明令禁止,反映保丁代人上番之事已非偶然;[39]元丰八年(1085)八月,刑部奏钞中提及一个斗*案,其中的当事人,泰宁军“代名大保长张存”,亦为受私雇代役之一员。[40]在保甲制有提举官专领,保正长们可以“依倚弄权”[41]的熙丰时期,尚有人不愿亲自服役,私自雇人代名应役,可知保甲乡役的无偿化与强制性,是熙丰以后代役需求由州县役下移至乡役的主要原因。
绍圣至北宋末,州县役全面恢复官雇之余,亦曾尝试恢复乡役雇直,但收效甚微,[42]反而苛扰保正长等保甲乡役人的记录却不断增多。[43]这些都为南宋时期乡役层级私雇的爆发性增长埋下伏笔。
三、南宋私雇代役的发展
正德《松江府志》云:“绍兴间,图适厥中,衙前弓手则用雇法,乡都保长则用差法”,[44]概括了南宋在继承北宋中期职役改革成果的同时,也沿袭北宋后期产生的新的职役弊害的特点。
南宋初,朝廷财政危机频发,迫使州县想方设法竭泽而渔,[45]保甲乡役不但成为无偿之义务,[46]而且被赋予更多基层行政职能,成为州县转嫁财政压力与聚敛阻力的对象,“民当正、副,必破其家”,[47]保甲乡役的代役需求更为增长,乡役遂成为专业化的代役人发挥所长的新领域。现存记载私雇代役人的史料,关于北宋的,多集中于州县役,反映南宋时期的,多集中于乡役,亦殆由此。
南宋时的代役形态主要表现为:朝廷被迫默许私雇;私雇代役人活跃于保甲乡役的同时,开始向义役组织渗透;私雇代役现象成为南宋官方考虑职役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一)朝廷默许私雇
与元祐时承认私雇的合法性不同,南宋初以恢复嘉祐旧制为号,要求乡户亲身应役。但经过北宋多年的发展,代役已成大势,故而南宋时的这种规定不但实施难度更大,对基层社会的干扰也更多,民户常为此聚讼纷纭,占用官方大量的行政资源。[48]迫于现实,朝廷逐渐放宽了对私雇代役的限制,陆续规定一些没有亲身服役能力的民户如高物力单丁户、寡妇有男为僧道成丁之户、老疾侍丁户、坊郭遥佃户等可以私下雇人代役,[49]后来又放宽到一些特权阶层,如僧道、太学生、部分官户、得解举人等,[50]“官司不得辄追正身”。但这也为普通主户非法私雇代役人开启方便之门。面对民间越来越多的私雇代役现象,有官员建议朝廷干脆完全解除限制,如“左朝散郎陈璹知饶州代还,论诸县保正副长,科役烦多,尤为民害。……望特诏有司,许凡当役保正副长,除情愿应役之人,听其从便外,并许雇人代役”,[51]当时虽没有得到朝廷的明确回应,但到光宗时,臣僚又反映,“在法,差保正许募人代役者,自有定制,如官户、寡妇之类是也。今富有之家应身充役者,往往亦募人代役”,违法私雇代役人的现象已很普遍。而该大臣说,因为由于代役人借派送传票、帮官府催税办事之机敲诈民户财物,因此建议“自今代役人有犯,其违法募之者不觉察,当于案后贴说,坐以‘五保内有犯,知而不纠’之罪”。[52]当代役人作奸犯科时,才以知而不报之法惩办雇主,并不言追究其违法私雇代役之罪。朝廷同意此建议,实际上也是对富户私雇代役的让步,私雇代役由此深入南宋职役各层面。
(二)私雇代役渗入南宋义役
南宋时义役成为民间应对乡役的一种重要方式,[53]孝宗(1162-1194)时程洵概括义役的主要实施形式“大要有二:有分岁月而人自为之者,有裒其费而众募人为之者”,[54]说明义役组织也存在集资雇佣代役人的现象。梁庚尧甚至认为义役团体集资募役比团体中的民户亲自应役的情况更多。[55]
以集体之力应付差役的“义役”,亦不能无弊。相较而言,“分岁月而人自为之”的形式缺陷更多。“中户以下旧来不系充役者,皆拘入义役”,“此等人户,县道生疎,支吾不行,……间有主役而不仁者,反为打话卖弄之人,充役之家一举遂空”。[56]役首排役不公,导致在义役组织里的中下户不但仍受轮差之苦,还增加了受役首侵渔的风险,并无享受到义役的好处。但以义田收入雇募代役人的地区,此种漏洞则大为减少。
黄震在江西提举任上,惩本路义役之弊,在下辖各县张榜推介台州义役的“雇募长役”之利:“上户各出田供长役之费,……而役事自有义役庄田雇募长役,人户并不知有役事之扰。” [57]其实台州黄岩地区在嘉定五年(1212)初行义役时也曾出现“田连阡陌者捐助或不毫毛,仅仅及等者反困抑”的窘境,至淳祐九年(1249)重整并改为雇募代役人后才有黄震所描述的盛况。刘宰谈及义役之利时也指出,“义役之利,役可募人而已不专任其责,故役久而人不病。”[58]也许正由于“雇募长役”可某种程度上纠正义役弊端,故而到南宋后期有相当多的官员在试图重兴义役时,不约而同地引导义役团体雇募代役人。如端平(1234-1237)年间的知华亭县杨瑾,“停差保长,募民为‘直乡’(原注:凡里正[59]之事属焉),重置义役田以充役事”;[60]饶州德兴县在端平之后亦“按民产高下,各使出谷,名日义庄,募人充户长,……革一差之弊,募乐充之人”。[61]由此,义役组织仿佛成为国家职役政策渗透至乡役过程中的过滤器,乡役的轮差之法通过部分义役组织,转而为雇,一来使南宋朝廷对基层实施的社会控制产生了微妙的适应性变化,使南宋乡役层面增加了雇募的因素,二来也使私雇代役行为在义役组织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即使是一些仍然坚持由乡户亲自轮充应役的地区,代役雇直也被视作集资襄助应役户役费的参照,如理宗初(1225-1228)婺州义役的安排即是“约雇役费用之需而均率”[62]田产。总的来说,在南宋,无论是义役组织集体出资雇佣,还是参照雇役之值仍由乡户轮充,私雇代役现象都或多或少影响着义役的实现模式。
(三)私雇代役现象成为官府制定职役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
南宋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亲民官,无论制度设计还是在处理基层政务时,都把私雇代役人的存在纳入他们的考虑范围。如南宋绍兴(1131-1163)年间朝廷要求把田产散处各县的富户的资产分县汇总,归入各县物力最高一乡与该乡的人户同排役次,这样,富户可能会同时被数县差派,很难一一亲身应役;坊郭人户如果有田产在乡村的,称“遥佃户”,也要与乡户一起轮差保正长之役,这些被轮差到的遥佃户恐亦无法亲自到乡村居住一、两年执役。但此规定行之三十余年,民间并无多大异议。乾道(1165-1174)年间,一度命坊郭户可免乡役,但不数年即遭反对,重新按旧法施行。[63]宁宗(1195-1225)时黄榦所言解释了类似政策之所以能长期实行下去的社会背景:“户长所管者,催科,亦何必皆本都之人哉!今之为保正副、户长者,皆非其亲身。逐都各有无赖恶少,习知乡闾之事,为之充身代名。”[64]既然都不是正身充役,自然可以不再考虑正身是否在本都、是否同时应两县之役了。此外,南宋官府在考虑排役的时候,亦较少考虑当役户的丁口数,往往只凭物力轮差,[65]这也是因为官府也注意到民间私雇代役的普遍,只要有高强物力,应役即非难事,轮差高强物力少丁户执役并不会引起多少反弹,才会有此惯例。
更有甚者,因私雇代役的普遍,民户一经被差即请人代役,以致有州县虚设一个所谓“传帖人”的职役名目,“每月雇钱多者至十余千,少不下数千。……不曾承传文帖,亦令僦雇而占破”,[66]借此生财。
当然,对于南宋私雇代役现象的普遍程度,亦不宜过分高估。从上述史料也可发现,有能力私雇代役人的,往往是乡村、坊郭富户。虽说充保正者必一乡之豪,但由于豪民避役并非只有请人代役一途,还有“吏以舞文,愚弄村民,富者多避免,而下户常见充役”[67]的现象存在,那些被富户与胥吏通同作弊逼迫入役的中下之家,既因为没钱贿赂官吏而被陷入役,很可能又会因为无钱雇人代役而难免破家失业之命运。这种现象在南宋也是屡见不鲜。
南宋私雇代役之余绪亦及元明。元代,私雇代役仍然是百姓减轻职役苦难的重要途径。[68]如延祐五年(1318)浙西廉访司言:“访闻腹里路分,坊里正等役,一乡一都之间有依验众户包银分数,共出银钞雇人代役,遂得安居”,[69]即是一例。
至明,不但私雇代役盛行,而且还出现了联通雇役者与被雇者的中介行业“包当人”。[70]不过明代时垄断化了的代役人与包当人又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于是又逐步出现把差役折银,化力差为银差,进而推动职役赋税化,以一条鞭法变差役为纳银之努力。[71]若从这一角度看,则雇人代役或可算是明清时期赋役银纳化、职役吏员化等等探索的先声,宋初起自民间的代役之法,就不单是数百年来民间应对差役苦难的良策,还是推动我国古代赋役和基层管理体系演变的一个制度背景与经验来源。
四、小结
宋代差役问题产生的背景,是唐中期以后逐渐增多的维持国家有效运转的新事务,未能纳入官府的职能范畴,以致一些本应由官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职役的形式令民户代为提供。因此它既是特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入宋后又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情态产生矛盾。
私雇代役现象的出现与发展,说明在国家控制以外,地方社会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朝廷职役制度的效能与走向。
首先,它使朝廷制度的内容与实际运行出现某种差距。在北宋前期,这种差距意味着主户在差役政策下,仍略能享有雇役的选择,这疏解了由差役问题产生的社会张力。在北宋中期以后,朝廷役制迁延不定,这种差距则意味着宋代社会能借助私雇代役多少平滑掉制度屡变对基层与地方官府的扰动与冲击。
第二,私雇代役使民户通过付出相对稳定的雇直,避免亲身应役时费用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经营本业的时间与投资收益的稳定预期,促进了他们对本业的投入。此外,代役人通过提供代役服务使自己的劳动力产权获得收益,官府则因缘获得较专业的工作人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因此私雇代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府在职能转变上的滞后与缺失,推动了宋代社会财富的积累。
第三,私雇代役作为起于民间的非正式规则,在熙丰时期为雇役法的构想提供了前期经验。在号称恢复差役的元祐年间与南宋时期,尤其在差役制度保持得较为彻底的乡役层级,私雇代役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不断发荣滋长,其背后实获部分州县的承认,而朝廷出于财政、军需与地方稳定的考虑,也被迫日益放任它们的存在。这反映了国家政府与地方社会对话与博弈的过程,也折射出制度内容与社会经济变迁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机制。
[1] 关于宋代职役的研究很多,较早的研究可参见刁培俊:《20世纪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学界注重引入新的研究视角以揭示两宋役法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田晓忠:《论宋代乡村组织演变与国家乡村社会控制的关系》,《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等,但关于私雇代役现象,却似乎始终是前辈学者在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个环节。
[2] 孙应时:《宝祐琴川志》卷12《义役记》,《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67页。
[3] 见李春润:《杂职和两税法后的代役纳课》,《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宋代职役的名目,虽然一些源流可上溯至汉晋,但相当部分职役名称实际上形成于唐末、五代,且性质多为藩镇属员,而非轮差之职役。两税法虽在唐后期已颁布,但尚未完善,由此增加的职役负担也远未达到宋时水平。参见聂崇岐:《宋役法述》,初发表于《燕京学报》1947年第33期,后收入氏著《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页;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89页;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宋代州县的职役和胥吏的发展》,载氏著:《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版,第575、657页;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载氏著:《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39页;金毓黻:《唐代两税与宋代二税》,《中国学报》第一卷第1期,1943年;郑学檬:《五代两税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梁太济:《宋代两税及其与唐代两税的异同》,载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19页;李志贤:《“宋承五代之弊,两税遂呈变态”——论宋代赋役变革与两税法精神的传承》,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4] 然而烽丁属兵役还是职役尚不能确定,且受雇者并未改变其佃农或自耕农的身份,与宋时的职业代役人差别尚大。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6页;徐秀玲:《唐前期西州雇人代役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1页。
[6] 宋代关于民户争产兴狱之记载甚多,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不少,可参见高楠:《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本顺:《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程民生:《论宋代私有财产权》,《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等论著。
[7] 公共产品在经济学中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参见王正明主编:《微观经济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197页)。我国古代,并没有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概念,因此宋人对朝廷与官府在国防、产权登记与仲裁、社会秩序、学校等方面的付出,自然也只是从“治民”、“教化”等角度理解,但这些政府行为客观上起到提高全社会的生活与安全水平的作用,且不能限定受益人,具备公共产品的显著特点,这并不以宋人的主观目的而改变。乡户被差提供的如捕贼、烟火桥道、军需品运输等服务时,他们既不能限定受益者又不能向享受服务的人群收费(也就是所谓的私人提供公共产品时无法阻止的“搭便车”问题),故亦属公共产品范畴。因此本文出于分析论证之需要,借用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名词来概括宋代职役所包含的在基层官府与乡村组织中服务的内容。
[8] 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二五,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69页。
[9]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1,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536页下,吕陶言。
[10] 唐中后期随着户税、地税在国家收入中的占比提高,色役与杂任才渐显繁重,但此时民户亦面临动荡时期的其它威胁,稍有物力之家多想法隐托避役,贫户则多倾向于选择逃亡藏匿。参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第336-337页;胡如雷:《两件敦煌出土的判牒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70、72-76页。
[11] 相关趋势可参见漆侠:《关于宋代雇工问题》,《知困集》,第162页;王棣:《北宋差役的变化和改革》,《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三月辛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330页
[13] 如司马光在元祐初回忆道:“从来诸州招募人投充长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乡户衙前,此自是旧法。”见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七-二八,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七日,第5033页
[14] 职役种类的划分,前人有不同标准,参见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中国通史》第7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9-625页;王棣:《宋代经济史稿》,长春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405页。
[15] 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一之四,庆历二年五月,第6755页。黄繁光亦曾提到弓手私雇人代役之事,只是没有把庆历年间的沿边弓手私雇代役的背景与元祐时期东南上户私雇的情况分而论之。参见氏著:《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40、43页。
[16] 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一之四,康定二年(1041)七月,第6755页。
[17] 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1,庆历元年二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3页。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丁卯,第2207页。
[19]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六二,天圣四年七月,第4386页。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章惇奏,第8823-8824页。
[21] 虽无直接证据表明熙宁雇役法之构思源于民间私雇代役之法,但从雇役法的顶层设计者曾布、章惇等人对私雇代役的熟悉程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戊子,第5472页;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23-8824页),以及熙丰变法早期任详定差役利害的钱公辅曾在明州试行雇募衙前等经历为看(脱脱等:《宋史》卷321《钱公辅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21页),至少变法重臣对私雇代役有深刻的理解与赞赏,如果以此推测宋前期的私雇代役现象对熙宁雇役法有所启发,当可成立。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第5521页。
[2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24页。
[24]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二九-三一,元祐元年二月六日,第6171-6172页。
[2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8,元祐元年五月辛巳,第9187页。
[26]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七,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6180页。王岩叟奏章原文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第8895页,但个别文字有讹。
[27]王岩叟奏入时,章惇尚在两府,曾布尚为户部尚书,参见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第三册,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35-236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第8911页。
[28]苏轼与李常均曾论奏役法,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2,元祐元年七月丁巳,第9299-9300页;卷407元祐二年十一月壬戌,第9901页。
[29]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七,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详定役法所言,第6180页。
[30] 苏辙:《栾城集》卷39《三论差役事状》,载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3页。
[3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9,元祐元年十月庚寅,第9455-9456页。
[32] 杨时:《龟山集》卷18《书三•上提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5册,第287页上。
[33]苏辙:《栾城集》卷45《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载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787页-788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9909页。
[34] 属职役范畴的役人与自愿投充、有出职机会的胥吏虽然有时工作内容类似、名目也一样,但身份仍有区别。注意到此区别的学者不多,参见高树林:《宋朝赋役浅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役、吏的区别在熙宁雇役法实行后渐趋模糊,由此出现了役人吏员化趋势,对此笔者将另文再述。
[35] 南宋时陈傅良历数桂阳厢禁军的职责,“通厢禁军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各九十六人,……又有押部纲运、赍擎文书之差拨……”(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19《桂阳军乞画一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主管公使库、酒库、设厨、茶酒帐设司,并差将校”(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等,所言尽是北宋前期衙前、承符、白直之责,说明熙丰时期军人的代应州县役之举,在熙丰之后,已渐成军人的份内之事。
[36] 很多地区的耆长、户长时而轮差,时而雇募,如福州地区,“熙宁二年,募耆长、壮丁。四年,仍旧于本等人户轮充。……七年,……本州总括诸县耆长……壮丁……乡书手……,等第给雇钱。寻罢募壮丁”(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4《州县役人》,载《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页);台州地区也有类似情况(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19页)。还有一些地区,乡役被视为轻役而仍轮充之旧,如熙宁四年七月六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言:“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三六,第6225页)。
[37]与免役法几乎同时推行的保甲法,差派产生保甲头目如甲头、保长、保正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第5297-5298页),到熙宁七年十月辛巳,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7,熙宁七年十月辛巳,第6277-6278页),为保甲混入乡役系统之始。此后,朝廷屡经尝试拆分保甲与乡役系统均告失败。
[38] 绍圣二年,朝廷确定以保正长等兼代耆、户长、壮丁之法,保甲头目名称正式取代旧有乡役名称,成为新的乡役承担体系。本文将这一保甲混入乡役后的新的乡役体系称为“保甲乡役”,以示区分。见脱脱等:《宋史》卷178《役法下》,第4329页。
[3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壬辰,第5769页。
[40] 事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9,元丰八年八月癸酉,第8582页。朝廷大规模修改熙丰雇役法始于元祐元年二月,故元丰八年八月时,各职役仍是以官雇为主,但保正、保长因属保、甲系统,乃由差派产生而不由官雇,所以此处“代名”保长,当是私雇代名。
[4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5,元丰八年四月庚寅,第8495页。
[42] 《宋史》卷178,役法下,4329-4330,第4333页;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30,差役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1册,第608页。
[43] 至迟到宣和二年,已经出现保正长等保甲乡役人被责成管理乡村、供应州县等现象,见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1,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9页。
[44] 顾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6,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131页。
[45] 史料中关于南宋朝廷的财政危机及中央、地方间争夺财源的记载不少,可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3、150-154、173-175页;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46] 在保正长兼代耆户壮的初期,保正长仍保留部分雇直,直至南宋时乡役雇直才被彻底挪用,见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八一,绍兴五年正月十八日,第6197页,亦可参见黄繁光:《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表十四”,第251-255页。
[47]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八二,绍兴五年十一月八日,第6197页。
[48]所谓“良民惮役,争讼嚣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7,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4页),南宋史料中相关内容多不胜数。胡舜陟说,“臣出守五郡,每视讼牒之中,理诉差役十常七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有二月丙午,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34页),可见差役导致的诉讼占官府日常理讼的比例颇高。
[49]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八一-八二,绍兴五年三月十日,第6197页;食货六五之八四,绍兴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条,第6198页;六六之二一,淳熙六年十月十三日,第6218页。
[50]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八一-八二,绍兴五年三月十日, 第6197页;食货六五之八六-八七,绍兴十九年八月十二日,6199-6200页;食货六五之九八-九九,乾道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第6205-6206页;食货六六之二六,绍熙元年十月十一日,第6220页。
[5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0,绍兴十有九年九月壬寅,第3030页。
[52]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二六,绍熙元年十月十一日,第6220页。
[53] 关于义役的缘起、推行范围与对义役的评价等,可参见梁庚尧的《南宋农村的均赋与均役》(载氏著《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57页)、王德毅的《南宋义役考》(载氏著《宋史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53页)、黄繁光的《南宋义役的综合研究》(载林徐典:《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5页)、葛金芳的《从南宋义役看江南乡村治理秩序之重建》(载氏著:《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等论著。
[54] 程洵:《尊德性斋集》卷3《代作上殿札子三》,《知不足斋丛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集,第15页a至第16页b。
[55] 梁庚尧说:“南宋史料中,程洵所说的第一种方式较为少见,而以第二种方式为多”(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270页),但并未说明其论证过程。
[56] 黄震:《黄氏日抄》卷79《公移•江西提举司•咸淳八年(1272)八月十一日交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第816页。
[57]黄震:《黄氏日抄》卷79《公移•江西提举司•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第816页。(又见黄震:《黄氏日钞》卷86《台州黄岩县太平乡义役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第906-908页)。
[58] 刘宰:《漫塘文集》卷23《二十三都义庄记》,民国《嘉业堂丛书》本,第08册,第13页a。按其文后自注,此文作于绍定六年(1233)。
[59] “里正”这一职役名称,已经于仁宗至和二年时取消,但民间仍多以此名指代户长及后来的保正、保长等役。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夏四月辛亥,第4330页。
[60] 顾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6,第131页。
[61] 按刘克庄的记述,德兴县在淳熙(1174年-1189年)年间曾兴义役,一甲子之后,知县卓德庆重新整顿之,则此时应为端平(1234年—1236年)年间或更晚。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6《德兴义田》,《四部丛刊》初编第24册,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5页a。
[62] 王懋德:《万历金华府志》卷九9《宝庆义役法》,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68页。
[63]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六之二一,淳熙六年十月十三日,第6218页。
[64]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3《代抚州陈守》,《宋集珍本丛刊》第67册,第770页上。
[65]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〇〇,乾道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6206页。
[66]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九六,乾道元年八月五日,第6204页。
[67]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九六,乾道三年三月十八日,第6204页。
[68] 元代民户大抵沿用差役,兼以诸色户计之法(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19、684-686、704-706页),于是同样也出现职役使人破家鬻子之况,参见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6页。以往研究提及元代百姓避役时多举贿赂、投充等法(参见郑天挺:《元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及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第106页),较少说到雇人代役之事。陈高华曾在《元史研究论稿》中引《元典章》认为元代法律许雇人代役,只是民间私雇代役现象不多,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2页)。
[69] 顾清等:《正德松江府志》卷6,第137页。元代一本针对吏员的启蒙手册《吏学指南》中,把一个本来通指雇佣的词赋予了特定的含义:“顾倩,谓以物顾人代役也”;同时对官府雇役的情况另以“雇募”一词概括(徐元瑞撰,杨讷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说明对于元人来说,以物为酬私雇代役现象颇多,以致官场用语有以特指;而从元人对官雇、私雇役人的清晰区分来看,元代的官雇代役与私雇代役两种现象都有。
[70]明初的职役弊病又再次严重,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6、475页;张伟保:《均徭法与里甲岁办:明代江西役法改革的初步实践》,载张伟保等:《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明中期以前尝试过的各种赋役改革的执行层面,不乏私雇代役人的身影。赵毅、丁亮两位曾列出浙江地区19种力差的承当方式,其中只有3种为亲身应役,其余均为私雇代役,可见私雇代役现象之普遍。见赵毅、丁亮:《从银、力差的变迁看明代均徭法的演化路径——以浙江地区为例》,“表5”,《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4期。关于北方代役现象,亦见牛亚贵:《关于明中叶徭役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8期。
[71] 参见刘道胜:《明清时期徽州的都保与保甲——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二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赵毅、丁亮:《从银、力差的变迁看明代均徭法的演化路径——以浙江地区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4期;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尤见第17-19页。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com
编辑:潘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