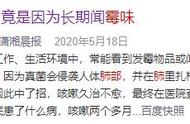郭沫若。资料图
《郭沫若年谱长编》(林甘泉、蔡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录有不少谱主未公开发表的诗词,多为应景之作,但有少数篇章别有寄托,其中尤以和龚自珍《己亥杂诗》三首值得品味。和诗作于1970年1月9日,正当《李白与杜甫》的写作行将完成之时。
龚自珍原作系“舟中读陶潜”三首(在全部315首中列于第129-131),《年谱长编》引用时并未按原作顺序,可能是以唱和先后排列。因未见原稿,无从断定。以下逐一试作解读。
一、一赋闲情韵致高
龚原作: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
郭唱和:
先生毕竟是诗豪,一赋闲情韵致高。
夸父女娃同拜倒,征知满腹有牢*。
龚自珍原作脍炙人口,“读陶三首”中最负盛名。郭沫若最初论陶潜,应数作于1943年的《题画记》,“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但同时批评陶潜“邻于自利自私”。直接认同“陶潜酷似卧龙豪”则是1964年春为南阳“诸葛草庐”的题词:
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令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咏,亦不逊于陶令也。
以陶渊明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自然是对武侯文才的竭力推崇,也是对陶令武略的极度夸张。
郭沫若于“二分平淡”中拈出陶潜的《闲情赋》,叹为“韵致高”,真是独出心裁。古往今来的论家和读者,恐无人视此赋为陶诗平淡风格之标本。故斯时斯地钟情此赋,当别有寄托。笔者揣测,大概是这样一段美文让郭沫若击节叹赏: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请比照郭沫若作于1948年辞别于立群的《此身篇》吧:
此身非我身,乃是君所有。慷慨付人民,谢君许我走。赠我怀中镜,镜中有写真。一见君颜开,令我忘苦辛。赠我琉璃梳,每日必梳头。仿佛君在旁,为我涂膏油。赠我象牙爪,能搔身上痒。仿佛君在旁,代搔不须想。赠我珐琅帽,是君所爱戴。仿佛君在旁,余温犹尚在。赠我皮手套,是君亲手购。仿佛君在旁,紧握我双手。赠我毛线衣,是君亲手织。仿佛君在旁,拥抱不相释。谢君珍重意,我亦知自爱。非为爱此身,为民爱器械。
郭沫若将此诗书赠当年创造社同人并书跋如下:“右系寄赠立群之作,成于北上舟中。见者谓颇别致,在余则仅抒写胸膈,所谓鄙直如偶语耳。”词藻诚然“鄙直如偶语”,但构思确乎其来有自。
无独有偶,这年夏季,在完成《李白与杜甫》之后,写了一组《读诗札记》,第二则《东风吹绽海棠开》考证敦煌曲子词《虞美人》抄本之错讹,解末句“拂下深深红蕊落,污奴衣”,即联想到当年赠于立群的诗句:
花朵插君胸,花粉染君衣。花朵虽凋谢,花粉永不离。
这是诗人1938年11月在南岳避日寇空袭时寄怀远在桂林的于立群组诗中的一首。诗人认为自己的诗与敦煌曲子词中的“污奴衣”有一脉相通之处,遂勾起对昔年情感经历的追怀。
1967年和1968年,郭沫若两个未及而立之年的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接连非正常离世,迭遭重创,于立群病倒。斯时斯事,年逾古稀的郭沫若格外珍重亲情。这可能是钟情于《闲情赋》的心理动因。
为印证“一分*”,标举世人熟知的《读山海经》(13首),其九“夸父诞宏志”,其十“精卫衔微木”,即为《山海经》中最为著名的夸父逐日与精卫填海。《年谱长编》在“夸父女娃同拜倒”句下却有“‘娃'殆为‘娲'之误”的质疑。这当然是毫无依据的。《山海经•北海经》有云:“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女娲补天当与此诗无涉。《读诗札记》第四则《形夭无千岁》推翻陈说,认为“刑天舞干戚”系宋人节外生枝的误改,而后人视为定论,“是一件很奇怪的公案”。要“形夭无千岁”方得与“猛志固常在”为对(“形”指肉体,“志”指精神)。郭沫若论证“陶渊明是尊仰上帝的人”,故不可能歌颂刑天。
应当强调的是,这首和作的新意不在单纯应和“二分梁父一分*”的卓见,而是对《闲情赋》“韵致高”的涵咏。这当然是“六经注我”,以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
二、圣贤任侠哪边多
龚原作: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郭唱和:
孟轲读倦读荆轲,三颂吟酸咏九歌。
记得先生尊鲁叟,圣贤任侠哪边多?
所谓“陶潜诗喜说荆轲”,其实纵览陶诗,吟咏荆轲者惟《咏荆轲》一篇。这是全部陶诗中最富“金刚怒目”色彩的作品。无怪乎朱熹论陶潜豪放,以此诗为“其露出本相者”。故龚作怀古叹今,寄情“江湖侠骨”。事功意识十分强烈的革命家郭沫若,对于仗义任侠,不乏心灵之交应。1940年代寓居陪都重庆,郭沫若以火山喷发之势,接连创作六部历史剧,就其总体而言,洋溢着战国时代的侠义精神。《棠棣之花》中的聂政本就是行侠的刺客,《虎符》中的信陵君、侯赢寄托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而直接以荆轲刺秦王为背景的《高渐离》,更是侠文化的产儿。1948年春,寓居香港的郭沫若观看苏联影片《江湖奇侠》,写下这样的观感:“我在这部《江湖奇侠》上不仅看见了传说上的大侠那斯列琴的形象化,我更看出了现实的革命伟人列宁和斯大林的象征。列宁和斯大林正是今天的乌兹别克人现实的那斯列琴了。”
但是引发郭沫若唱和意兴的,显然并非“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侠义。
“孟轲读倦读荆轲,三颂吟酸咏九歌”,这是对陶潜的描述,而非作者自况。读倦、吟酸当指陶潜勤于诵读儒家经典——《孟子》自不消说,《诗经》(由周、鲁、商三颂与十五国风、大小雅构成)亦为儒家经典,辛苦诵读之余,方及《史记》与屈*(认真说来《九章》才显“牢*”,以《九歌》指代只是为了协韵)。陶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之咏,故郭沫若“记得先生尊鲁叟”,而“圣贤任侠哪边多”的发问,多少是对这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微词。这样理解,笔者的依据是《李白与杜甫》(下节论及)和《读诗札记•形夭无千岁》。郭沫若解读《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批评“陶渊明倒是缺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并引韩愈《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认为“对于精卫的评价,韩愈见解高于陶渊明”。联系到写作《李白与杜甫》时的精神状态,郭沫若议论这些世有定评的历史人物,既有“慨世还是慨身”的同情理解(尤其在李白),也不乏对学界主流的刻意反拨(尤其在杜甫)。对陶潜的微词,乃月旦李杜之余波所及。

《郭沫若年谱长编》,林甘泉、蔡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三、五十何殊百步走
龚原作:
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
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
郭原作:
先生情性青莲温,应向田家说报恩。
五十何殊百步走,同归朝叩富尔门。(“尔”殆“儿”之误。)
此诗直接与《李白与杜甫》相关。陶潜《乞食》有云:“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故龚诗云“冥报因他一饭恩”。郭沫若则由此生发“先生情性青莲温,应向田家说报恩”的联想和比较。在《李白与杜甫•李杜在诗歌上的交往》一节中,郭沫若比较李杜的性格和诗歌,认为李白“更富于平民性”。所举作品,其中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一首:“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郭沫若称道李白“深知稼穑之艰难”,“因此,他在农家受到款待,他感谢得非常虔诚,谢了三次,不能动箸”。 这便是“应向田家说报恩”的由来。陶潜乞食,对象究系何人,诗中未有明示,但说“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应向”云云,看来郭沫若对陶潜的“冥报以相贻”似有微词。这种情感,在“五十何殊百步走,同归朝叩富尔门”两句中,表达无遗。由龚诗“颇觉少陵诗吻薄”连带到对杜甫的批评。杜甫乞食而诗,最出名的大概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这样的几句:“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末了,亦有“常拟报一饭”的感恩表示。照字面解释,同为乞食,批评杜甫“诗吻薄”乃“五十何殊百步走”,确乎令人费解。盖陶潜《乞食》何曾有“朝叩富尔门”之意蕴,而杜甫又何曾因此而对陶潜“诗吻薄”。如何解读,应从《李白与杜甫》中寻求答案。
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门阀观念》一节中,郭沫若认为杜甫“较之李白具有更加固执的门阀观念。这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得十分露骨”。列举诸多诗文予以解析后,郭沫若出人意外地提出“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对于陶渊明却有微词”。于是举出《遣兴五首》之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通过对杜甫与陶渊明在门阀观念上的比较,郭沫若认同“陶渊明自称为尧皇帝的后人是出于假冒,这也暴露了陶渊明的庸俗的一面”。但从杜甫没有承认与陶是同族,得出的结论却是:“这可从反面来证明杜甫的门阀观念是怎样顽强,并也同样证明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郭沫若的逻辑是:陶固然有庸俗的一面,但你杜甫更庸俗,有什么资格居然“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呢?
由此看来,在乞食报恩上,龚自珍称道“陶潜磊落性情温”,批评杜甫“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之“诗吻薄”。郭沫若则引发李白与陶渊明的比较,称道“青莲温”;更借题发挥,由“少陵诗吻薄”引发杜陶比较,讥刺“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这就不是“五十何殊百步走”,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了。
论到李杜的庸俗,郭沫若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也正是在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同时,郭沫若迭遭巨痛,乃有自省,在致郭世英生前好友的信中,坦承自己“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这三首和作对陶渊明的评论,多少可以让世人窥探这位当年曾以歌德期勉的诗人在其晚年的心境。
冯锡刚
责编 刘小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