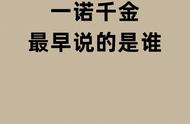▲陳少梅《東坡居士像》,紙本設色,127.5×33.3cm。私人藏品。
至于北宋朝野对于官方禁令的执行情况,更不是当局者可以控制的。据李纲《跋东坡小草》记载:“东坡居儋耳三年,与士子游,墨迹甚多。余至海南寻访,已皆为好事者取去,靡有存者……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祐学术,以坡为魁,恶之者欲置死地而后已。及崇、观以来,虽阳斥而阴予之,残章遗墨,流落人间,好事者至龛屋壁、彻版屏,力致而保藏之,唯恐居后。故虽鲸海万里,搜裒殆尽。”这说明,即使在蔡京当权的十多年间,民间对于各种东坡文献资料极为珍视、私藏之风相当盛行。以至于今日,东坡诗文、书画作品的保存仍算比较完整,应与北宋末年人们的努力有关。

▲[北宋]李公麟《東坡笠屐圖》,絹本設色,66×27cm。私人藏品。
南宋初年,“元祐之学”一度遭到秦桧的打击,但遭禁的原因是,当时主战的“二程”派理学家认为,宋、金之间是君父之仇、绝无讲和的余地,这将不利于高宗、秦桧议和政策的推行。也就是说,尽管高宗在位之时,尚无给东坡平反的可能,但打压“元祐之学”的重点已不是苏学而是“二程”理学,东坡的官方名誉已开始逐步恢复了。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南渡之初,苏符升为宣教郎,在由汪藻起草的制文中这样写道:“伟哉千载之英,繄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见,有孙而才。”字里行间,对于东坡是极为推扬的,党祸之遗似已荡然无存。绍兴二年(1132),高宗又在《褒赠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敕》中说:“党籍之禁行,而尔四人为罪首,则学者以其言为讳。自是以来,缙绅道丧,纲纪日隳,训至宣和之乱,言之可为痛心。”基本上全面否定了北宋的“元祐党人”之事。可以说,至此以东坡为首、旁及苏门诸子的身后声誉已得到了事实上的恢复。

在此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高宗亲书、御前“首席画家”马和之创作的《赤壁后游图》卷,画中描写的正是当年东坡夜游赤壁的场景。尽管此作装裱成书画合卷有可能是之后的事情,但也反映出,无论是高宗本人还是当时的朝野舆论,对于东坡已没有什么禁忌,只是由于某种考虑,没有正式表达罢了。故宫博物院的余辉先生甚至认为,这是“一次为苏轼平反的宫廷书画合作”。事实是,当时的宋金两国都涌现了许多东坡赤壁题材的绘画作品。这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提醒人们,双方都需要东坡来证明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特别是“苏学北渐”的金朝,抬高苏学的目的异常清晰。在这种状态下,南宋不得不考虑正式为东坡平反以为回应。对此,高宗应是早有明确的指示,孝宗于继位不久的乾道六年(1170)九月追谥东坡为“文忠”—正式为其平反,无非是一个官方程序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前二十五年高宗这位太上皇都是在世的,显然此事得到他的认可。由此可见,出于与金国政治对峙的需要,高宗在位期间不可能做任何有损于东坡的事情,高宗之后的整个南宋朝野更是将东坡奉为一代伟人,其中隐含着一个必然的现实逻辑。

南宋初年,文人和民间东坡写真遗像的保存和再创作也颇为乐观。继北宋末年民间对于东坡书札的高度珍视之后,南宋初年,东坡书法的市场卖价已达“百千两金”(张元干语),这自然影响到人们对于东坡画像的热衷。从南宋初年的文献来看,当年苏门弟子、友朋们私藏的李公麟版本的东坡写真像或为后人遗失,或为密藏,总之已极少显露。但李公麟所作的另一件东坡像却频繁地出现,画中描写的是东坡神态安闲、横杖立于大海枯木之上,有些明显的诗意化倾向。东坡身后,晁补之曾见过这件作品并作《东坡先生真赞》一文:“非儒,非仙,非世,出世间,不可以纶缴,亦不乘风云而上天,何居乎?犹心醉经目营海,既逍遥乎?涛瀬忽焉,横枝按膝而舒啸鸾凤之音,犹隐耳而人固已反乎?无在也。”之后见过此画的邹浩补充说,它是李公麟在东坡南迁儋耳之前创作的,即李公麟知道东坡行将再次南迁之事后,作此以为纪念。当时东坡远在广东惠州,李公麟则隐居于安徽桐城的龙眠山,二人终生再无相见,所以,东坡生前可能没有看到此画。这个画像一直流传到南宋,生活于高宗、孝宗之间的周紫芝再次见到它,作《李伯时画东坡乘槎图赞》一文:“东坡高目九州,视生死犹大梦,均溟渤于一沤。故能以巨海为家,以枯木为舟。风涛如山,而神色甚休。”这与晁补之的文字正好形成了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