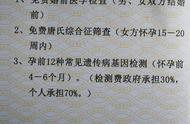▲ 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贝多芬传记电影《不朽真情》
电影中,贝多芬将身体贴在钢琴上
可越是苦难,他反而越具有创造力,他的音乐以最简单不过的和声、节奏型为始基,发展成令人骇然的庞大音乐世界,充斥着无穷力量。
03.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
对苦难的描绘终究只是为了衬托贝多芬所追求的欢乐。在苦难和欢乐两级之间,是贝多芬顽强的斗争,是他「坦白的」、「自由的」力,他的《第七交响乐》好像是「无目的的,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的欢乐」。
交响乐似乎成了贝多芬寻求力量的宣泄,探索思维之深的载体。在交响乐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空间,他像一位上帝,用精致的乐思构筑起不同的世界。
他一生只作有九首交响乐,但其中的每一首,不论编制的庞大还是内容的深刻,都是海顿、莫扎特不可想象的。而罗曼·罗兰所说的「力」,也毫不吝惜地被贝多芬挥洒在这些交响乐中。
贝多芬追求力量,过去音乐中的那种和谐、平整、诙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哲思,而同时期音乐的浮夸、轻薄、忧郁也被他所抛弃。至于他最厌恶的,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不真诚。
那些宫廷音乐、贵族聊以消遣的音乐,只有音符的躯壳,却不显露活生生的人,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因此,贝多芬在自己的音乐中,一开始所追求的便是斗争的、革命的「力」。
他早期的代表作《「英雄」交响乐》即是这样,它始于一个充满「动机」的乐段,不断发展,最终趋于完满。这样的手法存在于贝多芬后来的全部交响乐里。他创造了全新的作曲方式,把音乐纳入自我的探索与表达中。
一开始,《「英雄」交响乐》是贝多芬准备题献给拿破仑的,那是他所崇拜的力量和权力。但当拿破仑宣布称帝时,他愤怒地将刚刚写就的作品改成了「英雄」,这也成了他唯一自己命名的交响乐。
这个「英雄」是贝多芬心中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是不仅有力量,有权力,更是仁慈、博爱、有理想的英雄,他的一生都在努力使自己成为这样的「英雄」。在后来的日记中,他终于骄傲地说:「如果我打仗也像作曲这样在行,我会打败拿破仑」。
I. Allegro con brio (第一乐章 有活力的快板)Berliner Philharmoniker/Herbert von Karajan - Beethoven: Symphony No. 3 "Eroica"

▲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第一乐章
阿巴多指挥
在罗曼·罗兰看来,贝多芬在用一生完成了一次欢乐,给自己加冕。这一次欢乐是在他的《第九交响乐》写成首演之时,这部交响乐即是为人所熟知的「欢乐颂」。它的前三个乐章在一种不断地前进、拼搏之中进行,器乐提出的主题从晦暗、深沉的乐思开始,一直走向明亮、灿烂的终曲。
男高音与女高音的交替轮唱使得欢乐达到了极致,那是无数个痛苦的日夜、无数次被命运击垮所换来的大彻大悟,那是以勇气和爱谱写的乐句,是伤痕累累的英雄献给世界的博爱。

▲ 电影《不朽真情》
对贝多芬《第九交响乐》首演的还原
罗曼·罗兰用了很大篇幅描绘《第九交响乐》的首演盛况,写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指挥乐队,演出结束后「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是女歌手搀扶他转过身,他才看到观众的喝彩,这「唯一的一次欢乐」被这样描述道:
「当贝多芬(再次)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
这一刻,「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
罗曼·罗兰在全书的结尾评价到: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
04.
颓废青年的导师
《贝多芬传》出版于1903年,中年的罗曼·罗兰感受到了另一种颓废。法国在一系列的「改朝换代」中日趋衰落,以往庞大的君主国以及拿破仑时代的蓬勃之气已损耗殆尽,巴黎的文化中心地位正在被纽约所取代。而在法国的周围却是敌人环伺,奥匈帝国与德意志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巴黎的青年们,包括罗曼·罗兰这样的中年人,在世纪相交之时逐渐丧失掉了斗志,浸淫于糜烂的生活中,满足于酒、诗歌、大麻所带来的幻想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罗曼·罗兰来到了贝多芬的故乡波恩。在这里,贝多芬再一次使罗曼·罗兰提起了斗志,「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都令罗曼·罗兰重新振作起来。
这是罗曼·罗兰萌生出写《贝多芬传》的念头,他在《序言》中说贝多芬「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更描述了后来他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起因。可以说,贝多芬是罗曼·罗兰一生的榜样和导师,是教他「如何生死」的指南者。

▲ 贝多芬遗像 素描
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了1932年,年轻的傅雷在人生的这一阶段陷入了迷茫。他常常接触的浪漫主义文学、音乐使得他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中寻到了一丝宁静,同时却让他陷入到一种忧郁、颓废的情绪中。他评价自己这时期的状态是:「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
这时,一本书闯入了他的世界,它就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很多年后,傅雷还想起当时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
「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于是,傅雷一读完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本书译成中文,推荐给更多迷惘、消沉,不知人生何去何从的青年们。
傅雷和罗曼·罗兰,一位是伟大的翻译家,一位是伟大的小说家,他们都受到那位德国的音乐巨人贝多芬的影响,走上了各自的路。在译完《贝多芬传》后,傅雷又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许多著作,终成翻译大师。
而罗曼·罗兰在写完《贝多芬传》后,一面继续写作,成为「用音乐写作」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另一面又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和平主义的斗士。
在他们背后,是一位支持着他们的贝多芬。那是力量的不竭源泉,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时常孕育着英雄主义的萌芽。
05.
「用痛苦换来欢乐」
苦难是艺术的永恒主题。罗曼·罗兰写作《名人传》,举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人,是为了提醒自己应以何种方式对抗苦难,超越苦难。
一战与二战时期,罗曼·罗兰都是和平主义的大使,他厌恶平庸,更厌恶用极端方式杜绝平庸。二十世纪的和平并不是和平,相反,只不过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中场休息罢了。
蔓延在欧洲的情绪,要么是达达主义的玩世不恭,要么是虚无主义的彻底绝望,还有就是《魔山》中的颓废主义。这些在罗曼·罗兰眼中都是亟需改变的。
他去贝多芬那里取经,希望用生机勃勃取代死气沉沉,希望用青年般的力去创造美,希望回到「田园」中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近乎于痴心妄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想法却是最美好的。
也许,罗曼·罗兰是对的,只有贝多芬有能力拯救20世纪的厌世与恐慌。他对苦难的感受之深,对自我、自由所体现的充盈的力,他欢乐的纯粹与高尚,这些也许才是青年人最好的榜样。
在*戮混淆了斗争的苦难年代,罗曼·罗兰将希望寄托于一种真正的自我的斗争和升华,一种具有德性、智性的博爱。
他在《贝多芬传》结尾重申了「用痛苦换来欢乐」的态度,并在后来以贝多芬为原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结尾表达了更深刻的思想,它像是贝多芬一生的寓言,在不满足于平凡、不颓废于逆境中负重前行,将最终提炼出的爱的种子播撒于未来:
,「……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体象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他们长时间的嘲弄他,笑他。随后,黑夜来了。他们厌倦了。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得那么远,再也听不见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
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
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