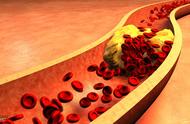恋情思量。
在我最爱岑辞的那一年,他喜欢上了我资助的残疾女孩。我看见他和朋友的聊天对话,温娅的人生太顺了,她完美得像一个假人,我觉得越来越没什么意思。那一刻我的人生轰然崩塌,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去了国外。五年后我回国媒体采访我问:听说岑家继承人岑辞即将订婚,您知道这个消息吗?我摇摇头,好像知道这么一个人但是不熟,祝他新婚快乐。
当晚看到新闻的岑辞连夜坐了飞机,从伦敦赶回了上海。我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古典舞的比赛,三年一次的国际大赛,最后的展示舞台位于上海。刚下飞机就有媒体围了上来,经纪人手忙脚乱地帮我应付着。一家小暴的记者突然把话筒伸了过来。他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岑家小姐,我们听说岑家继承人岑辞即将订婚,请问您知道这个消息吗?
岑辞,我偏头想了想,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可能是以前某个朋友,我露出职业性微笑,得体地回答,好像知道这么一个人但是不熟。不管怎样,祝他新婚快乐。其他几个记者却了一声,不熟吗?圈子里传言:你们以前是恋人呢?我总算想起来了。他曾经是我的未婚夫,确实不熟,我再一次强调,太久了,我已经不记得这么个人了,我没有夸大其词。
我和岑辞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小学的时候,他会因为别的男生拽了我的辫子把人家拉去操场痛打一顿,会为了赶上观看我的第一场舞蹈比赛,辗转几趟飞机连夜从海外飞回来,也会因为我说不喜欢他,不珍惜自己的身体,放弃了拳击,赛车这样危险的游戏,认识的所有人都说他爱惨了我。眼中除了我再也看不见别人。我以为我们会一辈子这样下去,顺理成章地订婚,结婚。
可我却在毕业前夕,偶然看到了他和好友的聊天记录。他说:我好像对温娅没有感觉了。朋友发来一个挑眉的表情,也该差不多了吧。你们认识二十多年了?就是恋爱,也谈了五年,换谁谁不腻。过了一会,温娅太完美了。完美得像是一个假人。她的人生一点波折都没有,不像胡央听不见,还能坚持考上大学。我在小杨树身上又重新看到了生命的热情。胡央是我资助的女学生,她家境差有先天性耳聋也不会说话,我给他买了助听器,带她看医生,资助她大学四年的学费,怕她遭受孤立。我还主动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
岑辞见到她的第一面,开玩笑的说:胡央,你真是长在沙漠里的一棵胡杨树。原来,原来,他心里面的天平早就已经发生了倾斜。看到聊天记录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人生都崩塌了。我花费十多年的青春,用力喜欢一个人却换来这样一个结局。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面,一个多星期都没出来,直到闺蜜找到我。

那时候,我已经不会说话了。她强硬地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情绪出现了极大的负面问题,必须进行外部干预,否则今后可能发展为更严重的心理疾病。但是这种治疗也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后来我出了国,也开始渐渐遗忘那些曾经与岑辞有关的情感。我们过去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那些回忆慢慢变成了一个一个符号,解码与我再也没有了任何意义。除非强迫性地进行回忆,我甚至不记得我以前还认识过岑辞这么一个人。
经纪人是从我在国外进修的时候,就一直跟在我身边的。她把那些八卦的记者赶开,拉着我上了车。问她一边开车,一边焦急地看着我。你不是吧?那些小报记者说的话。你别介意,我摇摇头。不会,我无所谓他们说什么的,是真的。经过长期的药物治疗后,我的情感波动好像被磨平了,我不会再轻易为任何一件事情欢喜、痛苦或悲伤,只是冷冷地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着他们的发展。经纪人叹了一口气,你能这样想,也行。就是不知道那些无聊的报纸会怎么写?
果然,第二天,井浩温亚从此不熟,井浩就上了热搜词条。评论里大部分都说传媒集团的独生女温娅嘴硬,口是心非,怎么可能连青梅竹马的未婚夫都不记得,肯定是被甩了。还要挽回一点自尊了。前男友要结婚还是会难过的吧?我无所谓的看着这些评论,偶然看到一句听说岑辞昨夜从伦敦搭私人飞机回来了,挤在角落里的一句话没什么人回复。
我点进去里面贴了一张照片,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人匆匆的从停机坪前向外走去,他就是岑辞。他们告诉我我曾经为了这个人生生退掉一层皮,差点连自己的命都丢了。我看着自己的胳膊那里遍布着深深浅浅,一道又一道的伤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也会有感情,这样充沛的时候我打了个呵欠,放下手机准备去卧室大床上躺一会,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才早上六点多,我厌烦的拉开门。
一个男人站在外面,身高体长看起来有些疲惫,加上黑色长风衣是照片里的那个男人。陈禽我张了张嘴犹豫的说:陈先生身子却没有动独身女性,不能随意让陌生男子进家门,这种道理我还是懂的。陈禽紧紧盯着我,眉头却皱了起来。陈禽我找了你五年,他一字一顿声音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沙哑的厉害,只是这一句就说不下去了。

我哦了一声,点点头那是有什么急事吗?没什么急事为什么要一直找我?他嘴角扯开像是听到了什么奇怪的话。五年前我们就要结婚了。结果你突然不告而别凭空消失,连一句话都没留下。岑辞你现在问我找你有什么事,你不觉得很搞笑吗?他的语气隐隐含着一些愤怒仿佛不可置信。
我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可我觉得明明这个叫岑辞的人更加搞笑,我们很熟吗?五年前我去了英国进修舞蹈,我的人生规划除了亲密的家人之外我不觉得应该向其他人交代。现在他气势汹汹的跑过来质问我为什么离开?凭什么?我凭什么得告诉他?当然这些话我并没有说出口。
自从确认情感认知障碍后心理医生就会提醒我在社交场面上偶尔要注意一下分寸和礼貌,也许我自己觉得这些话说出口后没有什么,但对面敏感的普通人有可能,就会对我产生奇怪或者不好的印象,比如冷漠、突兀、不近人情。想到这些,我定了定神,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按照礼仪教科书上的句子,一板一眼。当年添麻烦了。所以,现在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这些话我自认为回答得滴水不漏,没有任何问题。
可岑辞却好像完全无法接受。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咬着牙看着我。问,他低吼出声,你能不能不要再装了,不要再装成这样一副跟我完全不熟,冷淡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岑辞一脸烦躁,可我觉得奇怪,我讨厌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讨厌揣度别人的心理状态。刚刚好这个时候,卧室里的电话响了,我像是有了救星,连忙进去接了起来。
是孟凡,他是我这次比赛的双人舞搭档,我在伦敦时候的舞蹈老师,一位站在舞蹈界顶端的大师,也是孟凡的叔叔,他曾经对我们两个评价过。论天赋,还是温娅要稍稍好一些的。但是温娅,你缺了一点什么,知道吗?只有技巧。没有感情。
孟凡因为家里有事,没有和我坐一趟飞机回国,刚刚才落地上海。喂,我已经到国内了。孟凡的声音一向特别有朝气,他大大咧咧地在电话那端朝我喊: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你的生日。STRAWBERRY JAM,我说你好厉害,有给我准备生日礼物吗?有的呀,惊喜,因为对外界的敏感度太低,所以我会格外重视礼仪。像生日,纪念日这种事情,我会提前在手机的备忘录里面,记下来,省得外人怪我疏忽。

听到电话里孟凡开心地反应,我觉得这次我应该没有说错话,挂掉电话后,我才想起房门口还站着一个人,没什么事情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委婉地送客了。
正当我斟酌怎么开口的时候,岑辞自己先说话了,温娅,你以前自己说过,你记性不好,除了家人和我,不会再刻意记住别人的生日。我果然是记性不好,以前竟然还会说出这种话。所以他炖了,你真的再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了吗?我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句,怎么都不会得罪人的话。对了,祝你订婚快乐。岑辞听到这句话后,一句都没再说脸色甚至变白了一些,整个人冷冷的转身掉头离开。我希望他不要再来了,毕竟一个好的前任应该和死了一样,我但愿他有这种觉悟,做一个死人。
晚上,我按照约好的时间去了孟凡给我的地址。人间小众酒吧。他从小在伦敦长大,在国内几乎没有朋友,于是这个生日只有我一个人陪他见到我。孟凡猛地窜起来向我招手温亚。他是典型的舞蹈生,身量很高,在人群中特别显眼,我露出微笑,生日快乐啊。
我亲爱的搭档说着,我从包里拿出礼物递过去一只腕表。前几天在时尚网站上偶然看到,顺便买了下来。孟凡倒是对这个礼物特别喜欢,他左看看右看看,迫不及待地戴到自己手上去,然后兴冲冲地何我展示。你眼光真的很棒,我点点头,没怎么说话。我们聊了一会孟凡突然抬起头观察我的表情。你今天是不是不高?
其实对自己内部的情绪我有时候也会反应迟钝,但起码有一点我知道,今天早上我没睡好,六点钟那个叫岑辞的前未婚夫就过来登门拜访。岑辞不足的一天,搞得我整个人都精神疲惫,大概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点倦怠的情绪。想到岑辞,我随手又点开了微博,发现他从我这里离开后,下午就通过岑氏集团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声明,宣称本人并未订婚,媒体拍照中那个一起吃饭的女孩,其实是自己三叔的未婚妻。不得不说岑辞的梦女还不少。
声明发出后,很多人就在下面评论,我就说他不可能随便订婚,那是个聋哑人拜托。岑大少怎么会看上她?三叔嘿嘿,我就放心了。
岑辞的三叔,我有一点印象,以前和岑家商量订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那时候他还在岑家的集团里担任高管,四十多岁的人离过三次婚,肥头大耳,早年秃顶。总之完美符合众人心目中油腻富商的形象。没想到,他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又要结婚,对方还这么年轻,我点开评论区里的照片。陈,岑辞和女孩面对面坐在一家西餐厅,女孩微笑着小腹已经隆起。我看着她的脸过去的记忆渐渐浮现,是她我资助过的残疾少女。那时候跟着父母的慈善项目到大山去做调研。在一个学校住了一天临走的时候她跟了上来,问我们:我不想一辈子都困在这里面,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出去?她说:她一定会好好读书做出一番事业,我那时候觉得她好勇敢。没想到单纯的其实是我原来口中的事业就是嫁给岑家那个除了继承股份和每年分红外再没有任何能力的三叔。知如此,我想还不如换一个人资助。孟凡看我盯着手机怔征出神,低头问道: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复赛失利怎么办?我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上次在英国举行的世界古典舞第二轮进入复赛的本身都是领域内颇有建树的青年舞者。我和孟凡合作进入了决赛,但是排名只有第三评委给的建议和孟凡叔叔一样,女舞者动作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