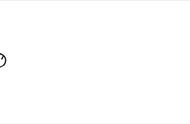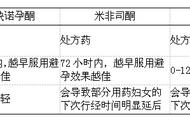一条运水的驴,一个目不识丁的铜匠,一个“扎根农村”的英语教师,这三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人和动物,用同一个名字,“驴得水”。这部电影以这头驴的名字命名,而这个尴尬的身份,正是引起整个故事的诱因。

《驴得水》讲述了一群“品行有污点”却怀揣教育梦想的教师,在偏远的乡村开办了一所小学。虽然待遇凄惨,生活艰苦,但是老师们却活的其乐融融,整天嘻嘻哈哈打成一片,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色彩。然而这种快乐平静却被特派员的突击检查打破。
原来因为学校的开支有限,需要一头名为“得水”的驴下山打水。于是老师们不得不多谎报了一名教师名额,并给这名教师取名“吕得水”,换来一份薪水贴补。为了防止事情败露,他们临时找了来修钟的铜匠冒充这个英语老师,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可以蒙混过关时,麻烦才刚刚开始……
话剧爱好者大多都知道《驴得水》,这部黑色幽默话剧在2012年上演后口碑上佳,被称为“零差评”话剧。和开心麻花品牌的话剧不同,《驴得水》是一部埋设了大量隐喻,以闹剧直指人性的有思想深度的喜剧。

我想可能是开心麻花想要改变自己的定位和路线吧。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讨论的内容,我关注的是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和他们第一部电影一样,尝试将话剧搬上银幕。
《驴得水》的编剧周申曾提到,他和另一编剧刘露最初完成的是电影大纲。而用他的话说,这部戏更适合电影,因为“当时的故事里会出现很多孩子和一头驴,这在话剧舞台上是很难以写实风格表现的”。但因为出现了有人盗用部分剧本拍摄同名微电影的情况,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并改动了写作大纲,用更快上演的话剧形式来演出这部戏。
似乎是阴错阳差,《驴得水》从电影变成了话剧,但事实似乎证明了这是个明智的选择。这部戏也基本实现了编剧设定的,从头笑到尾,但却笑着流泪的预想。
听说《驴得水》要翻拍成电影时,我很震惊,更何况是开心麻花公司出品的电影。虽然我对开心麻花的喜剧并无任何歧视——并且认为他们的话剧在走世俗喜剧道路上已经做到颇具技术的地步——但他们的作品一直走得是纯搞笑的路线,和许多话剧爱好者一样,我早已经习惯将开心麻花的戏视作“扩大版的小品”。而《驴得水》的深度,显然超过了麻花习惯的范畴。

一、镜头下的人——人物内心的立体感
《驴得水》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孙校长,教师张一曼、裴魁山、周铁男,校长女儿孙佳,以及被用来扮演“吕得水”的铁匠和铁匠媳妇。在话剧舞台上,这些人物作为整部闹剧的起因和受害者,推动这个故事前进。
在话剧舞台上,这些人是组成闹剧的因素。和其他闹剧一样,这些人物往往不会是绝对主角,你很难说《驴得水》的主角是谁。铁匠?张一曼?孙校长?都不能,而题目中的那头驴,根本没出过场。
在舞台上,闹剧的主角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和人的互动关系。我们会感受到一开头众人互相取笑逗乐造成的闹哄哄的气氛;特派员对大家施压时候的紧张压抑等,但人物不会特别突出,因为“闹”的氛围必须是多个人的互动才能形成。所以以舞台形式表现的闹剧,真正突出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
而电影则不同,电影的镜头下的人物成为画面的主体。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人物的脸部特写一经放大之后,心理细节的表达就凸显出来。
如校长给张一曼剪头发的时候,从张一曼眼中幻化出来的想象,是三民小学几个老师穿上新校服其乐融融的场景;而回到现实中,张一曼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已经被剪成瘌痢头。这种对比使张一曼被逼疯的过程变得更为具象化,耗时不长但是效果突出且合情合理,而这在舞台上是需要演员经过很多互动和个人表演才能逐步达到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从话剧走上电影,本身就是个很冒险的做法,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话剧并不适合于电影。开心麻花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改编了它的话剧《夏洛特烦恼》。为了配合电影的感觉,整部戏在删改之后,已经和话剧相差甚远,观感不及其同名话剧的一半。镁光灯下的舞台有它表演的特殊性,和镜头下的电影终究不同。
对于《驴得水》来说,早已获得认可的剧场表演是有它本身特殊基础的。话剧舞台看似写实主义的布景对应着整个虚构的情景设置,使得全剧从一开场就展现出闹剧特点。这种特点因为舞台的“亲临现场的感受”而变得尤为突出,由此烘托出整部戏的气氛。舞台对于喜剧而言,有着先天优势。
但是电影《驴得水》却多少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开始反观编剧所说的,这部戏更适合电影这样一个观点。
同样的状态也出现在周铁男身上,在舞台表演中,他被枪击但是没有击中之后,趴在特派员腿边的恳求的状态,让他显得特别猥琐,突出了这个人物转变后的软弱无能状态。但电影中,镜头特写了他死而复生的狂喜和再次被威胁的突然恐惧,直到他趴在特派员腿边时恳求中口水都不住的留下来。这让这个人的转变获得更多的同情,也让悲剧的感觉加剧。
这里还要提一句,里面不少角色还是由这部戏的话剧演员扮演的,从外形而言,这些演员算不上突出,但他们的表演功底使得这些人物性格显得更为到位,而且细节表演的精准也确实让人称道。
另一方面,镜头的推远拉近以及聚焦的效果,使得人和人的关系有了主次轻重的差别。比如在裴魁山在骂张一曼的时候,镜头就以多人群像,拍出张一曼的背影和裴魁山脸部状态的变化,而孙校长和周铁男以远景状态存在,但其中铁男试图阻止的一个举动做了一个远近镜头的切换,这使得这个镜头中的人物心理的挣扎鲜明了起来。
对比话剧,电影中的人物成了绝对主角,人性本身的变化,在外界压迫下的转变,成为了这部戏的突出的线路。
二、镜头下的故事——人性堕落的悲剧
看过《驴得水》这部戏的朋友,基本都能感受到这部戏浓重的黑色幽默社会讽刺的色彩,掩盖在闹剧之下的表达是非常聪明的做法。特派员所代表的政治强压,和这些教师在强压下为了维护“理想”用谎言掩盖谎言,并且打破底线扭曲人性的过程,充满着政治隐喻和人性的反思,是整个故事表达中最具深度的两个亮点。
在舞台上,有大量的细节可以突出整个故事,比如为了威胁孙佳和铁匠结婚,孙校长被绑架还被戴上了“打倒XXX”的牌子,而孙校长是被黑化后的裴魁山和周铁男亲自绑起来,为了讨好特派员,对比之前两人于校长的齐心协力显示出讽刺的悲凉。
但是电影里,这个细节被改成了特派员骗孙校长出去,并打昏他绑在了驴棚,而此时已经疯了的张一曼因为听从校长的话不敢从房间里出来,所以对他的呼救叫声置若罔闻,对比张一曼的疯言疯语和孙校长绝望的眼神,又加重了某种人物转变所带来悲剧性,而政治寓意色彩却削弱了。
类似的处理还出现在最后一幕中,所有老师虽然被记过,但可以留下来继续任教,于是孙校长和裴魁山、周铁男重归于好。这一幕在话剧表现中,三人甚至互相拿之前的过节嬉笑取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对比之前批斗场景,这一幕透着浓浓的让人心寒的氛围,即使没有最后张一曼的自*,这一幕的目的也已经达到,而离开三民小学前孙佳的一句话,“如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那只会越来越糟”,则让讽刺意义达到顶峰。
但电影里,嬉笑和解的镜头变得平和了不少,孙校长的妥协色彩被削弱了很多,而将整出戏的重头放在了张一曼自*的枪声中。张一曼的死这里也做了浪漫化的处理,包括这部戏的主题曲“我想要”,从一开始她和裴魁山的爱情萌生时演唱的那种动人的状态,到她自*后镜头扫过她做完的新校服,还有孙佳箱子里的彩色球落满了山坡,将整个悲剧色彩烘托到了最高潮(这里也可以看出这部戏的角色重心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张一曼)。这符合了这部戏的主线,人性悲剧的讨论来取代社会隐喻。电影的处理,让这部戏淡化了政治隐喻,而突出了人性堕落产生的悲剧,使后者成为主线。
此外,电影的剪辑有明显的详略倾向。比如其中的一个片段——大家意识到用驴顶替老师名额可能会暴露到孙校长的纠结,再到说服铁匠冒充老师,所有的过渡性对白都被删除,只保留主干情节。而很多原本在舞台上的蒙太奇效果做出的画面则被删减,如从孙佳受到威胁到孙佳和铁匠的婚礼被剪掉,而孙校长被解救的过程也被省略。
相对的,人和人的感情部分由被扩充出来,比如张一曼在模拟下雪时裴魁山的眼神,铁匠在告别时对着张一曼唱的表达爱情的歌曲,拿到大笔奖金教师们在灯光中的舞蹈、铁男为了哄孙佳开心送的红色小球和最后孙佳箱子里掉落的彩球的对比。
在控制整个故事的节奏中,这部戏的剪辑可圈可点。电影的剪辑取舍让整个故事变得流畅明快,但是又没有削弱故事的主体矛盾,详略得当。让整部戏的观感反而有所提升。
当然,转变为电影语言之后,这部戏也不是没有“损失”之处。例如,因为突出人物,群体性的闹剧感被削弱了,整部戏似乎只有前半部分可以称之为喜剧,后半部分除了少数桥段制造了短暂的喜剧效果,整体陷入较为低沉压抑的气氛。另外,话剧所带来的人物群像的整体感,是闹剧的画面基础,而这个电影中往往因为镜头的限制而无法完全表达出来,比如铁匠和孙佳的婚礼那一场,在原来的话剧中,闹事的铁匠媳妇带来了全场的大混乱,一路追打的众人和四处逃跑的宾客,环绕着呆站着的美国慈善家,形成非常明显的动静对比画面,而这个显然是电影做不到的。
有朋友观影之后说,这部戏的故事表述,基本忠于原著,也少了惊喜。但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它重视原著。《驴得水》的剧本所讲述的故事本身,有完整精彩的精神内核,它用一个架空的故事,不但展现了当时当地的社会暗喻,又有穿越时间的人性直指。而如果大改特改,效果会怎样可能?那就不得而知了。虽然在话剧界颇受好评,但是绝大多数观众对这个故事并不熟悉。
如果能够用一个出色的表现形式,诚诚恳恳地将这个故事完整介绍给电影观众,本身已经是一件好事。更何况,这部戏的电影语言,不乏将这部戏的优势更为突出的精彩之处,更是让人欣慰。
可以说,《驴得水》算得上话剧转变为电影的成功之作。
现在的电影,缺的不是技术的突破、绚烂的画面,甚至不是演技的卓绝和镜头运用的高超,而是讲一个好故事的才华,和讲好一个故事的能力。
而这部戏也让我相信,真正的好故事有它自身的魅力,能跨越不同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