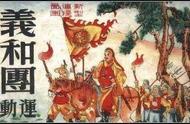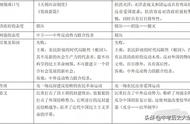其二:激赏军功以强兵。
为增强兵力,卫鞅在“农本”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十等爵军功制”,这一制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点。其一,“凡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新法将秦国的爵位分为了二十个等级,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出身,皆可凭军功享受相对应的爵禄。
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等同于取消秦国宗室所享有的世袭特权,公室贵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获取爵位和封邑了。
这一政策直接将卫鞅推向了老氏族的对立面,为他人生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军功爵”制度依然遵循了最原始的赏罚原则,却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阶级跨越的通路,老氏族的特权被打破。
想要成为秦国的新贵,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上阵*敌,凭借*敌数量的多少来获得高官厚禄。
在政策的激励下,秦国的有志青年皆愿意去从军,以敌军的人头为自己挣一份光明前途,秦军就此成为了一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其三,整顿地方以领政。
在大力推行前两项政策的同时,卫鞅又提出了“废分封,设郡县”的主张,即以郡县制度代替秦国实行了百年的分封制,形成了中央—郡—县—乡—里—村的层级制度。
为方便管理,新法还改革了现有的户籍制度令居民以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编户入伍入什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实行一户有罪十户连坐的惩罚措施。
严格的层级划分使中央的政令在地方上得到高效的实行,严苛的惩罚措施提高了犯罪成本,大大的降低了地方的犯罪率,二者互为表里,共同加强了中央集权。
强大的中央集权又使国家力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国力高度凝聚,国家自然不怒自威。
其四,移风易俗以正民。
为了纠正国民的歪风邪气,使国家不至于从内部溃烂。新法在社会风俗方面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比如禁止民间私斗,杜绝血腥的同态复仇法,避免国家战力的内部消耗。
又比如强制民间实行分家政策, 禁止已经成年的父子或兄弟居住在同一个大家庭内,以此来激发小家庭的独立自主意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国府的税收(秦法按户收税)。

四纲之下各有其法,在详细的层级划分与严苛的刑罚面前,秦国真正做到了举国同法。
朝野间官吏无贪,庶民无私,看似平稳的发展轨道背后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人民对于国府只有惧怕,没有爱戴。
刑*峻急,伤民之心如果说法律是维持国家运作的机器 那么民众的道德水平就是国家得以立世的脸面,要命的是,在商鞅变法的愚民政策之下,国家机器从国家脸面上狠狠碾了过去。
换句话说,秦人不愿犯法并不是因为犯罪可耻,而是害怕犯罪之后的惩罚。
变法后的秦法提倡“轻罪重罚”,并让邻里之间相互监视举报。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对人性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秦法在后世史书中以严苛著称,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商鞅经手的渭水大刑。
“(商鞅)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 比于丘山。——《新序.商君论》”

百姓们由此积怨于心,民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注定会有一场山洪般的爆发。
而在另一方面,秦国在六代雄主的领导下走向统一,国家的疆域在不断扩大,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作为保障,种种疏漏都表明,秦朝注定会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商鞅之法于秦国而言是治国理政的佳兵利器。
商君法的变田、赋税、农爵、军功、度量、官制等条例犹如一只匡扶朝纲的手,原本贫弱的秦国在它的帮助下成为了傲世中原的天下第一大国。
虽然最后商鞅被车裂,但只要秦法不死,战时的秦国就不会变形糜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