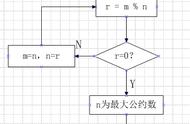作者:谢宗睿
这是今年大黑第四次出险,所幸人没事儿,责任也没啥可争议的。于是,短暂的惊惶过后,我点开微信通讯录,给“狂奔的蜗牛”打去了音频电话。
依然是秒接。听筒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又咋了,大哥?”“人没事儿吧?”“报警了吗?”“谁全责?”……伴随着一连串提问,老杜那张嵌着抬头纹和鱼尾纹的脸浮现在眼前,立马让我安下心来。
大黑是我的第一辆车。怎么认识老杜的,已记不清了。不过,自打五年前把大黑迎回家的那一天起,无论常规保养,还是意外事故,关于大黑的一切事情,我都托付给了老杜。很久之后,我才知道,4S店里分工其实很细,而老杜的职责既不是销售,也不是售后,更不是机修,只是保险定损员。
和能说会道的销售冠军比起来,定损员不太起眼。喜气洋洋把新车开出店门的车主,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大凡来找定损员的,除了个别车主还能勉力保持住一派“破财免灾”的乐天风度,其他无不垂头丧气、臊眉耷眼。说这是一份负能量满满的工作,应该算不上夸张。再加上在保险行业的“鄙视链”上,一线的定损员无疑处在中间靠下的位置,所以这个岗位通常留不住人。老杜是个例外,干这行整整十年了。
老杜个子瘦高,皮肤黝黑,皱纹很深,一头短发白了不少。上次大黑出险时,他刚做完核酸回到店里,随手把身份证放在桌上。我这才发现,老杜其实生于1990年,这真的让我有点儿吃惊。
这次事故让大黑伤得不轻,所有维修项目做完,花了近二十天。老杜一如既往地忙前忙后,又是和保险公司协调定损情况,又是催件,又是到车间查看维修进度,又是给我打电话说明情况,让我别着急,着实费了不少心。于是,接大黑回家那天,我特意赶在老杜下班之后才到4S店,取了钥匙便硬拽着他去了旁边的烧烤摊。
闷热的盛夏傍晚,几杯扎啤下肚,话就聊开了。老杜老家在河北的一个贫困县,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15岁初中一毕业,老杜就跟着亲戚外出闯荡,在县城炸过油条,在省城倒腾过旧家电,22岁那年来到北京,打的第一份工是修摩托。后来,老杜干上了保险定损员。“那时候,干这个没门槛,修过车的都能干。可我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交过不少‘学费’。”老杜说,“现在干这行的年轻人可就不简单了,刚才在店里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伙子是我徒弟,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今年毕业,现在在店里实习。书读得多,学东西就是快,比我当年强多了。”
“你就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打趣道。“怎么不怕呀,我可没敢躺平,我今年也大专毕业了。大哥,你看。”老杜猛喝一口,突然放下啤酒杯,掏出手机,熟练地输入一串网址后举到我眼前,“这是我的学信网在籍证明。现在想干我们这行,最低门槛是本科,我正琢磨着一鼓作气去考个成人本科。大哥你是知识分子,见多识广,到时候一定帮我参谋参谋。”老杜越说越兴奋,满面红光。
“初中起步,过了十几年,三十多了还要考本科的,你是我认识的头一个!”我由衷地夸了一句。没想到,老杜接下来的话更让我差点惊掉了下巴。“我媳妇儿更狠,她也是初中学历,后来一直自学。她这几年在一家公司当会计,一边打工,一边考注会。我的本科、她的注会,还指不定谁先读出来呢。我俩也想给我家那俩浑小子做做榜样。”
老杜有两个儿子,都在老家。“现在,我爹娘在老家啥都不用愁,唯一的任务就是带孙子。这些年,镇上的学校盖得和北京的一样气派,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好了,啥都不缺,这样我俩才能迈开大步只管往前奔呀。”老杜说着拿出手机,老老杜老两口、老杜小两口再加上俩小小杜,一家六口其乐融融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满满的幸福也顺着老杜深深的鱼尾纹流淌出来。
酒兴正浓的我恍惚想起一则“鸡汤”,大意是德国的一个下水道工人在修管道时常常吟诵席勒的诗歌,他说:“在漆黑的下水管道里,只有席勒的诗才会让我心里有光。”
那天聊得痛快,我俩都喝了不少。代驾把我送到家后,我便匆匆洗漱倒头睡下了。第二天清晨打开手机,两条微信留言映入我惺忪的睡眼。第一条是用手机拍下的一页书,上面用红笔画出了一句话:“舍之闻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另一条是语音。“大哥,昨天太感谢了。喝酒的时候,咱们聊到了保险行业的诚信问题。晚上我回到家读书,正好看到这一句,很受启发,和你分享。”“狂奔的蜗牛”对我说。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9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