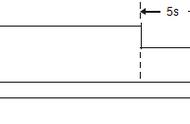不过,无可否认的是,正如蛮横的“命运”之轮推进着小说《活着》的叙事,汹涌的“历史”浪潮也推进着电影《活着》的叙事,原本平凡(也甘于平凡)的徐福贵,他的一生却由于奇异的历史风云而不断地丰富着。
他的人生遭遇里处处有大历史黑黝黝的投影,他多灾多难的岁月遭逢的是一个漫长时代的灾难,于是他“活着”的历程有了历史感,动荡的中国历史成了电影《活着》的叙事暗线,成了在艺术上成就徐福贵这个人物的神秘之手。
03“温暖”与“希望”:电影《活着》的叙事归宿
在电影《活着》中,叙事内蕴的自我矛盾没有尖锐到小说里那样的程度,原因很简单:徐福贵在影片结束时依然生活在理所当然的“有情世界”之中,虽然他亲生的儿女都不幸去世,可是他和老伴儿家珍、女婿二喜、外孙苦根,三世同堂其乐融融。
电影结束于一个“光明的尾巴”,死去的人们已成传说和追忆,甚至连惊心动魄的死因也可以成为心平气和的谈资。徐福贵再一次给小孩子讲起“鸡长大了就变成鹅”的“神话”,这个神话寄托着希望。
影片就在一片温暖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氛围中告终。似乎是风雨过后的彩虹,似乎是噩梦醒来的清晨,“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在此是不存在的,活着的人好好的活着。

观众也就感到了紧张之后的愉悦和感动,这从商业电影的角度来讲不但是中规中矩的,而且是堪为楷模的,余华曾期许的叙事内蕴似乎也凭藉声画的力量无形中实现了。
可是作为研究者,有必要继续追问:我们到底感动于什么?真的是感动于“活着”本身吗?其实很清楚,我们是感动于那温暖而充满希望的氛围,正是这样的氛围,才让活着成为可喜的。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大美,可是生生不息也掩藏不了生命的苦难和陨灭。

《活着》这个故事与生俱来的困境。这个困境说到底,在于创作这个故事的人过于匆忙、过于自信地取消了“‘活着’的根据”这个问题,他们有些莽撞地将这个问题归于伪问题之列。然而,指责前人的失误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笔者绝非自认为比当年的创作者们高明。
恰恰相反,正是有了他们的艰难探寻,才让我们今天得以在一步步的研究之后清楚地看到这个困境的存在与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