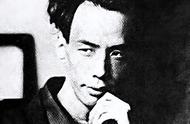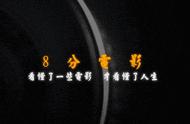2、妻子真砂的证词:
逃走的妻子真砂被人在尼姑庵中发现,在她口中,故事俨然变成了另一个版本:
当日,真砂被侮辱之后,心中满是惭愧和自责,但她救夫心切,跑去为丈夫松绑,却看到了丈夫冷漠的眼神,尽是鄙夷与憎恶 。真砂读懂了丈夫的眼神,羞愧令她备受煎,她祈求丈夫*了自己,可是武士仍然是一语不发,最后她悲痛万分误*了丈夫后晕厥了过去。
等到再度清醒时,本想随他而去,却奈何自己连自*的力气都没有。

3、死去的武士的证词(借由女巫之口):
因为前两位当事人说辞的矛盾,官府不得不另想办法,找来了女巫摆下祭坛,召唤武士的灵魂,诉说真相。本想着可以真相大白,却没想到他的说辞却让这个案件更加迷离。
武士回忆当天的情景:
强盗当着自己的面侮辱了妻子,之后更是百般唆使妻子跟他走,而真砂竟然被强盗打动,甚至不念旧情,要求强盗*了自己;武士大受打击,完全没想到妻子的无情,而一旁的强盗也被真砂的狠毒震惊,一把将其推倒在地。
强盗的举动让武士原谅了他,心里只剩下对真砂的愤恨,但真砂早已趁机逃走了。
强盗为武士松了绑之后也离开了,只剩下生无可恋的武士,用短刀自尽身亡。

竹林里的一桩命案,三位当事人口中竟然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而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镜头回到罗生门下三个避雨的人之中,借由他们的讨论,我们在樵夫的口中得知了第四种说辞:
4:樵夫的证词:
原来当日事发之时,除了三个当事人之外,还有一个一直隐于暗处的旁观者——樵夫。
躲在角落里的他,看到了强盗在实施完侮辱暴行之后,哀求真砂随自己走,并发誓会尽力养活真砂;真砂却跑去为武士解了绑,并要求两人决斗,谁赢了自己就跟谁。
武士根本不愿动手,甚至对真砂恶言相向:称其被侮辱之后就该自*;武士的说法刺激了强盗,他也放弃了转身欲走。同时被两个男人抛弃的真砂彻底怒了,对着两人破口大骂,挑拨着两人开始决斗。
随后,他们都拿起来武器,却完全没有强者风范,而是颇为可笑的、毫无章法的胡乱扭打在一起。最后武士被强盗用长剑刺死,真砂慌乱逃走,强盗也跌跌撞撞离去······

至此,竹林里的这一宗谋*案在各个角色的证词之中构建起来,每个人的证词都具说服力,但又相互矛盾,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一桩命案,四种说辞,谎言的表象之下,全部真相隐于竹林之中,如同其中斑驳的光影,每个故事仿佛泛着光晕,让人看不清摸不透,似乎处处是烈日的照射,又似乎处处都是令人无法看清的阴影。
二:谎言的幕后:失去重量的真相背后,直指人性的虚伪与自利史铁生曾说:
历史在发生时未被发现,在被发现时已被*。
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真实可以被叙述完美还原,因为不管怎样叙述,它终究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产物!
《罗生门》中的这场命案,真相只有一个,三位当事人却各执一词,背后的真相令人捉摸不透。
而影片中的樵夫作为目睹案件过程且无利益关系的第三者,按说他的证词应该是最客观的,但是最后,还是被同在避雨的仆役揭露:
他为了个人利益,怕受牵连,也在公堂之上说了谎,事实上,他偷偷拿走了命案现场的一把价值不菲的短刀。
至此,人性彻底崩塌,故事中的四人都说了谎,所谓的真相已然失真。
直到最后,武士是如何死的,影片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这已不再重要,作品的重点不在探查事件的真相,而是展现谎言迷雾背后所掩盖的人性弱点。
当事三人明知*人是重罪为何争相承认?武士已经命丧黄泉,为何不为自己讨回公道而是说谎自*?矛盾的背后,是虚伪脆弱的人性。
1:自利心:
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论人性》中指出:
支配人的生活的是意志、情感(或激情)而非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
《罗生门》中人物谎言背后的指使者之一便是“自利心”,这场命案,每个人都被困在舆论与道德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编造出一套最有利于自己的说辞,以摆脱负面的情势与印象,趋利避害的本性展露无疑。
2:虚荣心
虚荣心,也可称之为“美誉感”,这是致使他们说谎的根源之一。
美国作家鲁思·本尼迪克最初奉美国政府之令,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编撰出版了小说《菊与刀》,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目。
在《菊与刀》“洗刷污名”这一节中,本尼迪克这样分析日本人:
“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
“清除自己美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德”
“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命”······
日本的耻感文化中没有个人忏悔的元素,长久以来整个民族对于荣誉的重视及渗透在生活中的武士道文化,使得他们过分依赖于他人的目光而非本人的意愿,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消除耻辱,维护自己的名誉,使自己能够得到道德上的拯救。
多襄丸,作为一个强盗,一直为人所轻视、愤恨、不齿,所以他宁愿背负*人的罪名,也要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为了“真爱”而公平决斗,敢做敢当的真汉子,树立勇猛威武、光明磊落的正面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