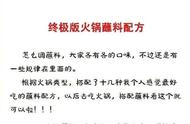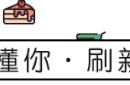作者:杨勇(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之作,《乡土中国》已经在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文学以及哲学等领域引发了诸多学术争论,但鲜有人从教育学或教育实践的角度对这本书进行理解和讨论。自2019年开始,《乡土中国》便被列入到全国高中语文统编教材的“整本书阅读”单元中。这首先意味着,《乡土中国》不再只是少数社会学专业师生的读物,而且还成为了全国高中生的必修课程,是高考考试内容的直接来源。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将《乡土中国》仅仅视为一本专业性的学术著作,而是要从更普遍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一个具有通识性质的教育文本。
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在走出大学课堂和学者的书桌后,《乡土中国》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与全国的青年群体发生实质的教育关联?这个问题同时摆在了诸多教育参与者的面前。自博士毕业以来,笔者一方面在高校任教,不断重温和研究《乡土中国》,另一方面与上海市、云南省的一些高级中学建立合作,参与《乡土中国》的课程设计,给广大高中师生群体讲解这一文本。在亲身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教育现象,值得分享和讨论。
《乡土中国》进入高中课本,对于现在的高中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飞速提升,如今的孩子大多出生并成长于城市之中。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云南,作为受教育主体的大多数学生日常所熟悉的生活是一种远离乡土的城市生活,他们的认知、经验与习惯几乎完全被城市生活所形塑。这导致的结果是,学生的生命经验与《乡土中国》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断裂或鸿沟,他们无法从自身生活出发,真切地理解费孝通用“乡土性”“差序格局”和“礼俗社会”来描述的生活状态。学生对文本没有经验层面的亲近感,无法与文本建立起生命关联,这便是教育最大的困难所在。另外,《乡土中国》一书的学术性也加剧了这一教学难题。此书本质上是一本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书籍,书中充斥着各种学术概念,对高中生而言,语言颇具抽象性和逻辑性。而高中生在语文课堂上接触得更多的是文学类的文本,这类文本更偏重引导学生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比如,统编教材中规定的另一本整本书阅读书目是《红楼梦》,它在风格和阅读体验上就更接近于传统的语文课本,因此更为学生所接受。相比较而言,《乡土中国》对于学生来说相当陌生,如果没有外在的督导,学生通常不会主动打开这本书,而是将其束之高阁。
突然闯入语文课堂的《乡土中国》同样也给广大高中语文老师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挑战。大部分老师像学生一样,之前并未真正接触过社科类的著作,他们对《乡土中国》同样陌生,不仅无法快速适应这本书的写作风格,也无法快速掌握书中的专业概念和知识。没有前期准备的教学自然很不理想。并且,老师们也在课堂实践中意识到,讲解《乡土中国》的教学方法需要适当更新。以往的语文教学强调的是情感传递和文化修养,但《乡土中国》的特点却是概念辨析和逻辑推演,语文课程标准和文本本身都同样要求老师做出改变,不能再以原来的标准和理念来开展教学和评价学生。就笔者的经验观察而言,无论是在上海还是云南,让高中老师乃至整个高中教育场域迅速适应《乡土中国》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形下,高校的相关研究者或教育机构需要适当介入,一起化解上述教育难题。
借着与滇沪两地高中进行合作的机会,笔者尝试以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身份来重新看待《乡土中国》。从教育的角度出发,首先需要考虑到,进入高中语文教材后,《乡土中国》面向的阅读主体是高中生群体而非大学本科生或专业研究人员。这便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到高中生群体所具有的特殊的心理状态。通常而言,一个处在14—18岁之间的个体生命,其心智尚未发展完善,我们不能一上来向其灌输过于概念化和抽象化的知识。教育的过程应当以学生个体的生命经验为基础,以教材和文本为中介,逐步将学生引导到更为普遍化的知识脉络和文化传统之中。因此,给高中生讲授《乡土中国》时,要适当消解文本本身的学术性和抽象性,减少对于专业概念的辨析,相对侧重和突出文本的经验性和文学性。《乡土中国》原本便是费孝通在《世纪评论》上发表的连载文章,其中充满了许多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例子和费孝通本人的生活经历。如果能适当地抓住这些案例,并结合学生当前的生命经验,那么能很好地将学生吸引到文本阅读中。比如,在讲述“乡土性”时可以引入有关上海话和上海弄堂文化的讨论,在讲述“差序格局”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他们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是否越来越平等化和“朋友化”,在讲述“礼俗社会”和“教化权力”时,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城市中的养老问题,等等。教育应该从学生个体与《乡土中国》的生命联结处进入,在经验中激活学生对于文本知识和概念的理解力。
除了学生个体的生命状态外,另一个需要费心的教育要素是课程设计。高中生虽然在心智和经验上有所欠缺,但是他们却拥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力图对于周遭世界和自我有一个普遍化的理解。而一个好的课程设计,不仅可以作为桥梁连接学生与书本,还可以充当一个文明中介,连接特殊个体与普遍世界。因此,在设计《乡土中国》的教学课程时,除了要从经验出发以抓住典型的生活案例之外,还有必要适当加入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内容,凸显文本本身的通识性。我们可以以此书为范例,向学生示范阅读社科类著作的方法,比如如何进行圈点勾画,如何书写批注。通过书写,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让他们能够以相对精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分析手中的阅读材料。在学生阅读和书写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会使用文本中的概念和知识,鼓励他们越出文本本身,有逻辑、有深度地思考自己周遭的社会生活。从这几个维度来设计《乡土中国》的教学课程,我们便能在为学生铺垫经验基础、找回教育本身的“乡土性”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城市学生自身的优势,打开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激活文本的多重意涵。费孝通写作此书时的视野是开阔的,他虽然着重讨论“乡土文明”,但全书的论述始终在乡村生活与都市生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双重比较中逐步展开。而城市里的孩子其实对这些文明变迁有着更开放、更丰富的体验。如果课程设计得当,青年群体与《乡土中国》之间的鸿沟可以被填平。当然,执行课程设计、开展实际教育的高中老师同样关键。专业研究人员和教育机构可以协助开发教学课程,但是最终主导教育走向的还是教师。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最后,回到社会学的专业研究本身。《乡土中国》变成一个教育文本后,其实给社会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些契机。社会学的知识走出了大学课堂,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所接受。社会学的专业研究者也有了一些用武之地,得以施展拳脚。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催生的新的经验现象反过来逼迫研究者以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乡土中国》。如果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来阅读《乡土中国》,就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有趣的教育主题。比如,“文字下乡”其实讨论的是知识和观念的经验基础,“差序格局”以及建立于其上的“道德观念”和“教化权力”涉及的是知识的社会效用与教育的社会功能,“名实分离”的本质则是知识的规范基础的变迁。作为教育文本的《乡土中国》不仅打开了上述这些讨论空间,而且还迫使社会学研究者反身性地思考自己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承者,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明确相应的位置与功能。不过,本文只是笔者基于近年的实践得来的一些体会,或有偏颇,还请方家指正。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