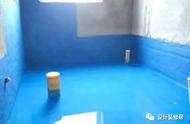胡渡 未来勇士服务号

现代军事教育伴随着西方军事科学地位的确立而产生。专业的教育、思想的统一和团队的精神,使二战前的德国战争学院成为军事职业教育的典范。
职业军人,在20世纪的几次世界性战争中做出了令人膛目的战绩。进入21世纪,社会文化趋向多元,战争形态不断演变,职业军人还能够独领风*吗?

参谋组织的发展确立了战争的科学地位
参谋(staff,标杆、支柱)一词来源于精通设营术的军需官,早期负责行军道路、设营等技术性勤务工作,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
到18世纪末,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军事数学理论,认为战争是一种可以计算的科学。拿破仑时期,战争已经不再是国王之间的赌博,而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民众战争。此时的法国国防部已经出现总参谋部的雏形,但拿破仑的个人天才阻碍了法国参谋机构的发展。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竞相向法军学习。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将科学精神引入军事领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06年,耶拿战败后,具有现代特征的总参谋部首先出现在普鲁士军队,主要负责地形测量、战场勘察、研究战略方向和未来战斗样式等,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沙恩霍斯特被认为是现代总参谋部的创始人,还赋予总参谋部军事教育任务。
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逐步成立了战史处,负责考察古代和近代战局;设立武官处,学习和研究外国军队;利用地图、模型和沙盘进行“图上演习”等。1815年之后,在若米尼“军事科学”思想的影响下,普鲁士战争学院减少了一般性研究而专注于教授军事专业和工程技术科目。
到了1850年代,赖赫尔时期的“总参谋部已经呈现出一副军事科学办公室的形象。”
毛奇虽然称得上是有教养的军官,但他的政治信条是“秩序”,一心想要造就素质一流的军事专家。他干脆抛弃了沙恩霍斯特培养“政治军官”的理想,取消了战争学院广泛的普通课程,把军史部当作发布“训诫”的讲台,留下了“精确无误”的军事思想遗产,为此后100年的军事教育确立了军事专业化的标准。
他清晰地觉察到技术进步在理论上的意义,成立铁道处,建立电报、飞艇部队,创新“分进合击”的指挥理论等,用科学精神塑造总参谋部。他要求总参谋部军官必须认真研究并熟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具有默默无闻的工作作风、掌握准确无误的工作方法、善于精心计算目标的可行性、对技术进步有充分的了解,以及团结部属的高度责任感等。
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总参谋部首次获得战争期间的作战指挥权。1871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使总参谋部赢得了传奇般的声誉,毛奇也被戏称为“神人”。
这一切表明,战争,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甘做幕后英雄的军事专业人才,“这个曾被贵族所垄断的领地,现在已为科学家所占领”。
技术主义有力推动了军事职业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技术兵器开始得到充分发展,军队更加依赖于国家的经济,达到战争的目的比过去更加复杂。技术主义强调由技术为主体构成的战争工具的作用,在机械化战争时代,占据了军事科学的头条位置,战争艺术似乎已经*。
鲁登道夫是一位“反克劳塞维茨分子”,他的总体战思想反映了一种单纯军事主义。泽克特则把总参谋部军官当作战争机器的零部件,不需要独特的性格,只需要经过精心训练、具有广博知识,而且具有可替换性。
他们两人都可以称为现代战争的工程师,致力于把德国军队打造成一部完美的战争机器。
此外,还有“闪击战”、“空军制胜论”、“坦克制胜论”(“机械化战争论”)、“职业军队论”和“小型军队论”等,都“将敌人当作系统性交战和毁灭的对象”,致力于发展系统性的战争机器。
富勒的言论充分表达了“技术制胜论”的观点。他写道,“现在我相信机械化战争,也就是相信武器装备的军队,这种军队只需要少量的人和强大的机器”,“就可以构成99%的胜利”。
到二战期间,希特勒希望德国军官“像皮革一样坚韧、像猎犬一样敏捷、像克虏伯钢材一样坚固”,而且不受思想的羁绊。总参谋部已经失去参谋、顾问和助手的资格,只是执行希特勒意志的工具;战争学院已经完全专业化,不再涉足非军事领域。
军事专业主义为军事职业教育供了理论支撑。
科学精神和技术主义使得西方军队,“不仅在武器上常常处于优势地位,在组织、纪律、士气、主动性、灵活性以及指挥水平方面同样胜过对手,”并由此确立了近代以来西方军队的普遍性优势。
1950年代,亨廷顿将其归纳为军事专业主义,它指的是军官特有的一种“职业发展模式”和“理想化规范”,包括军官的专业技能、军官的责任和军官的团体意识。
其中,军官的专业技能主要是指“暴力的管理”,即军事力量的组织、装备与训练和军事行动的计划与指导;军官的责任主要是指“为社会之军事安全尽职尽责”;军官的团队意识主要是指一种“保守的现实主义军人心态”,即一套“以团体为中心”的价值观,包括忠诚、服从、纪律、责任感等。
在亨廷顿看来,只有军官才有资格成为军事专业者,因为军官阶层以其独特的专业技能、责任意识和团队精神区别于其它专业。
亨廷顿认为,“暴力的管理”是一种极端复杂的知识能力,很难自实践经验中获得其重要成分,必须经过完整的教育训练才能具备。而这正是军事职业教育的精髓,“如果军官越接近专业理想型,就越显得强而有力;相反,如果远离专业理想型,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系统分析把战争变成了一门新科学
运筹学在二战期间的迅速发展,促使美国空军在战后建立了兰德公司,招聘了一批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处理硬件设施的问题,不久又招募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复杂的军事问题。
这些文人专家认为,先前的“各种军事事务根本没有经过科学研究,只是被二流人物漫不经心的关注了一下而已”,他们的志向是“以新方法取代老方法”,把战争变成一门新科学。
被称为“长着腿的IBM”的麦克纳马拉认为,系统分析是探索复杂军事系统的唯一逻辑,“所有的军事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在有效分配和使用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问题”。在肯尼迪时期,这些文人战略家凭着“成熟老练和高超的学术素养”,“进入了权力要塞,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胜过了军事顾问”。
一直到1990年代,美国正“明显地朝一支更为专业化军队的方向发展”,西方各大国普遍采用德国战争学院的军事职业教育模式,强调通过“明确的原则、事实的积累和既定的答案”,来训练和提高军官管理和运用战争暴力工具的专业能力。一些军方精英也开始致力于获得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学位,掌握军事科学的新方法。

军事职业教育的问题所在
军事职业教育在20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过度重视军事技术训练,忽视了战略意识的培养,在军事历史、政治和外交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德军的失败正是军事教育的失败。德国的高级军官从未被要求对战争的非军事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都是“坚强的战士、优秀的战术家、战役法大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无数的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兰德公司也被戏称为“科学与死亡研究院”和“数字理性主义研究院”。依靠系统分析成名的麦克纳马拉,也因为过度依赖计算机,而在越南战争中遭遇惨败;掌握高科技知识和武器的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胜利并没有马上带来政治胜利,反而陷入了泥潭,等等。

隆美尔是德军唯一没有接受正规军事职业教育的元帅,他清醒地看到了军事职业教育的问题所在:各国参谋本部的军官都是知识分子阶级,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把战争看作一种科学,因此很难摆脱主观偏见。
他认为,对部队而言,最好的福利就是第一等的训练,因为它足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但对高级军官教育而言,最重要的是对基本原则理解的同时,保持一颗独立的心灵。
弗里德曼认为,“不管人们热衷的新型武器是陆上的还是空中的,其背后显现的是一种现代主义魅力,它可能代表了一个建立在机器基础上理性的、崇尚技术统治论的超高效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