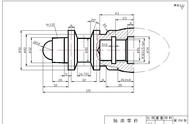今天是腊月初七,马上就要过年了。今年的春节,大概是不能回老家过了。年越近,思乡逾切。
我们老家,腊月里都要“打豆腐”。为什么把“做豆腐”称为“打豆腐“,这一说法沿袭自哪里,不曾听村里的老人说过,至今不解。
小年前后那几日,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打豆腐”。村里有一户人家,有做豆腐的手艺,全村的人每到过年几乎都在他们家打豆腐。
各家各户“打豆腐”需要自己准备柴火和黄豆,柴火要晒干,黄豆要泡好几天。村里过去种棉花,柴火自然是清一色的棉花杆,有的已经折成了柴火把子,有的干脆就是从地里扯出来晒*完整棉花杆。黄豆,多数也是自家种的。
我们县,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三分耕地。地少,土地过去主要用来种棉花,收入微薄,没有什么水田不能种水稻,吃米还要靠买。每家每户的菜园子都只有巴掌大,种点寻常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菜园子没有菜就得买菜吃。
即便如此,很多人家还是会种一点黄豆,因为年前家家户户都要打豆腐,这是那个年代过年必备的年货。没有种黄豆的人家,也要买黄豆打豆腐。
小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打豆腐,所以要排队。
小时候去帮母亲打过几回豆腐,豆腐坊是一间低矮阴暗的厢房,里面有磨豆子的机器,还有一个土灶,两口大锅,还有几口大缸,还有过滤豆渣的网兜和压制豆腐的木板盒子之类的。
离开那间低矮阴暗的小作坊太多年了,只依稀记得这些场景。
豆子泡好送到豆腐坊后先倒进机器里磨成浆,然后把浆倒进网兜里过滤。那些物件的名字我早就忘记了,只记得需要人工摇啊摇,豆汁沥下进了底下接汁水的大木盆里,豆渣则留在了网兜里。

图片来自网络
豆渣,可以当菜吃,也可以当饲料喂猪。豆渣当菜的做法,我至今大概还记得一些:把豆渣倒进油锅里翻炒,起锅前加点大蒜叶,放点剁辣椒,出锅后香味扑鼻十分下饭。不过,炒豆渣不能吃得太急,吃急了容易噎着。
过滤完的豆汁,随后就要倒进大锅里开始大火煮了。每家每户不仅要自己出柴火,还要有人负责加柴烧火,做豆腐的师傅只负责点豆腐。如果有需要,师傅可以根据各家各户的要求揭出几张豆油皮。这两年,我在武汉和长沙的一些餐厅看到过现场揭豆油皮做菜的现场。
后面的程序,大概就是用石灰水点豆腐了。幼时不关心这个环节,就知道豆汁一旦煮好盛进了大缸里,就一门心思等着吃豆腐脑。幼年家境贫寒、物质匮乏,一年到头也就那一天能喝到豆腐脑。
做成的豆腐,母亲用两个木水桶挑回家,留几块泡在水里吃新鲜豆腐,一部分切成块做霉豆腐,大多数要做成豆腐丸子。家里没有钱买太多肉,所以极少做肉丸子,多数都是豆腐丸子。把豆腐用手捏碎,然后加入姜末盐和一些酱油,搓成乒乓球大小整齐码在簸箕里。晚上烧开一锅油,炸丸子就开始了。
豆腐丸子炸出来金黄的,十分好看,却并不好吃。冷却后,用针线把豆腐丸子穿起来,挂到室外和腊鱼腊肉一起晾晒,晒干后可以房梁上吃到初夏时节。
四月份,天已有点热,菜地里还没有什么菜吃,豆腐丸子还没吃完,挂在房梁上长了霉,母亲也舍不得扔,取下来洗洗切成丝加点大蒜叶炒着也是一盘菜。
小时候吃这种豆腐丸子吃得快吐了,长大后一直不喜欢吃,但两个哥哥却好像很喜欢,没问过他们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我是吃怕了。
豆腐炸完,年也就到了。
褚朝新
2022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