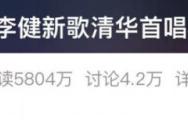蒂勒曼所强调和赞美有加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乐团让“所有参与者都因此感到一种特别的放松”的艺术氛围(“拜罗伊特乐队的音乐家比平时要开心得多,这正是在其他地方可望而不可即的”),在另一本书中有着高度相似的表达。那是汤姆·塞维斯所著《音乐作为炼金术》一书中写指挥家阿巴多与琉森节日管弦乐团的第6章。此处的着眼点在于,当阿巴多给予乐团每一位演奏家以最大的尊重和自由空间时,带来的是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乌托邦式美妙氛围。塞维斯引用琉森节日管弦乐团低音提琴声部首席(平时是维也纳爱乐乐团低音提琴声部首席)阿罗伊斯·波施的话:“我回想与卡洛斯·克莱伯,与列奥纳德·伯恩斯坦,与卡拉扬的合作,这些名字如今我们觉得如此伟大,但与他们合作也都存在问题!而且在乐团中对他们每一位也总有不同的看法。但这里(琉森节日管弦乐团)却没有,只有与阿巴多一起在音乐上的协调合作。”(Tom Service, Music as Alchemy, Journeys with Great Conductors and Orchestra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2, p.255)

与拼凑相关,甚至可以说因拼凑而具有的美妙合作气氛相对应的,是音乐演奏的水准。在2009年9月20日至25日这一个星期里,听到一场或几场国家大剧院“琉森音乐节在北京2009”阿巴多指挥的四场音乐会的听者(笔者有幸听了全部四场),能亲身感受到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马勒、莫扎特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中达到的是什么样的水准。

2009年,阿巴多指挥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而阿巴多与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并非孤例。由乔治·索尔蒂从世界各国35个乐团中选拔演奏员组成的世界和平管弦乐团,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拼凑乐团”,当这个肩负着世界和平理念的乐团于2005年9月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时,坐在乐团首席位置上演奏作品中大段小提琴独奏的不是别人,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时任首席莱纳·屈希尔。乐团中还有很多面孔都是音乐爱好者们熟悉的世界知名乐团的演奏家,包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华人小提琴家夏三多。这是什么样的“拼凑”!“拼凑乐团”的杰出范例还包括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与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一起发起成立的“西东合集乐团”,取自歌德诗集的乐团名字蕴含着深意——来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青年音乐家们并肩而坐,演奏贝多芬、瓦格纳,以及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信仰的人们共同热爱和珍视的音乐。

巴伦博伊姆执棒西东合集乐团 ©Monika Rittershaus
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伟大的拼凑乐团”,都不是常设乐团,而是每年只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的乐团,而它们的水准却为无数非拼凑固定乐团所不及。而它们也没有全年性的音乐季演出,所以,那种以是否有音乐季作为鉴别“水团”标准的说法也完全不适用。
放眼当今乐坛另一个现象级的演奏团体群——古乐团,拼凑的情况更加普遍。我们通过无数唱片和现场演出所熟知的著名古乐团,无论是罗杰·诺林顿的“古典演奏家”,还是已故指挥家克里斯托弗·霍格伍德生前创建领导的“古乐学会”,抑或约翰·艾利奥特·加德纳的“革命与浪漫乐团”,成员的共享率相当高。我经常想到多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午间,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教员休息室,我问研究古乐的学者蒙克教授,伦敦何以汇集了如此之多的一流古乐团,他笑着答道:“它们往往就是一回事。”(They’re always the same things.)
与“水团”有着“近亲关系”的另一种被认为充斥于国内新年音乐会舞台的,是所谓“活儿团”(这个词中的儿化必不可少,不然意思会发生质变),也就是为一桩或一系列演出的“活儿”而拼凑的团。行内人士对这种乐团并不陌生,我们经常在电影和电视剧片尾看到的一些乐团,就是专门录制影视配乐的“活儿团”。在唱片录制领域,“活儿团”同样存在,最知名的当属指挥家、唱片制作人和音乐改编者查尔斯·杰哈德创建的国家爱乐乐团(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其成员为伦敦各大乐团首席和演奏界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技艺精湛和视奏能力强,也就是说,“活儿好”,因为这样的“活儿团”需要以最高效率完成录音。在对该团的介绍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表述:甚至斯托科夫斯基和索尔蒂这样级别的指挥家,也与国家爱乐乐团有成功合作。索尔蒂为迪卡公司录制的深得好评的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帕瓦罗蒂和玛格丽特·普莱斯演唱男女主角),合作乐团正是国家爱乐乐团。